——对话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漆子扬教授

漆子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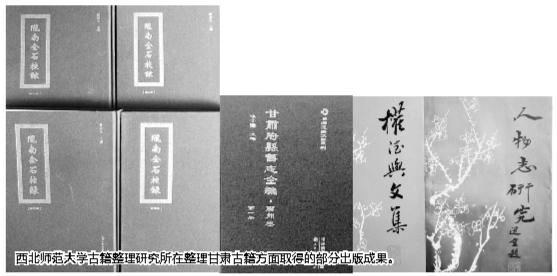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整理甘肃古籍方面取得的部分出版成果。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于1983年的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古籍所)是一个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汉文文献及西北地方文献为中心的科研教学机构,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属的全国唯一一所地方院校研究基地。
近日,记者就如何保护传承古籍,采访了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漆子扬教授。
“什么是古籍?”
记者:漆教授,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什么是古籍?
漆子扬:什么是古籍?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清楚。简而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古籍指辛亥革命前的书籍。现在范围有所扩大,包括民国时期的典籍,甚至1912年后刊印出版的著作,若在内容或形式上依然属于旧有的风格,如旧体诗文集、校注集释等整理类著作,也都属于古籍范围。
在纸没有广泛使用之前,书籍主要书写在竹简、木牍、绢帛上,把竹片木片用绳子连缀起来就叫“册”“篇”,捆起来存放叫“卷”“编”。
阅读古籍要讲究版本,也就是常说的善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文献学专业培训的人都不太注重版本。那么什么是善本?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好的本子。最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宋代文学家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在欧阳修看来校勘精审,没有讹误的版本就是善本,就是最好的本子。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也说:“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欧阳修、叶梦得对善本概念的总结侧重于古籍校勘的学术性,无讹文、脱文、衍文,甚或错误较少的古籍皆可称为善本。
清代晚期对善本的定义范围有所扩大,如版本目录学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轩语·语学篇》中提出: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旧本。”具体而言,足本指完整无缺、没有删节和缺卷的完整古籍;精本指精校精注,错误极少,甚至没有错误的古籍;旧本指旧刻旧抄的古籍。显然张之洞的定义范围在欧阳修提出的“精本”之外又增加了“足本”“旧本”两个要素。足本、精本侧重指向古籍的学术价值,旧本则侧重指向古籍的文物价值。我们常说孤本、珍本,一般都是从文物价值角度来断定的。
古代无论学者还是藏书家,都崇尚古籍善本。善本本身是精校本,是古籍中最优良者,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尽管历史上古籍多次遭罹厄运,如秦始皇焚书,项羽焚烧咸阳宫,西汉末年赤眉军烧长安,东汉末年董卓焚烧洛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焚烧洛阳皇室,梁元帝焚烧宫廷图书,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兵变焚书,金兵毁汴京,太平天国在南京、杭州、宁波烧书,尤其1932年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人寰。但是,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依然依靠读书人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一大批有识之士奋不顾身投入抢救古籍文献之中,聚徒授学,校勘古籍。
《汉书·河间献王传》载,刘德“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隋朝礼部尚书甘肃平凉市灵台县人牛弘上表隋文帝,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隋朝国家藏书一度达37万卷,77000多类。即使强盛的唐朝也望尘莫及。又如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遭罹太平军破坏的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部分散失民间。杭州乡贤丁申、丁丙兄弟发现当时杭州人包裹食物的纸竟是《四库全书》散页,深感悲切,遂奋力而起,搜求抢救八千余册,约占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并绕道运至上海保存。可谓天不丧斯文!
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古籍保护的黄金时期。国家层面加强对古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出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
记者:大数据时代,该如何理解古籍的当下意义?
漆子扬:先辈们之所以耗尽毕生心血保护修复整理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察,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实现复兴的精神坐标。
从知识层面说,不同年代的古籍承载着相应时期的知识和文明。如明代军事类古籍《武备志》,分类科学,收辑详备,从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五个方面,存录了古代极其珍贵的军事学资料,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如在青蒿素抗药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古籍《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获得泡水绞取汁的启示,从而成功提取了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青蒿素,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从学术史来考察,古人整理书目、精校精注的过程需要耐心与学识,更需具备深厚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学养。不管是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治学精神,还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术理念,对当下的学术界而言,具有端正学风、纠正时弊的正面引导意义和学术道德感召力。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全社会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文化依赖古籍代代相传的重要价值,尤其人文科学,古籍保护整理传承是一代学术高度的标志之一。今天保护古籍、整理古籍、传播古籍有了全新的目标,不仅仅限于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主要在于古为今用。
“厚重的甘肃古籍家底”
记者:据了解,在2010年到2013年间,古籍研究所曾对甘肃古籍进行了摸底调查。
漆子扬:我们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在2010年到2013年曾对甘肃古籍进行摸底,清理了清代学者邢澍《关右经籍考》、乾隆《甘肃通志》之《人物》与《艺文》、安维峻《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著书目录》、民国《甘肃通志稿·艺文》及张维《陇右著作录》《陇右方志录》、王烜《甘肃文献录》、郭汉儒《陇右文献录》等书目著录情况,查阅参考《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历代及民国以来编制的各种书目,而且作了一定实地搜访工作,共厘定1949年前甘肃汉文著述大约2100余种,包括经部250余种,史部440余种,子部380余种,集部950余种,丛书部12种。有作家学者2000余人。其中,王符、秦嘉、徐淑、赵壹、张奂、皇甫谧、傅玄、王嘉、刘昞、索靖、牛弘、李白、李益、权德舆、梁肃、牛僧孺、王仁裕、余阙、李梦阳、赵时春、金銮、胡缵宗、黄谏、彭泽、段坚、巩建丰、吴镇、胡釴、邢澍、张澍、李铭汉、王权、刘尔炘、李克明、王烜、杨巨川、韩定山、冯国瑞等都堪称大家。
2100余种著作,大多数流失散佚,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国内外除敦煌文献和民间收藏之外,现存共计约500种,其中经部古籍95种、史部古籍250种、子部古籍60种、集部古籍90种。民间收藏经过“破四旧”,估计数量不会太大,价值比较高的也不会多。这大概就是甘肃古籍的家底。
记者:在您看来,(甘肃古籍的)这个家底还厚实吗?
漆子扬:厚重!因为有的一种书就有几十册。
“呼吁成立‘甘肃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
记者:在4月16日由古籍所主持召开的学习《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线上座谈会上,有专家表示:甘肃民间有许多珍贵的古籍资料,抢救整理保护迫在眉睫。对此,您怎么看?甘肃省古籍保护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
漆子扬: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过近15年的努力,甘肃省主要的古籍收藏单位都完成了古籍普查工作,全省80%以上的汉文古籍完成了在册登记,可以说古籍家底是基本清楚了。
在我看来,现阶段古籍保护工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缺乏省一级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早在1981年成立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时,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方相应成立了由分管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副省长任组长的省一级领导小组。因此,我在此呼吁甘肃省也能早日成立“甘肃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组织规划我省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以免重复出版,浪费资源。
第二,古籍保护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古籍普查清点工作进行缓慢,基层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存条件得不到改善,无法达到古籍保护的基本要求。建议省财政部门设立古籍保护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定期下拨,用于基层单位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第三,古籍保存环境差,很多基层古籍收藏单位不是在建设之初就设计了古籍专藏空间,而是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随意选择一间或几间房子作为古籍书库。书库内既没有古籍专用书柜,也没有恒温恒湿的空调设备以及防尘、防虫、防光、防潮、防火、防盗等保护设施,有些古籍放在纸盒或木箱里,或随意打包堆放在某一个角落里。保存环境条件的不足,加速了古籍的损坏。
第四,缺乏一支素质较高、业务精湛的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队伍。古籍保护专业人员不仅要求懂得目录学、文献学、版本学,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古籍相关知识,同时,在数字化时代,还需要了解一定的照相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计算机基本操作等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技能。古籍修复人才的严重短缺,与海量的古籍藏量严重不匹配。
第五,古籍珍本的再生性保护迫在眉睫。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是古籍保护的一体两面,为了使古籍化身千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出版领域在点校整理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需加强影印和数字出版等手段。
第六,古籍数字化工作尚需加强。据省图书馆研究员、古籍所兼职教授、著名目录学家岳庆艳老师说,全国已建成了“古籍基本数据库”,甘肃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已近尾声,“甘肃省古籍基本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已纳入甘肃省图书馆的“十四五”规划中。目前急需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加强沟通与合作,尽早将“甘肃省善本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提上日程,真正实现“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目的。
“让古籍活起来实际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
记者:您如何理解讲好甘肃故事,“让古籍活起来”?
漆子扬:结合甘肃情况,“让古籍活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古籍活起来实际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把高深莫测的古籍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进行通俗化,符合现在人阅读新生趣味和方式的转变。比如选择我们甘肃历史上的家教文献、崇尚正义的文献,勤俭节约,勤政廉明,知书达理,爱护自然,扶助贫弱,吃苦耐劳,刻苦读书,报效国家社会,以及抵抗侵略追求和平等等文献中各类感人事迹,非门别类,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精选精注精译精评,配以古籍原本或善本的插图,激励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向上,使古籍走进千家万户。
第二,古籍活起来就是古籍的“数字化”建设。我们甘肃应该鼓励社会创建文献数据平台,并利用微信公众号对甘肃文献进行叙录式推广,力争使每部文献都有“前世今生”。打破单位壁垒,强调“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古籍密切相关。
第三,古籍活起来就是推动古籍“影像化”,包括善本影印。加强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制作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服务。支持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单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鼓励古籍文创产品开发推广,如高仿我省收藏的《四库全书》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经史子集各选一两种,让普通人了解《四库全书》的装帧版式等等。
另外,由我省高校教师、文史馆馆员研究员、博物馆馆员、省图书馆研究人员,与知名学者和有公众影响力的播音主持人、遵守艺德的演员共同参与,在电视台、广播、文化演出中推出我省古代学者和古籍保护的相关节目,让古籍家喻户晓。
“一代代学人甘愿寂寞只为甘肃古籍”
记者:古籍整理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寻查佚文,勘定异字,探究出处,折中是非,必须探尘封于旧簏,理虫烛之遗篇,而且往往数日不能得一字,通宵难以定一义,还是一项需要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工作。
漆子扬:我从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36年,领我上路的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校勘学家郭晋稀先生。我是1986年师大中文系毕业留校进古籍研究所,所里研究由所长郭晋稀教授指导我读书学习。郭先生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是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的高足,1950年来在师大中文系教书,闻名国内学术界,是研究古代文论和白居易以及音韵学的大家。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当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是郭先生评审的。郭先生当时让我把没有标点的繁体字本《汉书》每一篇《传赞》抄一遍,然后标点分段,做完一篇去家里让先生评阅,点错的地方都是我理解不准确的地方,郭先生给我细心讲解字义句意。先生讲课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评析深刻,让人仰慕不已。有时候我听不明白,先生儿子令原兄看我好像有点懵懂,他就现场翻译,一来二去,我和令原兄居然混得比先生还熟悉。令原兄擅长古代文论,读书极为广博,知识面非常广,曾整理校注《诗品》等典籍,主编过《大学语文》教材。大概两年后,1988年新所长到任,我和甄继祥老师、胡大浚老师、伏俊琏老师还有王锷兄一起参加了陕西师大辞书研究中心的国家八五辞书规划项目《十三经词典·仪礼卷》的编写,因为没有电脑,单位让我抄写阮刻《仪礼》前后不下五遍,编写整整十年时间,直到2010年才出版。因为参加集体项目,原来标点《汉书·传赞》的计划也随之泡汤。先生去世已经20多年,至今想起当年给我上课时抽烟的动作,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依然如昨。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雷媛荆雯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