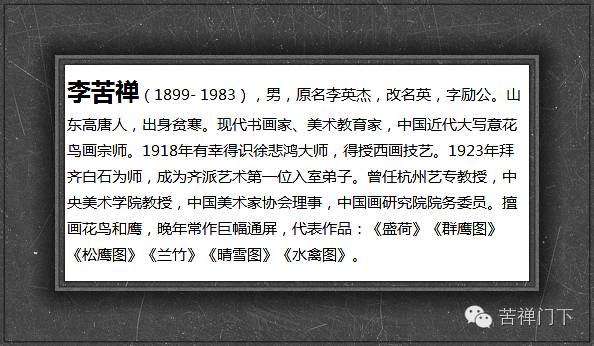
眼前一张公元1957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老旧发黄,似乎很平常。但仔细披读,却很有文史价值。先看第三版《访问记》栏目下的一篇报导文章《一个老画家的遭遇》,并附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报刊首次发表的李苦禅作品《浴沙图》。文章是由骆拓①署名发表,全文如下:
美术界的前辈们都熟知李苦禅作画,是以大气磅礴、笔墨纵横,淋漓尽致为其特色。老画家齐百石,徐悲鸿都对他的画作过很高的评价。从一九二九年,李苦禅在杭州艺专当教授算起,他从事美术教育已经有二十八年了。在过去,他曾经是许多青年所崇敬的名画家之一。
最近,记者见到李先生,他拿出两张近作,很激动地说“七八年没怎么动笔,笔墨都生疏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笔墨捆得生疏了?他才谈出下面一段遭遇。

李苦禅在煤渣胡同九号美院宿舍西屋(约1964年)
从教授到卖戏票
李苦禅说: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我竟会遭受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工作上到生活上的打击。解放后,徐悲鸿院长有职无权②,学校对我采取的措施,使他感到无能为力,曾为我掉过泪。
我和王青芳③在解放后不久,就被认为“思想落后”而解除职务,从教授变为每月领八块钱,十个月一领薪的“养老人”。学校的学习小组连我们的名字都没有,学习是我们的迫切要求,可是谁也不理不问。开会,听报告,要求参加也不准,可是有些领导又莫名其妙地斥责我说:“你为什么不开会,不学习?”
学校领导乘徐悲鸿院长病重时,把我和王青芳调去陶瓷科画茶碗④,整整画了一年。后来又突然调我去工会,我不敢问,只好顺从。到了工会,给我的工作是买电影票,戏票,有时票没人要,我只好站在戏院门口去卖票。过一阵,又调我去图书馆写线装书上的“上函”“下函”。这种遭遇使我灰心丧气,经常以酒消愁,当然我这种做法更使我“落后”消沉下去。这时“精神不正常”的“称号”也上了。
第一次和江丰握手
我的画也被作为谈笑的对象,有些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画的是什么玩艺儿呀!”使我几年来再不敢画国画了。我成天被关在家里,不能下去体验生活,按我的经济条件也只够出西直门,这让我怎么表现新时代呢?
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迫使我变卖东西,我爱人也因此被迫堕胎。于是我只好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很快派人来安慰我⑤,徐悲鸿院长对我说,毛主席随后给学校来了一封信,可是这封信,直到今天学校也没有给我看。我这个当教授的,在最近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会上,才能够和江丰⑥第一次握手,荣幸的手!

在宗派主义的排挤下
学校里,只有党团员、人事科说话权威。有些青年很厉害,专门找我们的“落后”事例。人事科不出门,光坐听汇报。我是旧社会来的,见面总有点头问好的习惯,团员说我是庸俗主义。发薪时我给孩子买过一条小鱼,就被人事科干部指责为“大吃大喝”。我唯一的美国毯子,因失口说它是好东西,就被作为斗争的理由,说我是“唯美国货者”。李苦禅痛切的说:勤勤恳恳工作,却遭到排挤,相反的,只要能汇报的却得到重视,这是极不公平的!
王青芳遗作无法处理
谈到王青芳,李苦禅眼泪盈眶地说,王青芳倒下去了,他的死和学校给他的压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学校一会儿让他去内蒙,一会儿又要他去哈尔滨工作,临行时,学校又说还没有联系好,这是在开玩笑!为了学习新内容的画,王青芳低三下四地忍受着领导粗暴地当面把他的作品揉掉,撕毁。他死后,学校连棺材钱都不准报销。他遗留五百多张画,像我这样的亡友,既不是权威,更不是有办法的人,也无法给他处理。希望有关领导能使他的作品和群众见面。我和王青芳申请加入美协,也遭到驳回,理由是:我们不够“资格”。
国际友人来的时候
我的东西送哪儿,哪儿都不要,实在是走头无路,当我送去美术服务部时,工作人员蛮横地说,你的画不行,留你两张吧!像我这样的国画家:只有国际友人指定要看我国的民族传统时,才“勉强”被学校拿出来应付一番⑦。有一次苏联的画家要看我的画,刚挂上就被领导责令去掉,被扔在墙角⑧。又一次,国际友人到美术学院参观,要看国画表演,学校到处找人都找不到的时候,只好把我找去⑨,当时有的党员很惊奇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他有神经病”
李苦禅说,美术学院领导已经不要我了,把我调去民族美术研究所当业务员,职责是什么,我到今天也不理解。可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是要我的,他们要求我去教课⑩,请问学校知道吗?李苦禅几年来的不幸遭遇,美术界许多人是不了解的,因而也听信他是“神经不正常”的谣传。直到美协召开国画家的座谈会上,李苦禅一边发言,美协的干部还一边对记者说:他有“神经病”。其实,在中央美术学院排挤国画的方针之下,李苦禅不过是被牺牲的老画家之一,而最使老画家难过的,除了他本人的遭遇之外,是这样下去会断送了国画第二代!
注释:
①骆拓先生是华侨,在国立艺专学习时是徐悲鸿先生的忠诚弟子,他在新加坡的家族与徐公关系甚密切,徐公也曾居于其父家中,作画甚多。1957年骆拓时任《北京日报》记者,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是他因此文,在不久之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摘了“右派”帽子之后他迁居香港)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纷纷来信表示同情,李即回信予北大同学们,感谢学生们对他的关怀,见附(一)李苦禅致邓锡良信函与注释。附(二)骆拓2008年6月九日赠李燕手书《李苦禅师友之情一甲子——戊子春千禧越八载八十晋一老人骆拓于加拿大安大烈洽文山芳草谷怀故人》附(三)国家艺术核心期刊《美术之友》2009年第6期刊文《江山万里心——骆拓。霜蹄露足气自豪》摘录。
②昔日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此前院长徐悲鸿先生在田汉先生的亲自动员下仍旧留在了北京,他在艺专所聘的全班教授、职员也皆未乘南京方面的专机飞往南方。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氏仍被任命为院长。但不久,他即发现自己无权参予决定任命教员,也无权参予制订院系的教学体制与课程的计划。面对昔日的1918年入其门的大弟子1930年以来的著名国画教授李苦禅的不公正境遇,他竟然不能出面讲话,只有在私下见面时含泪同情而已。甚至院方掌实权者对徐院长本人也有不予重视的言行。因此,家父李苦禅隔三差五地到徐院长家中,去安慰看望自己的西画开蒙恩师,互诉无奈之事。每次一见面,徐公就照例问一句:“苦禅啊!最近外面又听到他们说我什么啊?”这些情况,皆是父亲对我讲过的,今回忆录此。
③王青芳先生(1901——1956)近代文化功绩卓著的王森然先生评之“青芳先生,以画家而专长篆刻……其涩中带有坚挺气,而坚挺气中,又多奔放不羁之精神,峻拔奡荡,不亚邓氏(石如),稳练自然,驾乎㧑叔(赵之谦)……故齐如山先生(梅兰芳先生之文化高参)赞为创作……钱玄同、齐白石二先生均以,自具匠心许之,足见气象万千,卓然成家,独特之美,时无其俦,余爱苦禅画,尤爱青芳印刻,斯集兼而有之,诚开近世未有之奇秘者也。(按:此文发表于1936年出版之《李苦禅画集》后面三页,介绍王青芳篆刻与版画自画像,)王先生亦系木刻版画家,自号“万板楼主”,可知其版画创作之丰,但因遭冷遇,生活困苦,忍将已经刻好之木板以木料价钱卖予版画系,将其刨平,供他人再刻。其板之多且质良,我少时亲睹矣。有人知其画徐悲鸿先生奔马几乎乱真,出资请他专画徐氏风格之马,但不让题名款,他即知,这是让他伪造恩师之作,由他人仿题徐公名款以骗人。他则坚决不为,怒斥奸商,宁穷困而不失人格正气。他的形象可见于蒋兆和先生创作的《流民图》中:一身长衫,留着长发仰天者,即是他做的模特,形神皆似。
④当时中央美院设一陶瓷系,我常去观看,以后此系合并到了中央工艺美院。彼时家父李苦禅与王青芳先生被派到该系画青花釉下彩的茶碗,据说用以出口,为国家换外汇。但因为“不准宣传个人,”所以二人都不能在茶具上签名,皆成了 “无名氏”之作,故因不值钱而无一保存下来。
⑤此段历史可阅本人文章《毛泽东与李苦禅》
⑥最先接收“国立艺专”的党委成员为艾青等人,江丰则是在1951年后接任中央美院党委领导,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⑦有国际友人来参观美院时提出要看中国写意画,院中尚存有李苦禅四十年代留在“国立艺专”的范画裱轴,可以暂时出示一二。
⑧家父对此事殊为伤心,多次向我与友人言及。
⑨外国人来美院访问,提出要当场看大写意绘画的创作过程,因为当年尚无一人愿意领受此任,才打听到了李苦禅一向示范教学,故领导委托将此任务下达给他,他泰然临阵,毫不怯场,当着众人围观,信笔挥洒,有意先从尾部画起,最后添上鹰头,令外宾们拍手惊叹。表演回家后他非常兴奋,多次谈到,“我特意让外国人看看,只有我中国才有这种高度的写意艺术,让他们开开眼啊!”以后每逢外宾访问,都由家父表演做画,回来之后侃侃而述,充满了民族文化自豪之感。但这些画皆无任何报酬,都留在了美院,并不展出。
⑩因为苦禅老人以往的知名度很高,当年仍有不少院内外的学生主动要求向他学习写意书画。所以那时多有学生来家中学画,他则谢绝学生的学费,无偿无私地授课,并将当场演示的画作赠予学生。
读完《一个老画家的遭遇》之后再读这张《北京日报》的第一版,大字标题是《非党负责干部在市委座谈会上·充分开展尖锐恳切的批评,对整风将起重大推动作用》,在此题下报导的“各界人士发言”中有小标题为《黄浩发言》,报上原文摘录如下:
作为基督徒,他感到了房管局如同在家里,并且有职有权;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黄浩说,他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刚到房管局的时候,还嘀咕别人会对他另眼看待,但事实跟他的顾虑相反,没有人另眼看待他。他说,他在工作上有职有权,大家都对他很好。有一次他住医院,局长和主任、科长、秘书以及其他同志全去看他,待他如一家人。外国来的团体里面的基督徒曾经问他:“共产党待你好不好?是不是真的信教自由?”他介绍了他的情况,那些外国团体很相信,由此了解了一些共产党的政策
他对北京市政提了两点意见,他说,首都没有把三轮车工人管理教育好,比起武汉、杭州、上海、广州、汕头差得多。他说,北京的卫生状况太坏,要建设社会主义,人民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对随地吐痰等现象不加注意。他说,细菌比特务还厉害,大家应该如同对待反革命一样去对待细菌,消灭细菌。
我为什么将这两篇似乎豪无关系的文章合录与此呢?是因为如今的读者几乎全然不知两篇文字的主人公李苦禅与黄浩的历史关系之故。
黄浩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在北平沦陷于日寇的年月,他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的特派员主任,领导平津地区的地下情报工作,公开的身份则是称为“黄道长”的基督教徒。而家父李苦禅则是他在北平发展的一名以名画家身份为掩护的地下情报员,担任柳树井胡同二号情报站的工作。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个秘密组织仍旧坚守纪律,不得暴露组织身份和以往的组织人员。因此,在家父遭到美术界冷遇的情况下,住在北京东城区的李苦禅明知黄浩近在西城房管局工作,但绝不去找他来“解救”自己的困境。同样,能够在这张报上得知李苦禅遭遇的黄浩也绝不能到美院来,证明李苦禅是革命同志,仍要坚守“基督教徒”与“党外人士”的社会角色。有关先父李苦禅当年在黄浩主任的领导下如何开始地下抗战工作,可以详阅本人的另一篇文章《李苦禅在国难时期的地下工作》
附(一):
李苦禅在1957年的信札内容
锡良同志:来信和美术社同学们来信都接到了,知道您们见了报上关于我的访问和座谈的讲话,同情我,安慰我,惦记我。这样推心热诚,却(确)给我极大勉励与更坚决的内在力量①。大凡一切学术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弹性的,常常在中途上会被风摧雹打,这只是在我们预料的意识上作了准备:迟早是成功的!这就叫作“送力”,便是最大的努力,最后的奋斗,一种事业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关键”即在此点。认清了一切事项:文化、工业、技艺、学术等等,将我们人生澈底下来,便大胆的去作,即便发生偏差波折,我们的方向与动机总是不错的,任他们有权威的尽管来摧毁压制,我们的业务即是我们的权威,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早晚会被群众发现知道的,那便是我们的成功与永久的安慰!
我是贫穷的学生出身,我深尝过贫苦的滋味,因此朋友极多,岁数上不论等差,业务上不分高低。但军阀、官僚、富商、律师们,向不接近他们。和这些朋友②自然的发生了同情友谊感情。在廿七岁③开始作教读生活<教授>,在物质上帮助许多贫困的学生,也接济了许多当时地下工作的干部们,并因此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被逮捕入监狱。但我既不是共产党员,又非国民党员,仅是从来想不到个人名利的一位画者④。
文艺是无阶级性,无国界性的⑤,它是同情、共鸣而具含有着和平、敦厚、美感、道德、天真、情感等内因素形成的。根此去作必须修养,体会着这些内容,中国古人先进,讲画法“人无品格,下笔无法也”,大概指着以上等等所讲的。
在我卅年左右间,除去在学校教课外,在家还教了不少的学生,其中有生活困难的,我常供给笔、墨、纸、颜色等,兼常有帮助,经济方面上协助,向来不要什么报丑(酬)的。我感觉要报丑(酬)不伟大还浇薄,与我们所学的“画”很支离,而且极相反的,不协调。同学们不要以此为怀,大家只顾往前去努力,到成功那一天,那才是真正送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重礼品呢!知道就说就写的这一长篇,正确或错谬,我个人亦不知所云尔。
同学们:我近中微微感到情绪波动,仅稍影响著作画了,其余不感如何不适意处,对我关心,即此谢谢同学们!
李苦禅复。
赵增坤同学信已接读,谢谢您的惦念!
(此件信札手稿已收入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立项,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李苦禅全集》第八卷131页)
注释:
①此信写于1957年。当年报章上刊载了一些采访与报导文章,内容涉及当年中国画遭受极左思想的排挤,李苦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大写意书画课被取消,让他到陶瓷系画茶碗(不许题名字),到工会去买卖电影票……因此得到了北大学生们的同情与安慰。
②李苦禅一生从来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做事的人。他的挚友著名写意画家许麟庐说“苦禅一辈子,从来是交下不交上,朋友里少不了劳动人民”。
③李苦禅生于1899年1月11日,赶上戊戌年尾,故题画时往往以虚两岁题记。而此处的“27岁”则是实周岁,即1926年。但齐白石诗集中夸奖李苦禅的诗句“廿七华年好读书”则是在1924年,李苦禅25周岁。
④李苦禅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后参加了地下工作,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主任黄浩同志领导下,成为该情报站的正式成员,组织上安排他以无党派的自由画家身份做地下工作。因此苦禅先生一生皆属无党派爱国人士。他一生保守秘密,直至建国后只说自己帮助了地下工作,从未披露他当年的工作身份,即使受到怀疑和误解,甚至在“文革”中遭到毒打,命他“交代社会关系”,他也从未讲过上下线关系。他当年的工作身份是在2014年由北京市委相关部门首次公布的。
⑤他的这个观点是一贯的,曾在“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但他并不服气。
附(二):
李苦禅师友之情
甲子戊子春千禧越八载八十晋登老人骆拓于加拿大安大略烈洽文山芳草谷怀故人。二零零七年春,接到李燕由北京寄来加拿大找到我的信,既惊奇又高兴。八十年代初在香港李苦禅、胡絜青(老舍夫人)画展见到李燕,已经二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纪阔别了,好久了!
苦禅师在香港画展开幕式上当着数百人,众多新闻记者,把我拉在他与胡絜青、李燕的正中间,大声说:“骆拓为我受了罪和苦,受到不公平的冲击。我没有教过他,和他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忘年知交。”热烈地拥抱,我们二人眼都湿了。胡絜青听得掉眼泪,即刻赠我一副画,是纪念老舍和对我的敬意。感动人的回忆历历在目。
一九七八年我到香港后,很怀念苦禅,尤其是临别,月坛叙别,滴泪握别。我再书此文,以纪念苦老之情友之谊,让六十一年之交再现,留下一点珍贵的资料。我和苦禅师是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际在艺专由悲鸿师親为介绍,并告知他是最早北大的苦学生,很杰出。随后,黄警頑(徐悲鸿年轻时的救命恩人)又为推荐。谁都知道我是艺专唯一的华侨学生,父亲是徐校长的好友,住徐家,是监护的长辈。老师同学都对我热心和关怀,尤其是苦老,山东好汉性格,侠义之情。他知家翁精武术,我自小习武。苦禅师常与我谈到白云观,谈他如何拜师学武功,舞禅杖,舞大刀,耍竹节鞭,走圆步,翻鹞子,踢腿,顶头舌的吞吐,授磨墨呼吸顶舌,虎背熊腰,静心净心,深急重缓的修身之道。苦老在艺专课室没有教过我,但教了秘传之道。我持之以恒,六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教我是超级课程,也许只有我这么一个弟子。此外还有艺专老师李文晋、张大千和棋王谢侠逊三位尊称“师父”更精确。学这方面难在是,师不行学不到,必须又是友,也许还需禅心、道缘,入此境方有深谈之机。
李燕、李健(李燕之妹)不知我与苦老一甲子有这么的经历。苦老养生和作画是两者融汇最杰出的大画家。也许,石涛、八大也有这方面的功夫。齐白石师在授课示范时说:“你们数十年后便知,白石后笔墨功夫当推苦禅。”此预见我深为拜服。吾师为中国画坛创下了很粗的一根历史艺痕。又过了三十年,更确切李苦禅的笔墨是齐师后第一人,他发挥了释道儒的精髓,成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哲理思想。苦禅天地,笔墨有根。发之于世,光辉灿烂。
一九七八年离别旅居世载的北京,移居加拿大。二零零八年载怀着江山万里心,回故里观光国家的成就,并呈李燕、李健留念。
附(三):
2009年第6期《美术之友》刊文摘录:
骆拓在北平艺专还得到众多名师教导,如齐白石、吴作人、黄宾虹、李瑞年、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等。他和李瑞年、蒋兆和、李苦禅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期间,骆拓有时在学校画室或茶馆速写画得太晚了,就临时住在艺专教员黄警顽家,李苦禅甚敬之,经常去探望黄,自然与骆拓见面的机会就多,二人颇投缘。一天苦禅大师看了骆拓画的马和诗,大为赞许,并告诫:“不要画给人骑的马,不要画养尊处优跑不快的肥马,不要画干苦力活的厩马,徐(悲鸿)校长要‘师法自然’,白石师要‘似与不似之间’,你要画自己的马。最高境界是潇洒奔放,无拘无束。不要缰绳,要画马的野性,自由的状态,就像燕子李三(旧京城的义贼)那么快,来无踪去无影”。骆拓善画狂奔之骏马,应该说也是深受苦老的启发,他们从此结成莫逆之交,常在一起切磋儒佛道家之哲理。虽然李苦禅在课堂上没教过他,两人却成了亦师亦友的“师徒”关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