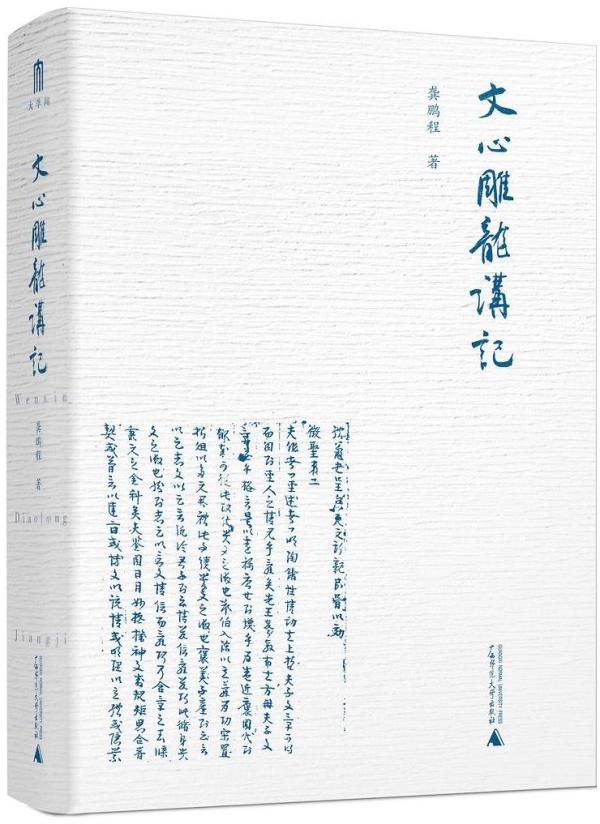
《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500页,98.00元
龚鹏程先生是当世少有的大家通人,其读书之博、著作之丰与自视之高均一时无两。龚先生曾批评以淹博著称的钱锺书先生“论学往往显得‘不当行’”,并隐然以博且当行自诩。在龚氏涉猎的诸多领域中,中国文学批评史无疑是他用力最久亦最当行的领域。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故研探《文心雕龙》逾三十载的龚先生在2020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记》(台版名为“文心雕龙讲疏”,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简体版,以下简称《讲记》),自会引来相关领域研习者的重点关注。
《讲记》一书脱胎于作者2010年至2011年在北大的研究生课堂,作者对课堂有如下回忆:“听众并不都是北大的,他们由四方跋涉而来,听我肆口讲谈,或以为奇。因为我桌上仅一张白纸,写着几条提纲罢了。”(第2页)由有限的“白纸”和“提纲”发展为近五百页的专书,作者的“肆口而谈”背后自是多年的积累。
《文心雕龙》是现代学术的一大重镇,“龙学”之名目足见此书之饱经研究。《讲记》原用于课堂讲授,自然不能不关涉相关背景与常识,也势必要时时回顾先行研究。不过,《讲记》一书,整体上仍是顺流而下,作者以自己对刘勰其人、六朝学术文化及《文心雕龙》一书的整体把握来展开对《文心雕龙》的讲解,对先行研究,则主要取作者认为有误的名家成说以辨正之。
龚氏的整体把握确有不凡处。故其讲论,亦多精要。
对于刘勰其人,由于史料过于有限,其生平只能是粗线条而模糊的。虽然在考实方面难有进展,但关于刘勰生平的争论始终存在,比如他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就曾经是大陆“龙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于刘勰与萧统(或皇室)之关系(这涉及《文心雕龙》与《文选》之关系)等,亦有不同看法。在有关刘勰的具体史料已被反复考索的情况下,如何对其人作恰当的叙述与定位,有赖于对当时制度、环境与人群的恰切把握。实际上,士庶问题在当时固然重要,但面对每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的具体轨迹,厘清士庶并不能说明一切。与其纠结于出身之士庶,不如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参照系以观察各文人。比如说,谢灵运无疑是高门大族之代表,其仕宦经历与人生轨迹足以被提炼出一“理想型”;而陶渊明、鲍照和刘勰则在另一端。比较刘勰与谢客、陶令等人之异同,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勰的命运与心态。然而,由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往往深爱刘勰,故在某一时段,强调刘勰出身庶族,似乎是为他增光;而另外一些论著又总是倾向于推测刘勰与萧统关系密切,进而强调《文心雕龙》与《文选》颇具亲缘度。对于刘勰的生卒年,作者并不作明确判断,而是列出了现存的不同说法,并同时叙述不同生卒年判断下的刘勰生平大要。对于士庶问题,作者主要依循旧说,从世系、亲属方面定刘勰为士族,但又强调他因为“孤儿寡母”而没落,只能依靠自己在文献词章方面的才能获得僧祐的帮助。而刘勰能够结交萧梁王室,恐怕主要是依托僧团,在当时的文人中,刘勰并不是最重要的,就现存资料而言,也看不出刘勰和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有什么互动。在这样一番生平描述下,我们甚至会发现,有的前辈学者强调刘勰卒年较晚(如杨明照、李曰刚先生所提出的卒年,较范文澜、兴膳宏之说晚了近二十年),或许不是基于文献考实,而是借此卒年考订推论刘勰有机会参与《文选》之编纂。考订生卒年尚且如此,遑论考述刘勰与其他文士之互动!《讲记》由此发挥,检讨考订文人生平背后的观念与方法,这确实是值得每一个习惯了“知人论世”的读者深思的。
就文化而言,一般提到“魏晋南北朝”,与之关联的学术思想首推“玄学”与“佛学”。玄学与佛学确是汉代以后的新思潮,也是六朝时期具极大吸引力的流行学说。正因为玄学与佛学新颖且流行,故而不少论者面对“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心雕龙》,仍然更愿意强调玄学、佛学给予刘勰极大滋养。但新潮和流行之下,当时文人的学问、思想、文化的底色,恐怕还是儒学。故而《讲记》从《隋书·经籍志》讲起,通过各部类经籍的卷帙多少,指出六朝时“礼学最盛,春秋学次之”,由此论证儒家学说在当时绝非无人问津。作者进而总结:“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玄学与老庄,其实当时最重礼法门风、经史传家。”如果我们认定玄学、佛教等新思潮才是刘勰思想的主要资源,那么《文心雕龙》一再申说的“征圣”“宗经”便是空唱高调。但如果意识到新思潮的影响是有限的,读书人读的主要还是传统经史,那么刘勰之“宗经”并非言不由衷。《讲记》更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将刘勰有关“宗经”的大论述上下勾连,从汉代讲起,梳理出了一条脉络,作者称之为“文学解经的传统”。刘勰认为,经典是最好的文章,故作文需取法经典。这样一种思路也不是石破天惊之论,在汉代大儒扬雄那里便有类似的表述,此后更是不绝如缕。扬雄是汉代最重要的儒生,其地位曾经极高,只是宋儒不再大力表彰扬子,也未将他列入圣人传道之谱系,故其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在刘勰的时代,扬雄仍然占据熠熠生辉之高位。就此而言,刘勰之倡“宗经”,不仅出于真心,而且渊源有自。
在讨论刘勰的思想渊源时,龚氏在方法论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思想最为玄妙,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落实到言辞、行为来把握。而论思想之影响,更近乎捕风捉影,仅仅凭借着表述、形态上的“相似”,是不能直接论定某人受到某种思潮影响的。比如说刘勰之“宗经”与扬雄之说,在表述上的确高度相似。但若要论证刘勰受到扬雄影响,还需考察刘勰是否提及扬雄,以及扬雄在当时的影响力。纵览《文心雕龙》,刘勰多次提及扬雄,且均为正面表彰或引述。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再结合扬雄在汉魏晋南北朝的崇高地位,我们可以同意:刘勰确在扬雄为代表的“文学解经的传统”中。若依此标准,现代学者或以为《文心雕龙》之结构取资佛典,或以为刘勰之“折衷”乃受佛教“中观”学说影响,均缺乏足够的论证。《讲记》对如是论述也多有驳正。
不过,中古文献毕竟有限,刘勰留给后人的文字想来也是他所有著述的一小部分,若过于追求“确定性”,很多问题便无法讨论。《讲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在论述确定的思想脉络、驳斥不可靠的渊源考索之外,还独辟蹊径地讨论了“类似”与“可能性”。这集中体现在第十讲“文字-文学-文化”中与道教思潮的比照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经典,但不同宗教对经典性质与来源的界说,正能体现该教特色。比如佛经乃是佛陀灭度后,后学们以回忆的方式结集而成,故佛经固然重要,却不在“三宝”(佛、法、僧)之列。道教却认为,经典乃是“天书真文”。不止于此,道教对文字推崇备至,龚鹏程将道教的“文字崇拜”归纳为“由文生立一切”和“以文字掌握一切”。以此观之,《文心雕龙》之“原道”,与道教的“文字-文学-文化”观念,确多有类似处。但龚氏在这番比较后又下一转语:“可是,我不喜欢说无确定关系的‘影响’。因此以上所谈,皆不是说刘勰受了当时道教思想之影响才有类似的说法,而是说当时实际存在着一种跟刘勰类似的思路,足堪对照、相与发明。”(313页)这样一种态度,对于从事“捕风捉影”工作的论者,确有极大的方法论启示。
《讲记》颇类《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涉及各方面均甚当行,上文所述“知人论世”与“捕风捉影”二端,只是举其大者而言。这离不开作者对中古思想、文学批评史的全面观照与深入理解。不过,作为无所不窥的通人,龚氏大开大阖的论学风格,难免会留下一些遗憾。具体而言,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讲记》均有可议处。
如上所述,《讲记》的一大贡献在于强调“宗经”并非刘勰的门面话,故对现代学者的若干说法多有辨正。不过,刘勰标举“征圣”“宗经”是真,但他却从不认为一般人乃至他自己可以成为圣人、写出经典。故《文心雕龙》的妙处在于:一方面标举“宗经”,倡导学习经典;另一方面又认定非圣人无法写出经典,故作者要根据自身条件与时代特征,学经典的精神而有自家发挥,此即“通变”之意。在这个意义上,“文之枢纽”部分,在强调了“原道”“征圣”“宗经”后,必须“正纬”“辨骚”:纬书假托圣人,将自己伪装成经典,故需正之;而楚辞“执正驭奇”,一方面师范经典,一方面依据自身情况表达,“取镕经旨,自铸伟词”,是非经典文章的楷模。以此观之,刘勰“宗经”是真,但不求亦步亦趋也是真。明乎此,我们才能全面理解刘勰的文学史观。《文心雕龙》多有论及文学史发展处,但刘勰面对不同的语境,有三套“话语”。首先是最敷衍的门面话,见于《时序》篇。刘勰在《时序》篇中有一大论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既然文章的好坏与时代的盛衰有关,那么在谈到刘勰所处的时代(“皇齐”)时,刘勰怎能否定?故《时序》篇讲到刘宋与南齐,均为好话,尤其是对“皇齐”,只见赞颂,不闻指瑕。
实际上,刘勰对刘宋以来的文风,多有不满。对当代文坛的不满,也正是推动他创作《文心雕龙》的一大动力。故《时序》篇最后,刘勰故作谦虚地说:“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这实是委婉表示自己上面的赞辞只是门面话而已。对于这一点,古今读者均无异辞。其次是《讲记》反复强调的倒退观,《讲记》认为:“刘勰对文学的评价是顺着经学来的,儒学衰了,文学就差。所以三代最好,汉次之,魏晋以后愈来不堪。”(214页)这话自然不错,但这也只是刘勰一半的真心话。正因为在刘勰以及当时人的观念中,圣人是不可学不可至的,经典也是无法通过后天努力达成的,故而若以经典为标准,那么后世文章均不如经典,文学史只能倒退;但若梳理各文体的线索,则每一文体的发展轨迹又不相同。就以刘勰时代最繁盛的诗赋二体为例,在《明诗》篇中,刘勰对“古诗”和建安诗歌极为推崇。在他的诗史图景里,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正体”固然无法超越,但真正吸引作者和读者的“五言流调”,却以“古诗”与建安诗为高峰,诗史的发展,并非一味倒退。至于赋史,刘勰最尊两汉,次重魏晋,也不是简单的“倒退”可以概括。这是刘勰文学史观的第三套“话语”,也即在整体上承认非经典不如经典的同时,对每一种文体都有专门的梳理与把握。故就整体论,后不如前;就各体言,各有轨迹。
刘勰在文学史论述上的三套“话语”背后,乃是当时的圣人观念,圣人是天生的(故《征圣》篇云“妙极生知”),所以学习圣人不是为了成为圣人,学习经典也不是为了写出经典。顺此思路,文章虽以经典为最高,作文却不必强求成为经典,于是乎文章也就有了自己的一片园地。《讲记》对这一点并无明确的体认,龚氏甚至认为“刘氏本人效法孔子”(180页),如此自不免有所失察。
如果说上述对“圣人/经典”的理解尚属一家之言,作者和读者未必认可。那么《讲记》中另有一些瑕疵,则是再版时必须修正的。以下试按照页码顺序逐一列举。
55页,《讲记》论及《出三藏记集》,介绍了《出三藏记集》的四部分,在谈及第三部分时说:“第三部分叫‘总经序’,对所有经典做个提要,写一个序论。”此说不确,《出三藏记集》的第三部分相当于总集,收录了汉译佛经的序言、后记一百二十篇,并无另写的“提要”。
91页,《讲记》论及南朝文风时引用了萧纲的《与湘东王书》并加以发挥云:“‘「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描写春天,竟要从《易经·归藏》中去引用。”《归藏》是传说中周代以前的“易”,今人讲《易经》,多指《周易》,故此处“《易经·归藏》”一说容易产生歧义。
104页,《讲记》由《隋书·经籍志》考察魏晋学术大势,论及《楚辞》时说:“《汉志》把《楚辞》看成文学之代表,所以归入诗赋略。《隋志》可能看重它表现的思想、人生观,故将之列入子部。”《隋书·经籍志》中,《楚辞》仍在集部。
111页,《讲记》云:“《老庄》因为是玄谈,更是不急之物了。”此处之“《老庄》”当作“《老》《庄》”。
148页,《讲记》云:“这天生下来的人性,《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是‘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段话出自《礼记·礼运》篇。”引号中的话,并不见于《文心雕龙》,作者想要引用的,应当是“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两句。
150页,《讲记》谈及“春秋五例”云:“根据晋代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序》可知,春秋纪事要‘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讲记》在下文还逐一引申了“五例”,但引文却只有四,缺了“惩恶而劝善”一例。
155页,《讲记》论及《宗经》篇云:“第二段分别讲《易经》《尚书》《春秋》《史传》《礼记》等经典如何之好。”这里的“史传”是何经典?实际上,《宗经》篇在第二部分依此讲了《易》《书》《诗》《礼》《春秋》五种经典的伟大。
167页,《讲记》介绍刘勰如何“分体论文”云:“然后怎么论呢?缘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虽未加引号,但后三句话乃刘勰原文,“缘”当作“原”。
203页,《讲记》讨论“文”之意涵云:“而且后世显然也一直沿用这层意思,犹如后世的人物评价体系一直沿用《史记·谥法》(原《逸周书·谥法解》)的规定。”《史记》何来《谥法》?
315页,《讲记》云:“1978年12月11至13日,我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文心雕龙〉的文体论》。”“1978”乃“1987”之误。
337页,《讲记》云:“可是经典如果把它看成是对闭的,是体大虑周、尽善尽美,那又糟了。”“对闭”疑当作“封闭”。
385页,《讲记》引《文选序》“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章”前漏一“篇”字。
452页,《讲记》谈“声训”云:“但汉人在《说文》之外同时还有另一部书也很重要:刘熙的《释名》。《释名》解释文字,主要用声训,就是寻找字跟字之间的声音关系,用声音来解释。比如‘天’,什么叫天,颠也,‘天’跟‘颠’,声音相同,所以用‘颠’来解释‘天’,颠是最顶端,最顶端就是天,这便是声训。”但以“颠”释“天”,乃《说文》之说,《释名》则将“天”释为“显”(“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讲记》这段话让读者易生错解。
以上舛误,有的显为手民之误,有的则与讲课有关。可以推想,作者在讲课时随口背诵,故出现差错,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错误正体现了作者腹笥之广。当然,在再版之时,修订上述讹误,《讲记》也将更加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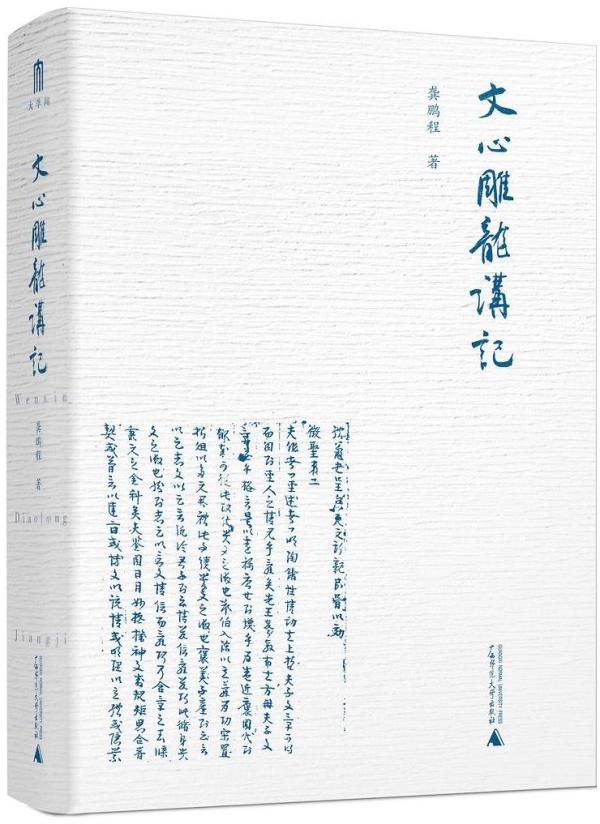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