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我,在庙合村七年制学校的一年级做了一名插班生。当时教室里没有桌凳,为了方便学生写字,大队部让泥水匠在教室里砌了数排土台子,外面裹上水泥。这就是村里学校最早的课桌。每排七八个学生共用,类似于宿舍的大通铺,凳子由学生从家里自带。当时班里学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最小的是我,只有六周岁;最大的是强娃,十八岁。差距整整十二岁,同一个属相。
每天,我们在土台子上写字,下课和放学的时候,满身是土,将身上的土拍拍,顿时尘土飞扬,但被尘土包裹的却是一张张笑嘻嘻的脸。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嫌谁脏。冬天的时候,因怕冷,有些同学竟然成个月不洗脸,以至于鼻梁上都有一层厚厚的垢痂,家长、老师也不管,同学们也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许多同学就这样腆着一张脏兮兮的脸,每天快活地在家和学校之间跑来跑去。
1979年秋,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这一年,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将教室里的土台子全部扒掉,摆上了课桌,但我的印象好像没有新课桌,全是旧的,不知是哪儿淘汰下来的,也没有凳子,但这已是巨大的进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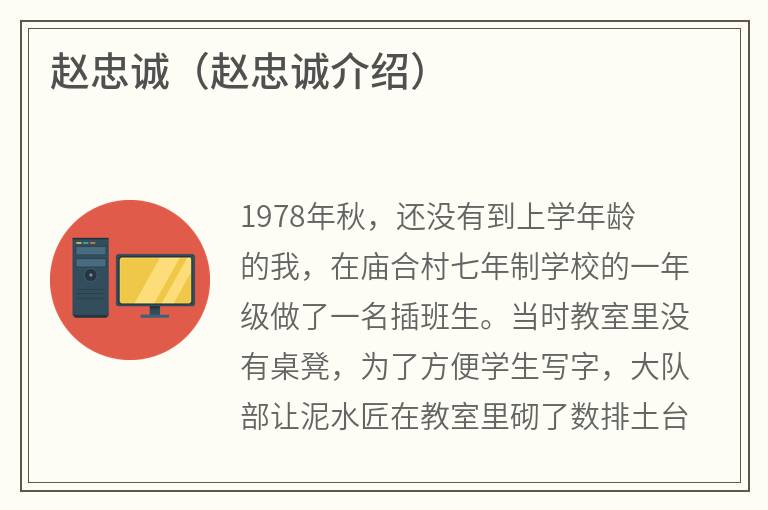
赵忠诚(赵忠诚介绍)
小学低年级留给我的印象似乎没有什么学习任务,整天在下课之后就是疯玩,玩法五花八门,有些玩法现在根本就没人玩,但当时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不必说放学之后在大自然里的无穷乐趣,单就在课中和课间,就有无尽的玩法在等着我们。冬天,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又八面漏风。同学们一个个冻得吸溜着鼻涕,响声此起彼伏,一个个鼻孔下面就好像有两条虫子在爬进爬出,没有纸张去揩,卫生纸在当时是奢侈品,讲究些的同学用手绢去揩,不讲究的同学就用衣袖去揩,时间长了,那衣袖就黑硬黑硬,油光光的。有时上了不到半节课,老师就问:“冷不冷?”学生大声齐呼:“冷!”于是,老师就让学生跺脚,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阵咚咚声,如同战鼓擂动。同时,教室的土地上就扬起一片尘土,伴随着的,还有同学们的一片嬉笑声。几分钟以后,麻木的脚慢慢恢复了知觉,又重新开始上课。下课的铃声刚响,同学们就冲出教室,女生常玩的游戏是跳绳,或一种叫跳马城的游戏;男生最常玩的游戏是“挤努努”,一个同学背靠墙壁,肩膀顶在凸出的砖柱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背靠墙壁用力挤向前一个同学,人越来越多,有时还喊着五花八门的号子,奋力向右挤,最后,靠近砖墙的那些同学就有人被挤得受不了了,哭着喊着从队伍里挣出来,一旦成功挣出,马上就喜笑颜开,又到队伍后面去挤别人。就这样不断有人被挤出来,又不断有新生力量在后面发力。短短几分钟,游戏就达到了高潮。刚才快被冻僵了的身体此时也恢复了热力,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以至到上课的时候,需要老师往教室里赶,这时,有些同学已汗流浃背了。
1980年前后,冬天特别寒冷,村里的涝池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用砖头也敲不开来。每天早上,踩着厚厚的霜花来到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啃着书包里那个冻的硬梆梆的馍馍。天寒,食物热量低,衣服又不大保暖,尽管同学们在早上不断活动,但到了早上最后一节课,一个个已是饥肠辘辘,盼着能早点放学回家吃饭,但那时连老师也没有手表,全校的时间基本依靠那只马蹄钟和校长的手表。早上最后一节课是最漫长的,没有计时工具似乎让人陷入一种无望的境地。这时,太阳不仅给了我们温暖,也给了我们灵感。不知是谁,在下课的铃声里,在同学们匆匆回家的脚步声中,在黑板下方用粉笔划出了阳光斜切下来的印迹。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钟表,尽管这只钟表随着太阳照射角度的不同需要不断调整,但我们毕竟不再处于一种无望的等待中了。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古代有一种计时工具叫日晷,原理竟和这如出一辙。
一年下来,黑板下方划满了密密麻麻的竖线,那是一年中太阳在每天同一时间留下的脚步,那是我们对时间的等待,也是青春年少时对时间的挥霍;是关于饥饿的记忆,也是希望和煎熬。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里开始流传一个画图的智力题:平面上两个套在一起的方框,四角分别用直线连起来,将此图用三笔画成,不能重复。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道趣味智力题,看起来简单易操作,于是,同学们的参与热情很高,但全校师生画了几年,依然无解。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一道无解的趣味题。
春节过后,杨柳的枝条一天天变绿了,直到有一天,有同学将变得柔软的杨柳枝条折下一段,轻轻地将树皮和木质部分扭分离,扔掉木质部分,只留下外面完整的树皮,将一端压扁捋顺,放在嘴边就能吹响。这是孩子们的春笛,也是春天到来的号角。
整个小学时代,在春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那个永远戴着棉帽子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每年的3月都会和我们相遇。这一个月,我们常常停课,扛着红旗,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大张旗鼓地去扫街道,或给孤寡老人、五保户打扫卫生。三月份的作文,似乎永远都是以好人好事为主题的《一件小事》。3月12日,还有一件必做不可的事,就是植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小学五年级(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今年就要毕业了,植下一棵树,作为你们的毕业纪念,等你们长大成人之后,回到母校,还可以看到你们栽的这棵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可能是老师的话极大地激励了我,我和同学赵忠诚选了一棵最大的槐树苗,共同栽了下去,非常用力,树坑挖得很深,水也浇得不少。此后,我就经常去看这棵树,但一天天过去了,树却没有发芽,快到夏天的时候,我才确信,这棵树根本就没有活,心里沮丧极了。我不知道,我的同学赵忠诚是否也去看过这棵没有成活的树苗;他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
然而,老师为我们勾画的愿景并没有实现,这片槐树林在不久之后,就不知因什么原因被铲除了,自然,那些成活了的树也没有摆脱噩运。
六一儿童节,全公社的学生都要到凭信初中去看文艺演出。这一天一早,全校师生打着红旗,唱着歌,一路浩浩荡荡地向凭信初中的大操场走去。但看了多年的演出,现在连一个节目也没有记住,能记住的,只是凭信初中的大操场里人山人海,彩旗招展。
六一儿童节过后,很快就到了收获麦子的日子。当时收麦时学校要放假两周,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有不同的勤工俭学任务。在生产队集体耕种时期,每个生产队的学生都由一个老师带领着拾麦。道路上、收获过的麦田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拾麦的学生。每天,学生将拾到的麦子缴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并登记重量,学校在收假之后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学生要予以奖励。包产到户之后,学校不再安排老师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大部分学生都在家里给家长帮工,家里劳动力多的学生才外出拾麦,但不管是帮工还是拾麦,学生都参与了劳动。一个收麦季过后,个个学生都晒黑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忽然对教学工作重视了起来,要求四五年级的学生必须上晚自习,当时,教室里还没有通电。于是,每天傍晚时分,同学们就从家里拿着五花八门的油灯来上自习了,有用墨水瓶做的,有用药瓶做的;燃料也是五花八门,有用菜油的,有用煤油的,有用柴油的,最糟糕的是用废弃的机油,点燃之后,一股黑烟扶摇而上。一间教室,二三十盏油灯,就是二三十盏污染源,一节晚自习下来,个个同学的鼻孔都变黑了。好在到五年级的时候,教室里就通电了,两个一百瓦的灯泡,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
我是1984年夏天小学毕业的,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也没有义务教育的说法,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考试,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没有考上初中,有的选择了补习,有的直接选择了停止学业,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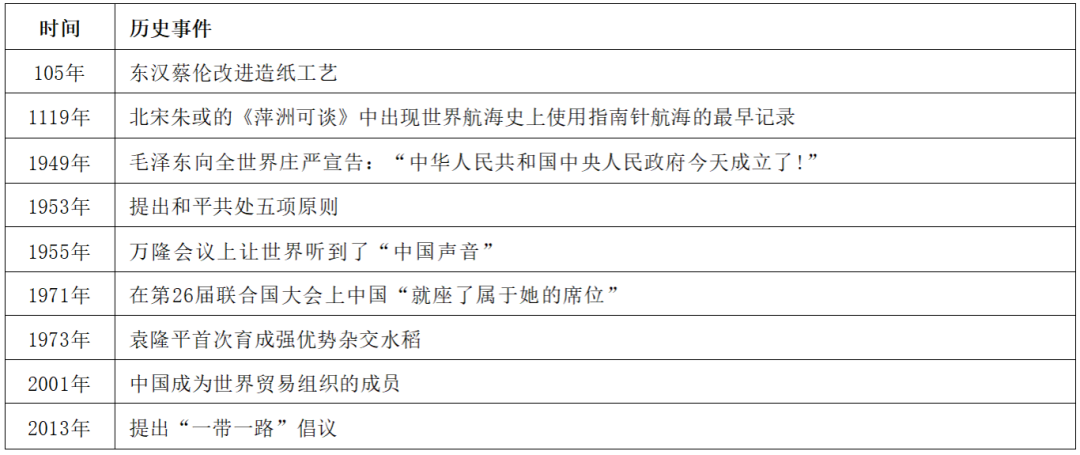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