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从新一期的《劳工:工人阶级历史研究》开始,朱莉·格林(Julie Greene)担任该杂志的主编。Maia Silber 在最近的 LAWCHA 时事通讯中采访了她。
您于199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新劳工史”的创始人之一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是什么让你进入这个领域?
我的根源最初是英国史和欧洲史。欧洲的劳工史研究非常活跃,我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和约翰·巴伯(John Barber)等学者,还师从扎拉·施泰纳(Zara Steiner)学习外交关系史。1930年代,我偶然开始研究威尔士矿工和共产党,并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我对劳工史的关注归功于这项研究,以及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左翼政治的兴趣。因此,当我离开剑桥大学时,我决定坚持与工人在一起,但从英国和欧洲转向美国劳工史。当时,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学领域的核心。我赞赏戴维·蒙哥马利从工人的角度重述美国历史的努力,我也赞赏该领域与当代政治和社会正义问题的联系方式。工人只是一种方式,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可以自下而上地做历史。耶鲁有些地方我不喜欢,但我喜欢和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以及他招募的其他学生一起工作:达纳·弗兰克(Dana Frank)、埃里克·阿内森(Eric Arnesen)、托尼·吉尔平(Toni Gilpin)、泰拉·亨特(Tera Hunter)、卡琳·夏皮罗(Karin Shapiro)、普里西拉·穆罗洛(Priscilla Murolo)。这是一群令人振奋的学生,他们都专注于劳动研究。
您是1998年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协会的创始联合主席之一。是什么促使您和同事们建立了这个组织,您的目标是什么?
LAWCHA 成立之初非常激动人心。我们的对话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我们(劳工史学家)没有任何中心组织。感觉就像一个巴尔干化的领域。有支持的支柱,但彼此分离。我们每年都在韦恩州立大学召开北美劳工史会议,我们还有丹·利布(Dan Leab)编辑多年的《劳工史》杂志。我们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将我们大家联系起来,开展对话,建立社区。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种直觉,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它不仅仅是工会、工业劳工和白人,也是一个与所有不同历史分支领域相联系的领域。大家一致认为,劳工史正处于紧张状态,我们需要让性别、性、种族和民族成为该学科的核心。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参与政治的组织,将历史与当代政治联系起来,倡导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劳工权利。因此,我们开始讨论并弄清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为所有这些制定一个章程。
从《劳工》杂志创刊伊始,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 90 年代末,丹·利布(Dan Leab)决定卸任后,我们接手了《劳动史》,我当时与莱昂·芬克(Leon Fink)合作。芬克成为了Labor History的编辑,而我则成为了他的评论编辑。此后不久,这份曾属于塔米曼协会的期刊被卖给了卖给了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出版社告诉莱昂,他们想要一年六期,而不是四期。他说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说,别担心,只要寄给我们四期,我们会重新包装成六期。莱昂说,我们不包装棉花。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走了,创建了Labor。那是 2003 年或 2004 年的事了,最终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Labor成为了与 LAWCHA 相关联的新期刊,而不是这家公司旗下的期刊。二十年来,我一直积极参与该期刊的工作。我担任了七年的审稿编辑,之后一直在编辑委员会任职。
那些年里,你们关于这个领域的对话对你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一位同事将我的第一本书《纯粹而简单的政治:美国劳工和政治行动主义联合会,1881-1917》(Pure and Simple Politics: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Political Activism, 1881-1917)描述为一部老式的劳工史,因为它关注了山姆·冈珀斯(Sam Gompers)和劳联(AFL)以及选举政治。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把劳工史和政治史联系起来。我很喜欢这个项目,但当我完成时,也许也是因为我之前专注于欧洲和英国史,我开始感到受到美国史的束缚。我想要一个更大的画布,考察更多样化的工人群体。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蒙哥马利曾敦促我们仔细思考非裔美国人和全球历史。因此,我受到一些人的影响,他们正在重新思考谁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劳工历史。在我读完第一本书后,一个灯泡熄灭了,如果我想走向全球和跨国,那么在巴拿马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项目可能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格林的第二本书是《运河建设者:在巴拿马运河上建立美国帝国》(The Canal Builders: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它不是回到欧洲史或英国史,而是试图超越美国国内史。当时有一种向跨国史的转变,让我很受启发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如果我一个人工作,肯定会更难完成《巴拿马》一书。美国和欧洲都有研究跨国问题的学者,比如Marcel van der Linden,为我的工作和兴趣提供了支持。
同时,您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在研究政治和国家方面也存在连续性。随着您进入跨国和全球背景,您对这些主题的态度是如何演变的?
我一直对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感兴趣,无论是推动改革,还是反抗,还是让自己适应国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当我转向一个更全球化的框架时,国家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核心,但国家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现在你谈论的是帝国主义,你也进入了一个公司(作为政治行为者)也非常重要的环境。并不是说它们不在国内历史中,而是当我广泛地思考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帝国的格局时,公司和资本主义显得非常重要——以及国家正在做些什么来支持公司或对抗它们。如果你看看波多黎各、牙买加或菲律宾,企业在那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必须对工人、国家、公司和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当地居民进行三角测量。
一方面,你们同龄人中的美国劳工历史学家在地理上突破了该领域的界限。另一方面,“新劳工史”带来的趋势之一是更加关注工人的经验和细粒度的社会历史。在推动地理广度和推动地方特殊性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
我看不出有太多的紧张感。多年来,偶尔会有人关注美国国史,他们似乎对跨国转向感到不舒服,好像这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各种研究,在地理上的所有尺度上。我把跨国和全球看作是提出新问题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有趣的融合,既有地方性又有全球性,例如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Shelton Stromquist)关于城市社会主义全球历史的著作Claiming the City。你可以在他的书中看到,要完全公正地对待各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将它们联系起来是多么复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研究,深入探讨观念是如何流动的,以及工人是如何相互沟通的。
回顾您创立 LAWCHA 以来的近二十年,该组织以及劳工史领域与您的早期目标相比处于什么位置?
我认为 LAWCHA 对劳工史学家来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深信它所做的一切,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它发展了一个社区,它帮助传播了对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领域的更广泛认识。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它已经开始接触非裔美国学者、拉丁裔学者、残疾学者和 LGBTQ 学者,了解他们的工作是劳工史的方式。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莱昂·利特瓦克(Leon Litwack)一起度过了一天,带他参观了我当时教书的博尔德,并带他去了书店,我记得他说他最喜欢的讲座总是关于劳动的,尤其是他会做的关于IWW的讲座。我刚刚在读他的一本了不起的书《心灵的烦恼》,我记得我对他说,你的书是关于劳动的,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劳工历史学家吗?他说,哦,不,我是非裔美国历史学家。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LAWCHA 面临的挑战,要引进像 Leon Litwack 这样的人,他的工作从根本上讲是关于阶级和劳动的。
为什么存在这种挑战?人们还只是认为劳工史只与白人男性产业工人有关吗?
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听过应该更了解的资深历史学家说,劳工史已经过时了,或者它只是工会的历史,或者它没有其他领域所具有的创造力。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开始减少。今天,美国各地的劳工议题都很热门,所以劳工史很热,而资本主义史的兴起等其他发展也为这个领域注入了活力。因此,偏见已经减少,但它仍然很强大。人们有一种感觉,即劳动史不是识别的“时髦方式”。像莱昂·利特瓦克(Leon Litwack)这样的人足够聪明,不会考虑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不时髦的,但我听过其他人这样说。我听说过很多年轻学者,他们去读研究生,想学习劳动史,听说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另辟蹊径。八年、十年甚至十五年前,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我认为现在也许事情正在开放。
这仅仅是一个形象问题,还是来自劳工历史学家进一步解决种族、性别等问题的真正需求?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阶级与其他历史动态或身份之间的关系。劳工史是一个不寻常的领域,因为从历史上看,它专注于一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社会运动之一,这意味着强调组织、工会和激进主义。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个领域的影响,以及它如何推动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经历时,这些界限就变得非常不稳定。我只想再说一遍,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以新的方式研究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家庭中的无薪工作,监狱工人,Uber司机或性工作者,都是工人阶级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劳工作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历史,它的愿望,它的战略,它的组织,现在和将来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着充分实现人权和劳工权利的斗争。
您能谈谈资本主义史对劳工史的影响吗?这两个领域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
它对劳工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历史领域的市场营销有时有点尴尬,因为它有时会与劳工对立起来。我曾在《劳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反思阶级的界限:劳动史与阶级和资本主义理论》]中写道。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现在的美国历史》(American History Now)中写道,资本主义历史源于劳工史令人窒息的感觉,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范式。但如果劳工史做得好,它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且一直如此。与此同时,对工人的强调可能会有些望远镜式,而资本主义史则促使劳工史学家思考他们的主题如何与更广泛的经济体系相联系,因此这对该领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今年7月,您接替莱昂·芬克(Leon Fink)担任《劳工》杂志的编辑。当您思考该领域的这些发展以及劳工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时,这将如何塑造您希望与期刊一起开展的工作?
二十年来,莱昂在领导该期刊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如此巨大。他为振兴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指导年轻学者并将新人带入这一领域。.我想继续该期刊的工作,但同时也要为这项工作带来新的想法。其中之一就是努力使期刊成为一个更具合作性的空间。莱昂当然与很多人合作过,他有一个很棒的团队——但在很多方面,他就是这个期刊本身。我想对编辑团队进行结构改革,这样我就有合作伙伴。我与申内特-加勒特-斯科特(Shennette Garrett-Scott)和杰西卡-威尔克森(Jessica Wilkerson)共同设立了高级副主编一职,我们三人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合作伙伴。我们会定期会面,讨论期刊的发展方向,并为我们的特刊集思广益,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的专长是跨国史、移民与帝国,而她们则对性别与性、非裔美国劳工史和资本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很高兴我们三人能够一起工作,同时还有总编辑帕特里克-迪克森(Patrick Dixon)以及我们在马里兰州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编辑助理(亚历克斯-邓菲(Alex Dunphy)和特里斯坦-威廉姆斯(Tristan Williams))。我很高兴 Vanessa May 将继续担任评论编辑。我还在努力与八人编辑委员会和我们的副主编举行更多的定期会议,并努力确保委员会本身能够反映该领域的全部能力。我们有专注于拉丁裔历史、非裔美国人历史、奴隶制、土著性、资本主义和 LGBTQ 历史的学者集中参与。我们正在用心确保期刊反映该领域的包容性愿景。
您最期待出版或希望未来出版的作品和类型有哪些?
我们对想探索的新领域有很多想法。新团队推出的第一期杂志实际上是以科学和劳动为主题的。是谁帮达尔文提行李箱,又是谁帮忙把东西装上比格尔号?谁在为科学工作付出劳动?这一期的负责人是塞斯·洛克曼、莉萨·罗伯茨和亚历山德拉·许。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此外还有莱昂·芬克牵头的关于社会民主的特刊,以及洛伦佐·科斯塔古塔客座编辑的关于全球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的特刊。接下来,我们将组织一次会议,探讨劳工史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一直致力于在非裔美国人历史学者和拉美裔历史学者之间建立联系。我们收到了一些关注拉美裔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的优秀投稿。这不会成为一期特刊,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三、四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劳工史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倾向于以 19 世纪晚期/20 世纪为重点,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早期的作品,以及更多关于其他劳工制度(如奴隶制和契约劳工)的作品。这类文章很难征集到,因为该期刊以 20 世纪的文章著称,所以学者们不会首先想到它。
您最近在《劳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高等教育的新自由化如何重塑了学者们的教学和研究条件。这也激发了校园劳工运动的复苏。杂志是如何应对这些趋势的?
在这方面,LAWCHA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希望期刊也能更多地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在过去的五到七年里,本组织一直在尽力支持学者。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在期刊和LAWCHA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共生的关系。去年春天,我们提出了期刊应开发一种组织模式的想法。我们希望鼓励LAWCHA的每一位成员将期刊视为自己的刊物,为我们撰稿,帮助我们宣传,并帮助我们传播该领域的广阔愿景。我们在组建编辑团队的过程中,确保非终身制学者和特遣队学者的声音成为核心,确保他们在编辑委员会和特约编辑中有自己的代表。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努力打破终身教职与非终身教职学者之间的壁垒。加布里埃尔·维南特是我们《当代事务》的副主编,他正在想办法在期刊的这一部分报道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征集论文,其中一个领域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危机。
高等教育的这些趋势是否影响了您的工作?
在我们位于马里兰州的校园里,学生们正在组织起来。他们远远领先于教师。马里兰州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没有集体谈判权,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斗争是说服立法机构给予我们这项基本权利。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参与校园斗争塑造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兴奋,加利福尼亚(2022年秋季有48,000名加州大学工人罢工)的斗争,它必须影响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我们在谈话开始时讨论了您在 "新劳动史 "高峰时期进入该领域的情况,以及您的团队如何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是否有一个短语或范式可以概括该领域的现状:"新劳动史"?这个领域是否过于宽广,无法用一种方式来定义?
我认为,这种宽泛性本身就会带来挑战。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例如,当我看到韩国或菲律宾的激进工人与殖民主义斗争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品,不仅关注他们的工作场所,还要关注他们的反殖民主义。但有些人会说,如果你不是在谈论工作,那真的还是劳动史吗?对我来说,我认为有趣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突破界限,尝试思考阶级如何运作。这也是我写那篇关于阶级界限的文章的原因。这就是我想说的前言,但回到你的问题,我不认为今天存在一种范式。这一领域已经变得非常广泛,在这一历史时刻,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工人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中右翼运动的根源,或工人在更不稳定和分裂的工作场所中的经历。 但在我看来,该领域有两个动态特别令人兴奋。其中一个我们已经谈过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在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塑我们的领域。 跨国转向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以及思考以下问题的新方法:谁是工人阶级,工人——白人、黑人、拉丁裔或亚裔美国人——如何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联系或不联系,全球关系带来的团结或紧张特权的来源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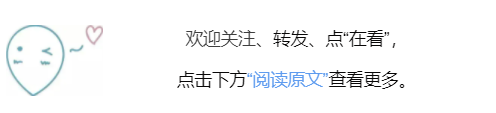
来源 | LAWCHA
翻译 |云舒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