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强调“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考古学的贡献作了全面肯定,为考古学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正是考古学所具有的“实证”特色,才使得它在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方面独具优势,显示出其在历史研究上的独特价值,而实证研究除了考古遗存(包括遗物和遗迹)的“自证”能力外,其价值挖掘离不开科技考古。可以说,科技考古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本体保存及展示也离不开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学科的作用。
近期,科技考古的价值在持续数月、由三星堆考古所带来的“考古热”中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专家解读,还是公众互动留言,这波“考古热”对“科技”在考古发掘和保护中的作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媒体在分析三星堆祭祀坑受到重视的原因时指出,公众被三星堆吸引,不仅在于祭祀坑出土的贴金青铜面具、青铜树、象牙、黄金权杖等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奇异文物,显示了古蜀国独特的文化面貌,也在于三星堆考古“跨越多个领域运用科学技术等划时代方法取得的考古成果”,“这一考古成果或有可能开创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未来”。无独有偶,在不久前揭晓的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显示出科技考古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入选“十大”或现场演示的20项考古成果,无论是在遗址探测与发掘中的遥感技术、数字技术,还是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古DNA、同位素科技分析,抑或是后期的文物保护,无不显示出科技考古的深度介入融合。科技考古所特有的实证研究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确确实实在“增强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正如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现场一位点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包括三星堆遗址考古和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所有成果,都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也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实物见证,科技考古在发现、分析、解读、展示这些文明成就方面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在此回顾科技考古的历程,让大家了解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及其重要性,同时认识我国科技考古所处的发展水平及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考古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学科交叉性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其中的实物资料既包括人工制品或通常所说的文物,也包括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的所谓“自然遗物”。这些实物反映着古人在技术、社会、信仰和环境利用开发等方面的信息,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但它们不会自证其价值,因而需要从不同角度采用跨学科手段,运用科技考古方法取得可以信赖的经过实证的信息,才能获知其意义,也才能使文物本体及其价值得以长久保存,世代传承。因为古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考古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北欧,一般是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说”的提出和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成熟为标志。不难发现,这些理论方法都是随着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因此这也决定了考古学与生俱来的学科交叉性质。如果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算起,今年恰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百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在山西、河南进行地矿资源考察,引发了仰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由此可见考古学与地质学联系之密切。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阳殷墟连续15次的考古发掘,发掘出以甲骨文、青铜器、大型建筑和王陵为代表的实物遗存,实证了殷商文明的发展水平和王朝性质,开启了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征程。考古学家利用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研究人类的体质,复原殷商时期的环境与生态,在科技考古尤其是生物考古、环境考古方面开启了有益尝试。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利比教授发明放射性碳素测年技术(简称碳14测年技术),将考古学家从经验主义的琐碎繁重的年代问题中解放出来,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存第一次有了绝对年代数据,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碳14测年技术被称为考古学上的第一次革命。2020年美国哈佛大学戴维·里奇教授根据近20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推动考古学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古DNA技术是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也预示着考古学新发展的到来。近年来,同位素分析、蛋白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上应用,成果出乎意料。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蚕丝蛋白的发现,把我国丝绸的历史提前到8000多年前,三星堆祭祀坑检测发现的蚕丝蛋白则让人知晓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对丝绸衣料的使用等。可以说,由于古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考古工作中遇到的对象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考古学在探测、发掘、分析、保护、利用各个阶段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科学技术的支持,科技考古是当代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50至60年代,由“二战”催生的航空技术、遥感技术和海洋探测技术被运用于考古探测,产生了航空考古、遥感考古和海洋(水下)考古等分支学科,以考古探测为核心的科技考古技术范围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随着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的解决,考古学对人工制品功能分析和“自然遗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基于科技的考古分析技术即科技考古应运而生,并产生了诸如环境考古、生物考古等专门考古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学继承优良传统,在重建古史的同时重视科技考古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用孢粉分析对古代环境进行复原,通过冶金考古方法对青铜器成分和工艺进行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科技考古得到初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碳14测年实验室的建立运行,第一次为我国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更多的绝对年代测年技术被应用到考古学中,支撑了全国范围内考古学年代序列和年代框架的构建,也成为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年代学支撑。
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的田野探测多依靠“洛阳铲”,通过打探孔的方式,借助经验知识形成对地下遗存的认知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遥感勘探技术、分析检测技术、计算机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学中。如运用航空遥感、高精度磁测、大地电场岩性探测和地球化学测汞等逐渐扩大探测的范围、提高探测的精度,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传统探测技术的结合中不断验证和改进新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揭示人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为目标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国际科技考古成熟技术在国内得到应用,日益成为国内学科发展的新态势,其在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青铜器起源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支撑起我国不同地区文明起源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对古代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和纺织品等人工制品的分析,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演变,而且推动了对上述人工制品的流通和消费研究,成为我们了解古代人群流动和技术交流等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学越来越强调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上的实证性研究,环境考古、生物考古、社会考古、经济考古等理论方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科技考古的支撑,考古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进一步多样化,几乎包括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各类遗存,发展出诸如人工制品成分分析、微观形态分析、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析技术,科技考古越来越成为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成为学科发展的新引擎。科技考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充分说明其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其本体所具有的脆弱性与不可再生性,需要人类社会共同呵护,以使其价值得以永续传承。在科技考古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利用现代科技对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共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号召各国投入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对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极大地推动了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也积累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等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文件的签署,对国际社会文物古迹保护与修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贡献,强调对文物物质属性的认知、对材料劣化(腐蚀、老化、朽坏)过程和机理的理解的“科学保护”理念逐渐被全球文物研究者广泛接受。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客观性、真实性和普遍适用性等优势,已经成为国际顶级文物保护机构的基本准则,并将这一研究思路应用于保护实践中。
随着新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文物保护科学与修复技术的进展突飞猛进。有机质文物(如漆木器、纺织品、纸本古籍等)、无机质文物(如金属、陶瓷、石骨蚌器、石刻等)分析检测深化了文物材质、工艺和劣化机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增进了文物价值的发掘和认知水平,提升了文化遗产价值保护和传承的科学理念与技术能力,多学科融合下的文物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工作模式已基本形成,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以石窟寺保护为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石窟寺保护理念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多学科融合的保护科技支撑模式和技术体系基本成熟;一些石窟寺重大保护工作及其成果在我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提升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水平;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纵观国际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科学与技术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一方面,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考古资料方面日益重视以科技为手段的实证研究,使得考古学在复原人们赖以生存的古代生态环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的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利用科技手段加强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日益成为国际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国内考古学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考古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术,许多是由国际同行率先发明、应用的,我国的文物保护还有大量基础理论和技术难题亟待攻克,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专业学者人数较少,专业人员缺口巨大,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手段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我国考古工作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更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这为我国考古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科技考古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作者:方辉,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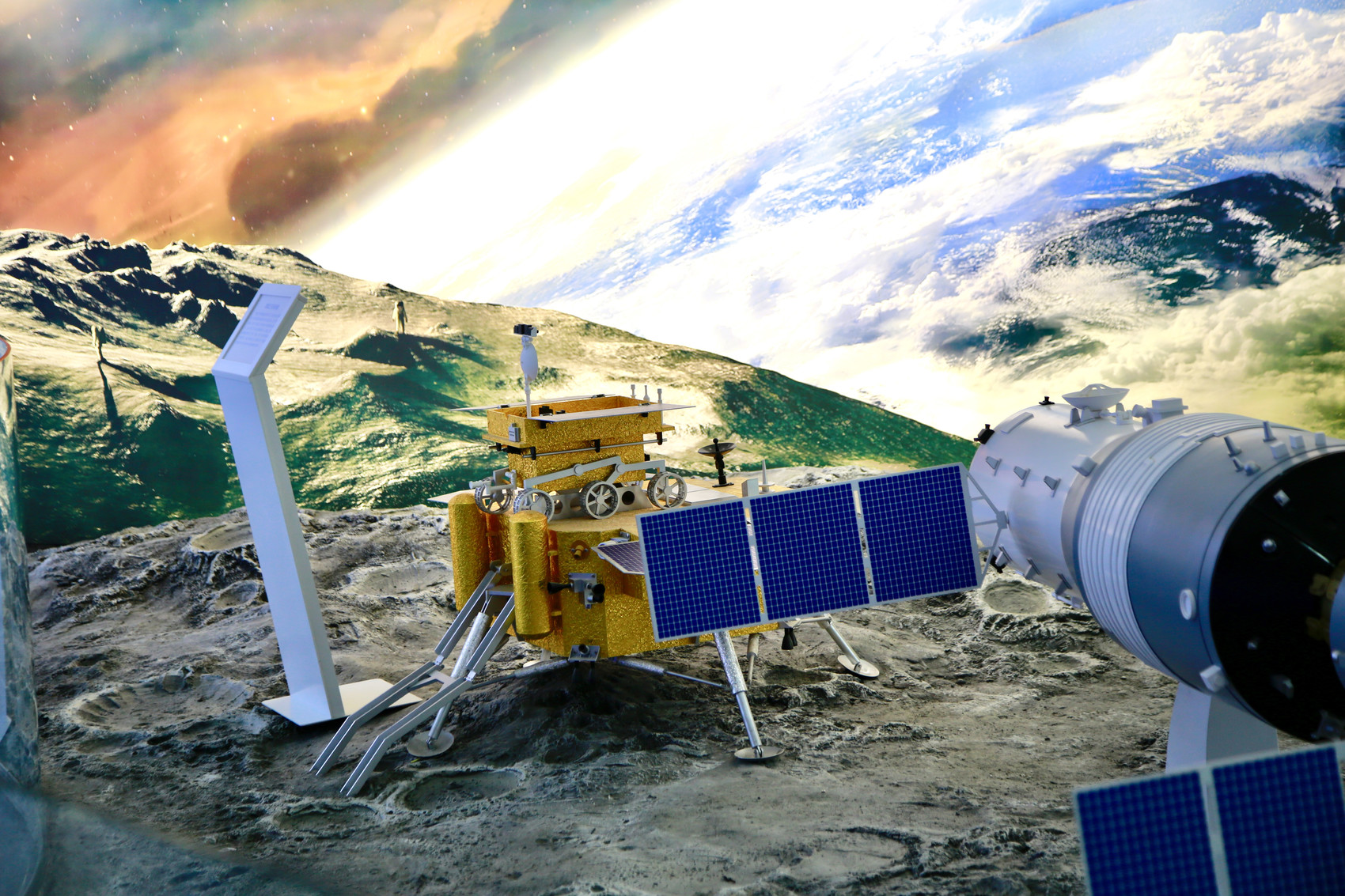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