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儿童史研究表面上看似沉寂,实际上已经伴随整个历史学研究范式转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本文聚焦于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边界”(border),讨论它为儿童史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可能。文章指明“边界”是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它既指作为儿童身体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有形的物质边界(比如年龄的划分),又指在全球交往中的跨境行动。这个概念的引入,扩大了史家的问题意识,将以往一些很少受到关注的新课题带入研究实践中,深刻地改变了最近三十年来儿童史研究的面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认知。
关键词:“边界”儿童史 少女研究 历史叙事 全球史
一般认为,儿童史研究发轫于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ès)1960年出版的《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英译本名《儿童的世纪》),20世纪60~80年代是其发展的一个高峰。对此,俞金尧教授和台湾学者陈贞臻已经做过系统的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儿童史研究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不过,这篇短文想要指出,这绝不代表这一研究领域的衰落。在表面上的沉寂之下,它和整个历史学研究一样,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和整个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广泛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以解释过去。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第一代儿童史家的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等人,强调儿童概念、亲子关系发展的“现代”性,特别偏好从经济因素、社会阶级和生产关系角度理解历史上儿童的角色,比如,儿童是怎样作为劳动力参与到家庭、社群乃至更大的社会生活中的。七八十年代以降,史家更加关注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因素,更强调从意义角度阐释历史。这股潮流后来被命名为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给儿童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研究路径,史家从关注何谓“儿童本性”,转变为关注“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童年”概念会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条件而有所不同,进而,儿童也在阶级再生产、文化转型、政治稳定的维护等方面扮演核心角色。伴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兴起,90年代以后,儿童史研究突破了过去隶属于家庭史、妇女史的藩篱,更加密切地与这些新的理论范式交织在一起。
本文聚焦于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边界”(border),讨论它为儿童史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边界”,是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它既指作为儿童身体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有形的物质边界(比如年龄的划分),又指在全球交往中的跨境行动。这个概念的引入,扩大了史家的问题意识,将以往一些很少受到关注的新课题带入研究实践中,深刻地改变了最近三十年来儿童史研究的面貌。
一般认为,“儿童”和“童年”都是建立在人的年龄阶段划分基础上的概念。1989年发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在法律上,儿童权利适用于新生儿和18岁之间的人。”这一标准被世界各国采纳,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并被包括大多数儿童史家在内的学者沿用。它主要依据的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尺度,看起来具有极强的普适性。然而,事实上,这个0~18岁的“公认”标准只是一个当代的概念。回到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判定儿童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
阿利埃斯(Philipe Ariès)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回顾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中的“儿童”概念。他指出,虽然一直存在年龄划分的意识,但在16世纪以前,儿童一直深度卷入成年人的生活,因而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童年”。从16、17世纪开始,孩子被置于家庭关注的中心。到18、19世纪,新的核心家庭逐渐形成,成员之间享受了更为亲密的关系,父母在情感上体会到,孩子是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也开始为他们考虑未来。由此,人们重新审视了作为生命阶段的“童年”与“成年”的区分,把“童年”视为生命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一环,“儿童”也被看作和成人不同的两个“社群”。这样,真正的“童年”才诞生了。
阿利埃斯的结论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学者纷纷投入相关研究,试图证明,“儿童”和“童年”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近代的发明,而是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其实,阿利埃斯并没有否认,前近代社会中存在“儿童”概念,他所强调的只是,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把童年看作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认为儿童需要得到和成人不同的对待,近代意义上的“童年”是从16世纪之后才发轫的。换言之,他是从社会文化意义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理学角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因此,阿利埃斯的反驳者对阿利埃斯的的研究不无误解。不过,有趣的是,也正是这些误解启发后继学者从生命分期角度,对一系列有关问题展开了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儿童史学科的成长。
按照阿利埃斯的描述,在近代之前的西方社会,人们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来界定生命周期的,直到16世纪以后,生理“年龄”才成为判断童年阶段的主要标准。这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并不只是把童年看作一个生理阶段,而是掺杂着不少社会因素。在对阿利埃斯范式的各种争论中,怎样界定“童年”也一直是一个基础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尤其是非西方文化中儿童史研究的展开,史家也逐渐达成一个共识:童年不是一个静等着“被发现”、“不受时间影响的分类”,它是社会文化的建构,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条件而有不同的“童年”概念。比如,在英国,直到今天,真正的成人年龄还被认定为21岁,18岁只不过是部分成年而已。
童年概念的多样性使得新生代儿童史家的目光从关注何谓“儿童本性”,转变为关注“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指出,“儿童”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儿童“像什么”和“是什么”的观念表象,及成人“为了”(for)儿童的生活所做的一切思考。
当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对传统的童年概念提出了挑战。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儿童的智力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彰显其智力标准的逻辑、语言能力七八岁时发展完善,这一看法得到早期心理学的印证。最近的儿童史研究则吸收了新的神经心理学成果,认为儿童的智力发展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更早,有些孩子在三岁时就已经具备完善的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样看来,过去区分儿童、青少年与成年边界的标准显得过于简单,该怎样重新定义和划分生命阶段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总之,随着儿童史和相关学科的推进,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年龄”是认识和理解生命过程、成长和“长成”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有生物学因素,也蕴含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个体的“年龄经验”由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形塑,也深刻地反映着这些相互交织的力量。回顾过去六十年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年龄的讨论,通常与生育、人口等“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90年代后期,年龄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学者们越发意识到,理解“年龄”对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具有深刻意义。这样就促使史家将“童年”等与年龄有关的概念放在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中思考。
近年来,这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庞德威(David M.Pomfret)的《帝国与青少年》。他在此书中提出,年龄是现代性叙事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年龄范畴,注意其与其他身份范畴的交叉作用,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会深化我们对许多传统课题的认知。为此,他把目光聚焦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中期受到英法殖民的四个东南亚城市,把年龄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讨论了青少年群体是怎样和殖民行动联系起来的。
殖民当局认为,亚洲热带地区(tropicality)的湿热环境,会使人的身体变得脆弱,因而规定,选拔前往殖民地任职的管理职员要优先考虑身强力壮的青年。为此,一批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派往殖民地任职。就这样,这一批在母国中还被当作“孩子”的人,来到殖民地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管理者。他们怎样适应这种角色转变,成了一个有趣的议题。在这里,随着地区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成人和未成年人的“固有”边界也被重新划分。同时,这也带来了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和当地人民的通婚问题,由此产生了不少混血儿。对于这些混血儿童,殖民政府一方面把他们视为殖民社区中一股不平衡和不稳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儿童的可塑性,因而通常会及早介入混血儿的生活,以确保他们的成长向着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方向发展,其中就包括将适龄儿童(一般是六七岁)送回宗主国接受教育。就这样,“年龄”问题再一次出现,成为殖民管理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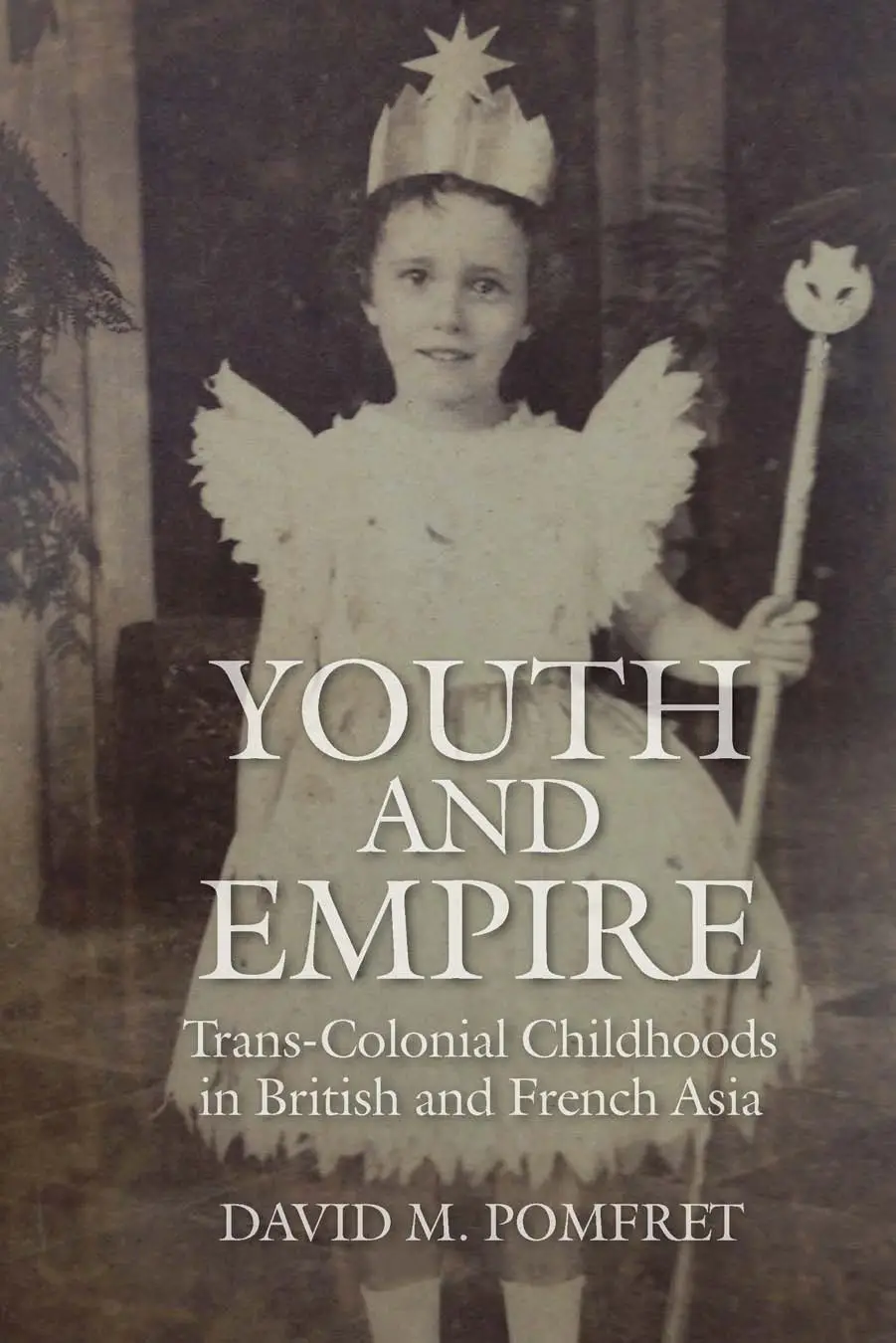
David Pomfret, Youth and Empi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庞德威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殖民地文化和“年龄”在帝国建设中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殖民历史,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以往那些理所当然的年龄归类范畴,如“年轻人”和“成年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自然”。我们必须将年龄和生命周期看作流动的范畴,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情境的多元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年龄的思考为儿童史和儿童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探索方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少女研究”(Girls Studies)。早在1976年,史家安吉拉·麦克罗宾(Angela McRobbie)和詹妮·嘎波(Jenny Garber)就曾撰文指出少女及少女文化的独特性,强调青少年亚文化研究需重视少女群体。不过,这一领域依然保持了约2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关少女、少女时期及少女文化的研究成果和书籍才显著增多。这种变化的出现,除了得力于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广泛开展,更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儿童史家对年龄的持续深入思考。
从字面看,女性研究(Women Studies)和少女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年龄差异。从成人中心视角(adult-centered perspective)出发,“少女”被认为成人的“他者”,“少女研究”也就尴尬地成为“女性研究”的“他者”。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就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妇女史与性别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将探索目光扩展到了包括妓女、未婚妈妈、女性上班族等在内的女性人群,但少女群体并不在其中。由于学者们缺乏对年龄范畴的深刻理解,少女研究长期得不到成人的郑重对待,而少女研究的出现,代表着史家迈出成人中心视角,对于年龄的深刻意义有了更为敏锐的意识。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汀·亚历山大(Kristine Alexander)的《导向现代女孩》一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和文化领域经历剧烈的变革。受到“女性获得选举权”“摩登女郎”等社会议题的影响,英国兴起了“女孩指导运动”,政府希望通过干预塑造理想的“现代女孩”。这一运动迅速扩散,在两次大战之间,吸引了40多个国家100多万成员加入。克里斯汀聚焦于参加“女孩指导运动”的少女群体,深入分析了这一运动在英帝国的英格兰、加拿大、印度三地塑造年轻女孩的具体方式,以及少女们对此运动的理解和回应。她将少女群体置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广阔天地中来审视,不但加深了我们对少女群体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广阔天地中来审视,不但加深了我们对少女群体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与国际主义等问题的深入理解。
如今,有关少女的历史文献资料(如文字记录、口述历史、实体物品)、少女的机构组织、少女群体的现实经验等课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跨学科的专题性少女研究也越来越包罗万象,议题更加广泛和重要,如少女和新自由主义、黑人少女研究、媒介性少女研究、酷儿(Queer)少女研究、跨国/全球性少女研究、少女与行动障碍、少女与女权政治等。2008年,学术期刊《少女研究:跨学科》( Girlhood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正式出版,这是该领域第一份跨学科学术刊物,意味着少女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已经凸显出来,以少女和少女群体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成为儿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次生领域。
年龄研究视角的引入以及它和诸多史学研究议题的结合,不但大大开拓了史家的视野,使我们对各种历史现象的了解更为深入和细致,也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体会到,包括童年在内的生命周期阶段区分标准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很难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框架。这种多样性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也与不同的地区和文化有关。这样,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边界”的空间维度。
除了年龄的划分外,“边界”一词更为常见的用法是与“边境”“区域”“国境”等空间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庞德威的著作中就同时含有这两种不同的边界概念:正是在殖民地的特定情景中,西方社会中固有的年龄区分标准才得以松动,年龄的跨界和空间的跨境不但同时发生,而且存有因果性的逻辑关联。这里牵涉近三十年儿童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儿童与空间边界联系起来,试图在一个跨国家和全球化的情境中关注儿童的社会流动和国际流动。
由阿利埃斯奠基的儿童史研究,最先在法、美、英诸国开展,史家与史家关注的对象、话题也限于这些国家。不久,儿童史研究开始迅速进入其他欧美国家史家的视野:加拿大的施奈尔(R.L.Schnell)、俄罗斯的大卫·兰瑟尔(David Ransel)、德国的玛丽·朱·梅尼斯(Mary Jo Maynes)和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意大利的马切洛·佛劳罗斯(Marcello Flores)和玛丽·吉本(Mary Gibson)等,他们对于所在国儿童史的探索备受瞩目。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家把注意力转向非西方世界,日本、印度、斯洛文尼亚、南非、巴西等国家的儿童史研究也日渐兴起。
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史家所关怀的问题当然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关,但也促使儿童史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而随着相关成果逐渐增多,一个跨国性的视野也逐渐凸显。
跨国儿童史研究首先体现为对儿童迁移和流动的关注,而这又通常都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比如前述庞德威的著作)、世界大战和全球化等近现代史上的核心事件有关。身处历史变局之中的人们,因为追逐梦想或躲避灾难,有时主动,有时被迫,背井离乡,前往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遇到了什么,如何学会适应一个崭新的环境,怎样和新的世界互动,等等,都受到了史家的关注。然而,一如既往地,这些关注都是从成人视角出发的,儿童群体及其经历常常被人忽视。儿童史研究者则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把目光投向越境儿童,讨论他们在跨越地理空间界线中的个体经验,以及其中交织的身份、族群认同和知识、信仰、情感的传播和交互作用,等等。
通过这些考察,史家试图从跨时代的视角重新思考并审视“亲密政治”如何经常与儿童发生联系、儿童的流动如何与地缘政治的设想和民族国家的巩固交织在一起,从而弥补了以往人们对近代史上重大事件认知中的成人视角的不足,呈现了更为丰富和细腻的历史事实,亦使这些老的课题释放出新的阐释空间。比如,休·莫里森(Hugh Morrison)研究了前往新西兰的英国殖民者中儿童的宗教经验,认为他们的宗教教育实际上是一项情感教育事业而非教义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另外,通过把儿童放在一个与异文化相遇的情境中,儿童史家一直追求把儿童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目标,也获得了更好的实践机会。比如,凯瑟琳·汪萨瑟(Kathleen Vongsathorn)发现,乌干达的英国传教士在对麻风病儿童救治过程中,培育出土著儿童的幸福、感恩观念,而相应地,土著儿童也在此过程中习得了表演此类观念的技巧,以获取传教士们的偏爱。
在两次大战之间,为了避免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欧洲社会对犹太儿童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迁移。儿童史家深入研究了这一历史过程及它所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其中,罗伊·考茨拉夫斯基(Roy Kozlovsky)的成果最为突出。他引入离散(diaspora)和流动的视角,以英国为重点,考察了一系列为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儿童开发的新建筑和空间环境。在详细探究建筑师、儿童专家和决策者的意愿、方法的同时,他突出了作为空间使用者的儿童如何接受、使用这些空间,对之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情感庇护所”的概念,将儿童空间的定义,由成人“为儿童”所建的空间,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的空间,彰显出以儿童为主体的研究新取向。
在跨国儿童史研究的基础上,有些史家提出了“全球儿童史”的概念。目前,这基本上还处在一个构想阶段,不过,随着儿童史研究的日渐兴盛和全球史研究更加成熟,“全球儿童史”的地平线也逐渐显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史家关注儿童和童年的全球联系,讨论生命的共有情形、观念与技术的散播、各社会之间的文化相遇对儿童与童年的影响,以及儿童怎样回应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实践看,以下这些论题备受关注:儿童迁移的历史与当代政治,以及不同时期和地域规范儿童移动的管理层面的基本话语,即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童年体制”,如果有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儿童和青少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关于童年和青少年期的理念如何被制度化,从而影响到政治运作和国家定义;童年和青少年期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实物以及亲密关系等因素得到塑造的;“年幼/年轻”的现代概念和经验是如何通过跨界的移动和交流而产生的;等等。
跨国儿童史研究也有效地利用了口述史方法。如朱利安·布劳尔(Juliane Brauer)对战后苏联占领期间德国人“父职”的实践与变化的研究,斯瓦皮纳·巴纳杰(Swapna M.Banerjee)对孟加拉被占期间儿童史的研究,均建立在口述史的基础上。对跨国儿童史研究来说,口述方法的引入,不仅能使历史细节的呈现更为多元,也有助于历史感知视角更具丰富性。当然,在接受口述访谈时,被访谈对象早已成年,他们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成人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口述本身只是一种诠释,而不是对童年经验的直接描述。不过,这并不只是儿童史研究遇到的特殊情况,而是整个口述史研究都会遇到的问题。事实上,这些访谈弥补了传统史料的匮乏,只要我们善加鉴别、分析和利用,对于复原特定时期以儿童为主体的历史经历,还是弥足珍贵的。
本文以“边界”这个概念为例,探讨了最近三十年来儿童史研究的一些新动向,挂一漏万之处自然难免。当然,本文的目的也不是要对这三十年的儿童史研究做一个全面回顾。事实上,即使只是通过这些有限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史研究并没有停滞,反而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儿童史家借鉴历史学其他领域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努力拓展理论视野,开发了不少新的课题。通过这些工作,儿童史家已经不再只是以成人历史补充者的身份自居,而是以自己独特的学术敏感性,积极介入传统的重大历史课题,从儿童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认知。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儿童是人类社会一个当之无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一步表明,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交流对话,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互惠之举。
本文转自王超、信美利:《欧美史研究(第3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18-328页,特此致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