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观念与社会”丛书 ——
〔法〕让•伊波利特 著
张尧均 译
ISBN 978-7-100-22787-2
定价:58.00元
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版

作译者简介
本书作者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系法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著作的翻译者和解释者,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
本书译者张尧均,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同济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现象学和政治思想史。
内容简介
本书虽然名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但实际上它既与黑格尔著名的《历史哲学》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对黑格尔庞大思想体系中的“历史哲学”的专门研究。从其内容来看,它倒更像是对黑格尔思想(当然是有关历史和政治的思想)的发生史或形成史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侧重的是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即《精神现象学》产生之前的思想。只在最后一章,它才较多地涉及了黑格尔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尤其是与《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关思想的关联。如果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建立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那么伊波利特的这本小书则阐述了黑格尔通达这种历史哲学的道路——一条漫长的“教化之路”。
目录(滑动阅读)
引言 黑格尔的观念论
第一章 民族精神
第二章 苦恼意识的最初形式:古代世界与基督教的自由
第三章 理性与历史:实定性与命运的观念
第一节 实定性的观念
第二节 命运的观念
第四章 黑格尔的第一个法哲学
第一节 黑格尔的一般立场:对独断论经验主义的批判
第二节 对康德与费希特的观念论实践哲学的批判
第三节 有机共同体的理想
第五章 现代世界:国家与个体
附录一 从最近的研究看黑格尔的早期作品
附录二 法权状态
附录三 《法哲学原理》序
附录四 理性的狡计与黑格尔的历史

译者序言(节选)
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出版于1948年。如果单看书名,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对黑格尔著名的《历史哲学》一书的导论,或至少是对该书的研究;但实际上它与《历史哲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伊波利特在文中甚至没有提到过《历史哲学》。本书也不是对黑格尔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历史哲学”这一方面的专门研究,没有探讨(比如说)像历史的动力、发展线索、目的论等历史哲学所应有的问题。从其内容来看,它倒更像是一个对黑格尔思想(当然是有关历史和政治的思想)的发生史或形成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本书侧重的是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即《精神现象学》产生之前的思想。只在最后一章,它才较多地涉及了黑格尔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尤其是与《法哲学原理》中相关思想的关联。如果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建立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那么伊波利特的这本小书则阐述了黑格尔通达这种历史哲学的道路——一条漫长的“教化之路”。正如伊波利特所指出的,在黑格尔“透过诸个别的民族精神的特殊环节而把历史哲学设想为世界精神的发展之前,应该有一段漫长的哲学发展时期”(26,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而这本小书正是对这一“漫长的哲学发展时期”的追溯。事实上,如伊波利特所说,《精神现象学》之所以特别令我们感兴趣,只是因为它“正好处在它所重新思考的早期著作和它所宣告的未来体系之间。我们在其中发现了黑格尔的整个‘教化之路’:在通达哲学之前他本人所遵循的道路,以及为了使这种活生生的经验进入一个严格的反思框架所付出的逻辑学家的卓绝努力”(15)。这种转变,借用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的话来说,就是从“泛悲剧主义”向“泛逻辑主义”的转变——伊波利特承认他这本小书正是从这个观点得到了启示,但与格洛克纳将这两者对立起来不同,他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一致。然而,问题在于,当“活生生的经验”进入一个“严格的反思框架”时,它还能保持其原有的那种活力吗?由这种活的经验所生成的历史性与附属于宏大思辨逻辑体系之下的历史哲学,具有同样的“历史”含义吗?

一
与“泛悲剧主义”和“泛逻辑主义”的区别相对应的,是伊波利特在“历史性”与“历史”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的区别。在此,历史指的是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大历史,一种由绝对精神在时间中展开自身而形成的诸个别环节,它体现在黑格尔一再引用的席勒的这句名言中:“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审判。”而历史性(historicité)指的则是特殊的历史现象及这种历史现象对当下所具有的意义。对青年黑格尔来说,他所关注的历史性问题就是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问题。
伊波利特指出,历史是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与谢林一开始就关注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不同,青年黑格尔感兴趣的是各种具体的经验性问题,特别是民族和宗教的历史。当然,他的着眼点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精神。他想要探索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的精神,一种与历史不可分割的精神的生命。相较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在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笔记中只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他似乎只是为了揭示这种精神的生命,才不得不借助哲学的概念,并在感到这些概念的不足时,迫使自己去锻造一些更适合表达人的历史生命和历史实存的新概念。正是对民族精神的最初洞见把他引向了对历史发展的思考,直至最后形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就此而言,黑格尔的思想是从历史上升到哲学的,在拥有一种体系性的历史哲学之前,他先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考。是历史性的经验本身引导着他去寻求一种关于这种经验的哲学表达,因此,这是一种历史哲学之前的历史哲学,或者说,这是一种关于“历史性”的历史哲学。
这种“历史性”思考的核心就是格洛克纳所说的“泛悲剧主义”,一种悲剧的世界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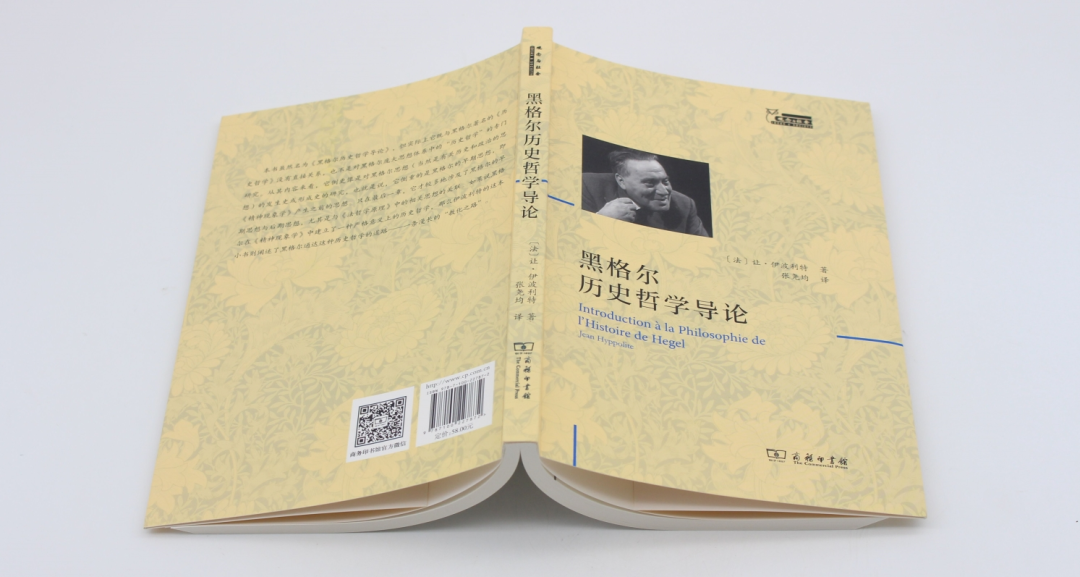
二
……泛悲剧主义是一种尚未进入意识,并因此而呈现为神秘的异己力量的一般命运;而泛逻辑主义则是一种被意识到,进而被理解和被认同的一般命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特殊命运到一般命运的上升正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运动,这也意味着命运已被把握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波利特说,泛悲剧主义是所谓的辩证法的原初形式;辩证法只是以逻辑的术语传达了泛悲剧主义的世界景观。(103,104)而就这种辩证法将泛悲剧主义所隐含的超越维度拉回到内在而言,它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景观的一种全新改变。笼罩在世界之上的那种神秘的命运力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国家力量。正如黑格尔后来借拿破仑的语言所说的,在现代,政治已经取代宗教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命运(参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而国家甚至就是在地上行进的神本身(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9页)。
就黑格尔自身的思想发展而言,这也意味着一种决定性的转折,即从早先对特殊的历史现象(尤其是民族和宗教现象)的研究转向对哲学体系的追求。在1800年,黑格尔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体系的需求,而他所尝试建构的最早体系似乎就是从耶稣的命运中得到了启发。在如今遗留下来的1800年的《体系残篇》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探讨爱的问题,但就其总的倾向来看,它似乎是更接近于这种爱的综合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完成,这或许是出于事情的必然。在研究耶稣和基督教的命运时,黑格尔就已经看到,爱的悲剧性命运就在于它不能无限地扩展自己而不丧失其应有的深度和力量。而从我们在此所思考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爱的辩证法的局限更在于,它不能说明历史现象,不能说明我们前面提到的耶稣的两种选择中的第一种,即现实政治的冲突和抗争。但从1800年以后,黑格尔事实上已越来越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他的耶拿体系就是从人的这种历史实存的悲剧出发建构起来的。这也是伊波利特的书的最后两章所要阐述的内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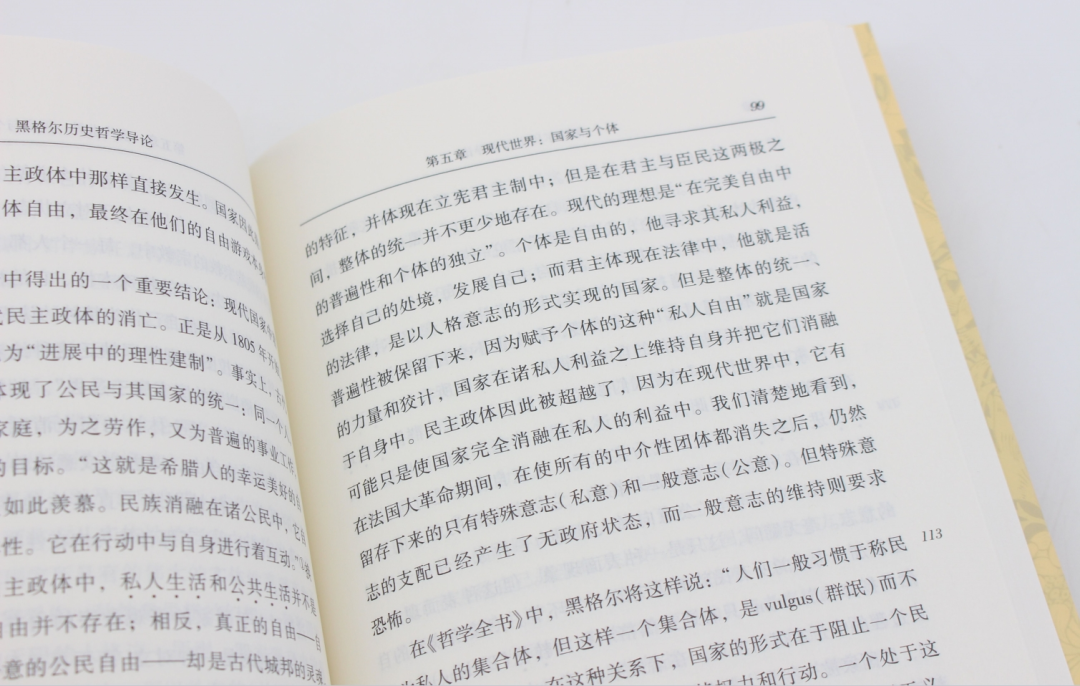
三
总的说来,伊波利特的这本小书并不复杂,而是颇为简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某种“暧昧性”。就像我们开头所说,这本书更像是对黑格尔的历史政治思想之形成史的梳理,他却用了“历史哲学导论”这样一个并不完全适当的书名。他借用格洛克纳的说法,把黑格尔的思想描述为从“泛悲剧主义”向“泛逻辑主义”的转变(我们前面已大致勾勒了这种转向的内在理路),但从这种描述中,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在思想与历史之间的某种奇特呼应。也就是说,从泛悲剧主义向泛逻辑主义的转变不仅仅是黑格尔个人思想的一种发展逻辑,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发生逻辑:先是一种自由融洽的理想状态(希腊城邦),随后是一种失去乐园的撕裂和被抛状态,人有了苦恼意识,感到自己受制于某种神秘的命运,直到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这种命运并不是特别地专属于他的,而是普遍的命运,甚至连绝对者也不能抽身于外。由此,命运就失去了其抽象的、超越的特征,而成了围绕着我们的一种具体的存在和力量,它显现为国家、他人,甚至就是我们自身。人与命运的关系就是人与国家、自我与他人,甚至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于是,最终的自由就是要达成人与国家、自我与他人乃至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与和谐。由此,历史的发生逻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句话:历史是自由的实现;自由是“人与其命运的一种和解;而命运就是作为其表达的历史”(123)。
在历史、自由和命运之间似乎绕成了一个奇特的圆圈;而圆圈,在黑格尔看来,正是思想之体系的特征。因此,是思想自身的运动建立了这种内在的联系(泛逻辑主义);然而,思想其实又不仅仅是它自身,而是(借用《法哲学原理》中的表述)“把握在思想(或概念)中的它的时代(或时间、经验)”,亦即被纳入“严格的反思框架”之中的“活的经验”(悲剧因素)。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这种转化中,经验还保有其原有的活力吗?
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有不需要某种框架而能独立呈现的经验吗?似乎没有,任何经验都有某种超经验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在康德所说的任何经验都需要一种先天形式和范畴才成其为经验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就像我们前面在讲到黑格尔的“历史性”经验时所说的,那些无法为个人掌控或把握的悲剧性经验就呈现出命运的结构。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所说:“现象就是生成与毁灭,但是生成与毁灭本身却并不生成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这种“并不生成毁灭”的“生成与毁灭本身”,当我们不理解它时就是命运,而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它,把它引向表达、引向概念时,它就成了通向意义和真理的一种逻辑运动。关键在于把沉默的经验引向关于它的意义的纯粹表达。但表达不仅仅是呈现经验的意义内涵,也是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意义结构。只要经验的意义没有穷尽(事实上也不可能穷尽),那么,从经验向语言的这种生成和转化原则上也是不会穷尽的。或许,这才是伊波利特所说的“暧昧性”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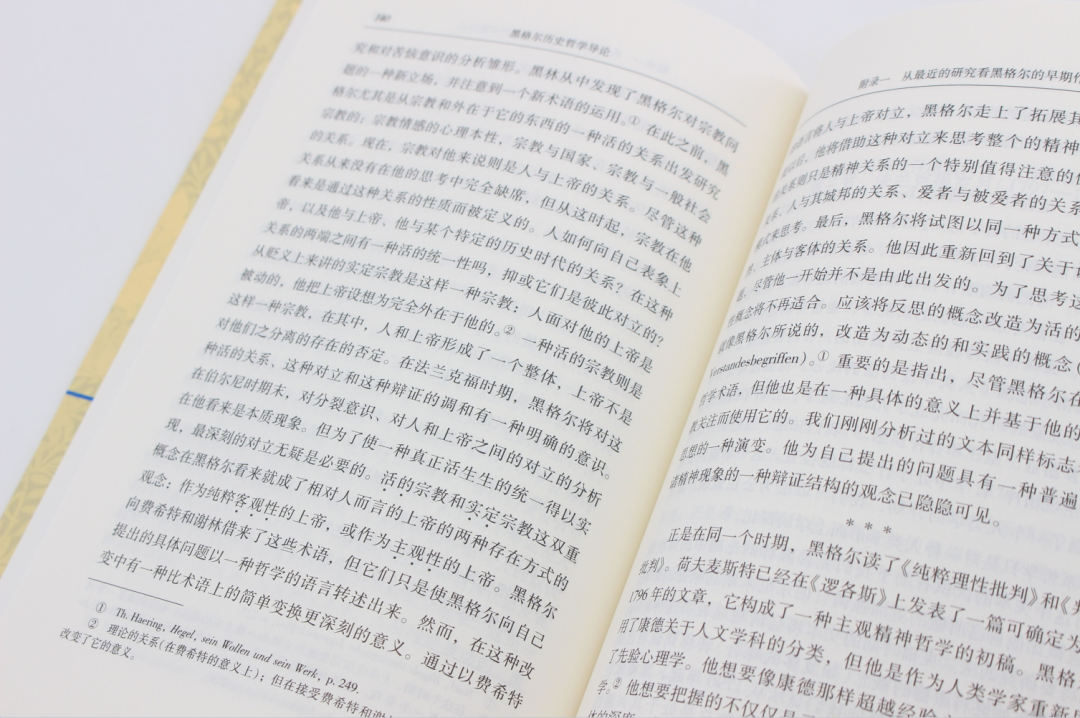

“观念与社会”丛书已出书目

《形而上学论》
〔英〕柯林伍德 著;段保良 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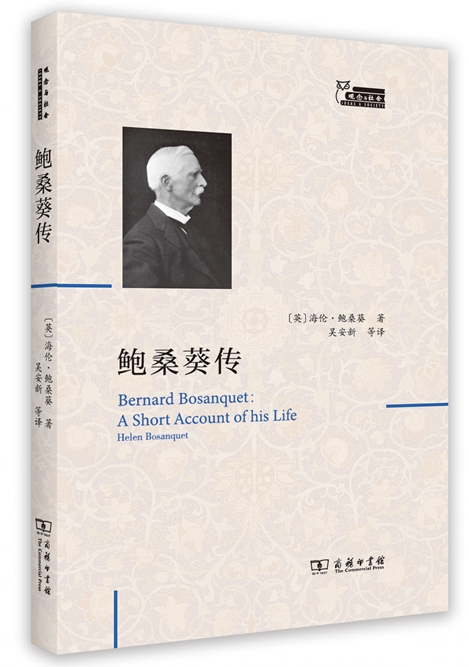
《鲍桑葵传》
〔英〕海伦·鲍桑葵 著;吴安新 等译
商务印书馆2023年9月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