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李硕(章静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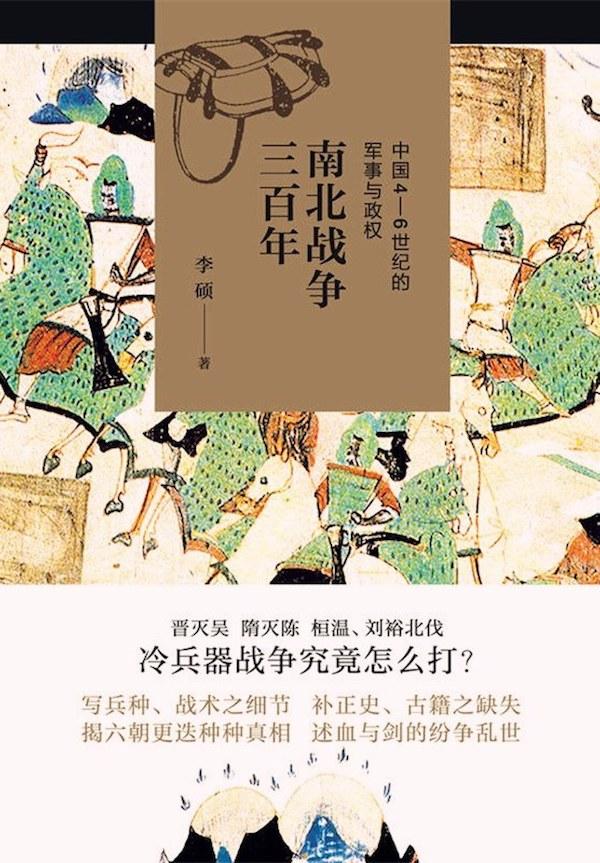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战争》,李硕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456页,59.00元

《楼船铁马刘寄奴》,李硕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325页,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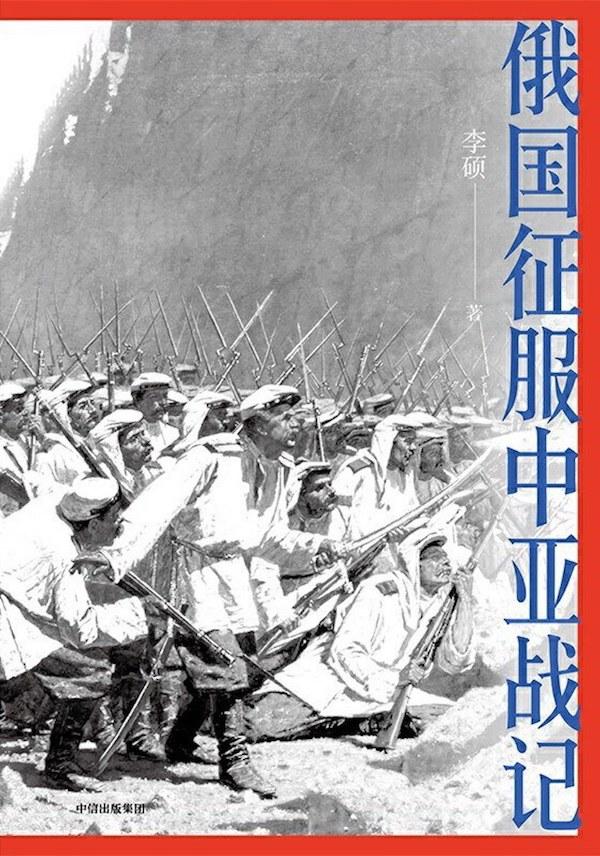
《俄国征服中亚战记》,李硕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3月出版,376页,68.00元
历史系科班出身的李硕,从来不为专业范畴所束缚,而是面向大众,追求历史写作的生动与精彩。他在博士论文中写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史,随后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即在此基础上改写,并出版了《楼船铁马刘寄奴》。曾在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工作的他,也长期关注历史地理与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近来出版的《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即是这一领域的成果。在此次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种种看法。
您的写作范围很广,出版过孔子的传记,同时长期关注中国古代战争史,最近又出了《俄国征服中亚战记》。您本人也一直很关注西域历史。您的学术兴趣是如何形成的?
李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和我本人的求学与工作经历有关。我本科是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毕业之后当了五年记者,然后回到清华历史系拿了硕博士学位。正是因为做过记者,一直比较喜欢面向大众写作。而且,我很喜欢历史写作之中那种打通古今,将历史与现实融汇在一起的感觉。最初这种感觉可能源于日本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它有两个系列,一个是1980年左右的,还有一个是2000年的。NHK拍摄的《丝绸之路》,既讲述了古代的历史故事,又展现了当下的风土人情,让你感觉到历史和现实完全融汇在了一起。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博士毕业是2012年,之后去了新疆大学工作。那会儿我就一直比较关注西藏、新疆,对这些地区的某些现实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想去当地看一看,至少给自己找一个答案。后来我在西部地区行走的过程中,就感到那种古今融汇的感觉,可能还是要到西部去找,因为东部地区的现代化速度太快,人口密度也太大,过往的历史痕迹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是以文物的形式存在,与实际生活无关。如果你往西走,过了胡焕庸线以西,你就会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就在当下,那种延续感是非常强烈的。去乌鲁木齐的过程中,一路上明显地感到人烟逐渐稀少,途经戈壁滩、大沙漠,最后突然进入一个与自己在内地的家乡差异很明显的城市,会觉得自己就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种新奇感也好、孤独感也罢,都促使着我去写作,但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西域的史料记载其实是很缺乏的,让我无处着手。碰巧那时看到了《征服中亚史》,俄国学者捷连季耶夫的三卷本著作。读的时候,我觉得俄国征服中亚的过程,一来本身很有意思,二来整个行军过程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实际上与新疆是很相似的。我想,可以写一写这个题材。
从大的历史转折来说,这个过程,是西方近现代的军事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开始向着古老的内陆亚洲逐步侵蚀。传统上,都是内陆亚洲的游牧帝国一次次地军事征服周边的农耕地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俄国也曾经被蒙古金帐汗国统治过上百年时间,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欧洲已经近代化了,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得到了发展,不仅能自保,还能向内陆亚洲实现反征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历史节点,借助俄国征服中亚这个事件,能够再现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在其他地方都发生过,农耕民族借助沿海地区来的西方近现代军事技术,形成了与游牧民族的实力之间的反转。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题目和我的博士论文,包括我之后写的刘裕,是都有呼应的。它关注的是,骑兵如何成为大陆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然后到了某个历史节点,又如何退出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大概从2015年开始,微信慢慢普及了,此后我生活在新疆,就不再感到地理上特别隔绝,心理上的孤独感也降低了不少。我想,如果我去新疆工作的时间晚上三五年,很可能就没有冲动去写《俄国征服中亚战记》了。
您的博士论文选择的题目是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史,而且写得非常的技术化,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做博论的?
李硕: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军迷。小时候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在县里的武装部上班,负责征兵、民兵训练,当时民兵还是有实弹射击、投弹这些训练的。他常常拿回家一些军事期刊或者是普及类的军事教材,让我有了接触军事知识的机会,但是当时获取知识的渠道还是很少的,在小县城买不到如今军迷耳熟能详的“三个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说起来,军事知识在中国社会普及的里程碑可能是1992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即使在比较偏远的小县城,书报亭里也挂满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军事出版物,我记得,就在海湾战争之后,县城的书报亭也有“三个知识”了,中国的军迷数量可能一下子翻了十倍不止。
我自己高考之后进了北大文科实验班,文史哲的课程都学,两年之后可以再选一次专业。当时我对明清小说比较感兴趣,觉得自己可以做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我关注历史演义小说,跟这段经历也有点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中文系是最自由散漫的,可以逃课,而且中文系有逃课的传统,因为旁听生很多,他们把座位都填满了,我不去也没关系。于是后来我又选了中文专业,但是文科实验班的经历对我还是影响很大的,我一直保有“大文科”的观念,认为文史哲本质上是相通的。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之后,我本来希望能够继续研究明清小说,考了几次中文系的研究生都没考上,索性转考清华历史系的研究生,这一次顺利考上了,跟着张国刚老师读硕士。最初他给我的题目并不是战争史,而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一个世家大族,范阳卢氏。我准备了两年,读了大量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觉得关于战争的记载不少,值得总结、研究。后来我直博了,觉得范阳卢氏题材有点窄,可以扩大一下,决定研究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后来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战争》就是在博论基础上改写的。
您非常擅长把技术化的细节融入历史写作,是如何做到的?
李硕:关于战争史的描写,特别是技术性的细节,比如说兵种、战术,甚至一些自然环境的因素,我都比较重视。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些因素,因为通过研究明清小说,我发现,大众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印象基本都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历史演义小说,战争叙事的程式化、套路化特别明显,而西方人对古代历史的记录,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非常真实、生动。这种反差之大,促使着我去复原、再现中国古代的战争。不得不说,西方人这方面确实做得要好得多,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英国历史作家霍兰写的《卢比孔河》。事实上,书中涉及的这段罗马史,当时的罗马人早就已经写得非常精彩了,之后历代西方作家不断地花样翻新,到了霍兰手里,可以说是集大成,他一方面继承了欧洲的史学传统,非常严肃、严谨,另一方面,故事又讲得很生动,通俗但不低俗。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里面最缺乏的,要么就是高高在上的官方正史,之乎者也,帝王将相,要么就是非常市井的历史演义。当然,我们不能说欧洲没有市井说书的传统,你看荷马史诗,它跟《三国演义》其实有几分类似,两员大将来阵前对打,其实并不真实,但是到了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末年的时候,西方非常成熟的历史著作就出来了。
您之前做过一个讲座,主题叫“战争作为一种方法”,对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
李硕:这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果从学院式的历史研究来说,战争史研究其实长期以来在历史学界都是空白,但是你要钻进去了,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有关系,你看多少文学作品在描写战争,无论诗词还是历史演义小说。从战争角度去切入中国历史,就能看到重大的历史节点,改朝换代也好,革命变迁也好,其实都是被战争催化、推动的。如果从普及性的历史写作角度来讲,关心战争的人确实也比较多,而且写战争是很有挑战性的,要尽量真实、完整地呈现战场环境,需要视觉化的写作技巧,这个工作做得好的话,你就像纪录片导演一样,全景式地向读者呈现了战争的面貌。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催促我尽量充分挖掘史料,然后才能把所有元素再现出来。
您是怎么挖掘史料的,能举个例子吗?
李硕: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数量和种类当然是不一样的。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基本史料是比较有限的,首先要读熟,信息点不能遗漏。还有一些已经失传的典籍,零星片语还保留在唐宋人编的一些大型类书里,例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要去爬梳、整理。还有一些更偏门的,我在写刘裕的那本书里用到了《大藏经》。当时慕容氏在攻打苻坚,包围了长安城,城里都已经人吃人了,仍然有一群西域来的胡僧在翻译佛经,这些佛经后来都流传下来了,保存在《大藏经》里。他们在译完佛经之后,会作序交代当时的情景,提到整个长安城被围攻的种种严酷细节。这些零散的史料如果能拼合起来,对复原当时受到战争影响而改变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很有帮助的,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不同于正史记载的反转性的事实。
我一直有个疑惑,中国古代文人常常是不懂技术的,可能也不关心技术,偏偏绝大多数关于战争的记载都出自他们的手笔。您怎么从中检索和辨析信息?
李硕:中国传统史籍的相关记载确实存在不少误区,以及留白之处,即便如此,如果你愿意花心思,或者有问题意识的话,还是能找到很多线索的。而且,不同的史书,记载的详实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写刘裕,史料相对来说就比较丰富,其他很多著名的军事人物,比如李世民,他打仗也很厉害,但是关于他的史料记载,就远没有刘裕这么详细。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区别?这里面存在一定偶然因素。刘裕和他手下这些大将的事迹,主要记载在《宋书》里。刘裕手下有几员沈姓的大将,沈林子、沈田子,都是很能打仗的,沈氏家族到了孙子这一辈,出了沈约这么一位文人,《宋书》就是由他来编写的。他的家族史就是刘宋王朝的开国将领史,他对各个细节更熟悉,至少获取信息是更方便的,换一个人来编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说来,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明清时期的史料可以说是极大丰富了,那么您有没有兴趣在这方面开展研究写作呢?
李硕:你说得没错,我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可惜这几年其他的事情占用了太多时间。就拿清代来说,保存下来的档案史料是非常多的,要复原一场战争,信息量确实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举一个例子。清朝道光年间,新疆爆发过一场以喀什为中心的所谓张格尔叛乱,他们几乎占领了半个南疆,清廷的平叛战争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我把《清实录》有关的史料记载大致看了一遍,得出一个结论:这场叛乱本来可以迅速平息的,完全不用拖延这么久,问题出在当地的军政长官没有决策权,想要调兵只能向朝廷报告,时间都耽误在了等待朝廷的回复上面了。因为新疆的报告送到北京,用最快的马也得一个月左右,朝廷收到报告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了,再把指令送过去,又是一个月左右,贻误战机太严重了。当然,这种信息传输问题,古代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遇到,我给你们《上海书评》写过一组关于《特拉法尔加战役》这本书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专门写到古代战争的“时差”问题。
您的博论写中国四至六世纪的军事和政权,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刘裕从南往北进攻,能够取得连续的军事成功。似乎中国历史上每次北方征服南方总是非常容易,摧枯拉朽一般,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您怎么看?
李硕:这个问题的历史跨度特别大,我没有认真做过比较研究,但是也有一些初步感受。在唐以前,整个中国北方还是人口、经济的中心,南方相对开发程度低,这是一个因素。当然,在唐之后,其实南方也发展起来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冷兵器时代,北方有战马的优势,打南方会更顺利一些。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技能是怎么来的?
我认为,在冷兵器时代,无论是基层士兵的战斗技能,还是高层指挥官的指挥技能,都是一种个人化的经验,很难得到传承,不像现在有军校教育,很多技术性的知识可以学习和传承。这就会导致一个现象,所有的军队都只能边打仗边学习,如果侥幸没死,就会积累一些战争经验。所以,对一个王朝来说,什么样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呢?就是那些经历过实战,又侥幸活了下来的军队,没打过仗的军队只能说是一些后备力量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理解一个王朝什么时候会迅速崩溃:如果外敌来得太快太猛,朝廷的军队没有来得及经受战争锻炼,让军队学会怎么打仗,就会垮得非常快,立刻就灭亡了。比如北宋灭亡的时候,多数军队根本来不及受到这种锻炼,而南宋为什么能够撑下来,因为还有些边缘地区的部队,岳飞韩世忠这种,虽然被打散过,但是又集结起来,逐渐积累了真实的战争经验,有战斗力了,就能继续扛下来。
所以,一个王朝,特别是和平时期的王朝,突然遇到敌人之后,一开头能不能撑住,是非常重要的。明朝面对清军的袭击,也有这个意味,一开始没顶住,本来地方上有很多部队的,但是都没打过仗,面对敌人毫无胜算。八旗军队渡江甚至没有专门造船,征用几条民船,甚至自己扎了几个筏子,立刻就把江南占领了。所以,战争开始后,能不能拖一段时间,熬到部队当中锻炼出一些能打仗的人,实在太重要了。你看安史之乱,一开始唐朝的军队面对安禄山、史思明在边境地区经历过实战的军队,迅速丢了半壁江山,但是唐军撑住之后,慢慢也就锻炼出来了,然后再逐步打回去。
还可以再拓开来讲一点。中国历史上还有另一种风格的战争,就是所谓“流寇”,比如黄巢、张献忠、李自成这些人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还有更早的黄巾军、天师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就是尽量不打硬仗,看到哪些比较富庶的地方没打过仗,当地军队也没有经验,就去打一打,专门捏软柿子。而且,他们也经常打败仗,万一遇到强手,甚至会全军覆没,本来几十万人,一次惨败之后只剩几百个人,但是很容易死灰复燃。因为这些老兵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能够很快地把个体的军事经验传递给新兵,一个老兵带一百个新兵打仗,很容易就能让他们学会打仗。在这个过程中,他门可以继续找软柿子捏,躲开强大的敌人,找弱小的对手打两仗,部队就锻炼出来了。反过来说,官军是没有这个优势的,他们没有选择敌人的主动性,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一个很小的范围,而且是敌人动了我才动,没有掌握锻炼自己能力的主动权。研究流寇的战争,也是解读古代史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