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2月2日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2018)上,《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获得2018年度“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

这是继欧阳敏《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产权制度》之后,《中国出版史研究》再次获得此项殊荣。截至目前,2018年度《中国出版史研究》刊发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已达10篇,累计转载达21篇。其中范军先生带领团队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依托中华书局自身的品牌优势和作者资源优势,《中国出版史研究》已逐渐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发布基地,诚邀各位专家学者赐稿。
在此节选《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文的第二部分《社会文化史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出版史》,与读者分享。
社会文化史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出版史
这一轮研究范式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地,笔者以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
的深入阐发
以社会文化史进路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认为此前的研究过于注重技术与物质层面,而对书籍的文化意义与书籍社会史的关注则严重不足。这种批评并不完全确切,如前所述,唯物史观主导下的中国书史研究已经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大量以这种模式撰写的书籍史或出版史论著,存在一种习见的“戴帽穿靴”叙述套路,即在对某一时代的出版业展开论述之前,先交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最后再缀以出版业的繁荣或衰落对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模式使得社会文化因素仅仅作为出版活动进行的布景或陪衬,而不是作为内嵌于出版过程之中的一种活跃元素存在,因而对社会文化因素参与书籍生产与传播的鲜活过程和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呈现,给读者的观感是资料堆砌过多,问题意识则显得不足。
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产生了不少成果。例如出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逐渐形成一个研究热点。查屏球讨论了汉魏晋之际以纸替代简帛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指出手抄本时代作品的传播方式造成了文学文本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成就了对陶渊明高洁形象的塑。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的《形于言,书于纸——唐诗的生产与流传》揭示了唐诗传播中口述传统与抄本文化的交织,文章通过对敦煌文献的考察探讨了唐代诗歌的传抄方式及其特征,指出作者、抄写者、读者共同参与了文本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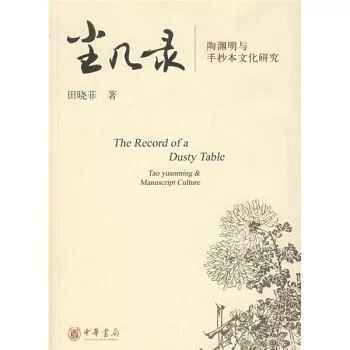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与书籍的易得,对文学创作活动与流派的形成带来重要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等。商伟研究印刷文化对文学史的影响视角独到,他认为《金瓶梅词话》从材料的来源到叙述模式的形成,都借鉴了日用类书等晚明流行的商业出版物。
关于出版与学术,苏珊·彻尼亚克认为宋代的考据方法与疑经思想与印刷书籍的普及有关。王志毅在《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中讨论了印刷出版业盛行对宋代学术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是关于晚明西学著作编译出版与传播的力作。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有专节讨论清前期学术出版的繁荣与乾嘉考据学兴起之间的关系。
出版与政治的关系,过去只是在谈到政府刊刻图书传播意识形态,以及关于禁书和文字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文化史学者对这一论题则有不少新的开掘。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力》讨论了早期文献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柯马丁主编的《早期中国的文本与礼仪》聚焦于编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早期这两个最核心要素之间的交织与互动,无论是文本的书写与呈现方式,还是宗教、政治礼仪中对文本的使用,都反映了早期书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印刷术发明后,出版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魏希德的《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在考察南宋科举策论的主导思想从永嘉学派转向朱子道学的过程时,利用当时出版的各种举业书作为分析的重要依据。周启荣的《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指出,晚明繁荣的坊刻举业书编刻活动对由官方控制的科举话语权构成挑战。魏希德与周启荣的著作都显示,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出版并不总是被动的姿态,这种对出版与政治关系的深度开掘把人们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二、书写眼光向下的出版史
在以往的出版史书写中,经典著作、珍善本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这些书籍因文学价值、学术价值或版本价值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印刷出版物来看,学者重视的多是校勘严谨、刊刻精良的官刻本、家刻本;流通于民间的坊刻本中,有许多因书坊为了牟利而尽量压低成本,导致粗制滥造,印制拙劣,被斥为“兔园册子”,不入研究者的法眼。
但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来说,这些低端出版物却是了解古代社会大众文化生活的一座宝库。在年鉴学派那里,这些读物也被纳入考量范围,但已被抽象为某些类型和一堆数字,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则对这些读物及其生产和传播过程做深入细致的解读,以期重构古代的坊刻业态和民众的阅读生活。

《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
国内学者近年来已逐渐重视对商业性出版活动的研究,如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秦宗财《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中心》等,王志毅在《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中也对明代的商业出版做了讨论。
通过各种类型的坊刻读物来深入探讨古代社会文化,是一个颇能体现新文化史旨趣的研究方向。周启荣的研究,正是利用当时举子们用过即弃的坊刻举业书来作为窥探民间以出版力量挑战官方权威的窗口。近年来对科举考试用书的研究渐受重视,台湾学者刘祥光对宋元举业书的研究、新加坡学者沈俊平对元明清举业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深度。何予明的《家与世界:16、17 世纪的刻本对“大明”的编写》则专门选择晚明几种类型的坊刻本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坊刻读物如何对经典文本加以挪用和改造以迎合乃至塑造读者的阅读口味,借以深入揭示晚明的坊刻文化。
日用类书是明清时期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较早对此类读物展开研究。台湾学者王尔敏利用不起眼的民间读物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成就卓著,其弟子吴蕙芳则对晚明日用类书首次做了系统梳理。其后王正华、刘天振等人的研究使人们对日用类书的编纂方式、文化内涵的认识更趋深入。
美国学者包筠雅把地处闽西山区的一个小镇——四堡的刻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揭开了清代至民国面向最基层读者的低端民间出版业的实况。四堡刊刻的启蒙读物、医书、术数书、举业书等,主要流通于福建和两广等地客家人聚居的偏远地区,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的阅读和文化生活,《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因而成为眼光向下的出版史的典范之作。包筠雅还考察了江西金溪、四川岳池的刻书业,这些对“边缘”地区出版业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的出版史研究过于关注江南、建阳、北京等大的出版中心的缺陷,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出版业的整体认识。
欧洲谷腾堡发明印刷术后,商业出版在出版业中占据主流,因而西方出版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偏重对商业出版的研究。传统中国则是官刻、家刻、坊刻三分天下,社会文化史兴起后,因坊刻贴近民间社会且为了弥补此前受到学界忽略的缺憾,学者们对商业出版物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 政府和士大夫的出版行为中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否没有得到充分揭示? 对此已有学者提出批评和纠正的方案,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研究架构或许是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出版的社会史
社会史是对人和人群的研究,出版的社会史就是研究出版活动中的人,即作者、编校者、抄写者、书坊主、刻工、装订工、发行商等。在过去的出版史叙述中,一些涉足于出版业的文人因其对文学和学术的贡献而被树碑立传,如宋代的陈起父子,明代的冯梦龙、毛晋等,而大批被卷入商业出版的中下层文人则湮没无闻。文人尚且如此,对商人、工匠等其他出版业从业者的研究就更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日本学者大木康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以陈继儒和冯梦龙为个案,考察了士人阶层与晚明繁荣的商业出版之间的紧密联系。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里对涉足于商业出版的士人群体做了更加广泛的讨论。关于这一方面,还有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对臧懋循的研究,韩国学者金文京对汤宾尹和俞安期的研究,何朝晖对山人梅鼎祚和俞安期的研究等。王炜的《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是这一方面较新的成果。
对文人书坊主的研究,近年来也在增多。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里,涉及不少参与小说创作和点评的文人书坊主、下层文人。对于文人书坊主的个案研究,有马孟晶对胡正言的研究,林丽江对程大约、方于鲁和汪廷讷的研究,毛茸茸对汪廷讷的研究,向志柱对胡文焕的研究,叶俊庆对周履靖的研究,井玉贵对陆人龙、陆云龙兄弟的研究等。

《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由于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的存世资料稀少,关于这些工匠在历史上的活动,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设立专章加以讨论,筚路蓝缕,钩沉索隐,居功至伟。书中关于刻工的资料相对较多,这是因前人编有古籍刻工名录多种,但其主要用途是为版本鉴定提供帮助。除了一些著名的刻工家族,如徽州黄氏有家谱等资料可供利用外,人们对于刻工的生平活动所知甚少。除张秀民外,前辈学者冀淑英、杨绳信、朱太岩、李国庆、侯真平等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辟专节讲述“刻工的世界”,是对刻工生活比较集中的探讨。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对写工、刻工的活动特点和生存状况开展研究,值得注意。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刻工从业状况、社会生活的研究还相当不足,结合刻工名录、现存版本等资料追踪刻工的从业轨迹存在很大研究空间,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随着性别史、女性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女性与书籍和出版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重要的成果有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张家才女》、魏爱莲《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等。
四、出版的文化史
出版文化,是以文化理论看待出版活动的产物,它是出版活动在价值观念、制度、语言与知识、技术与物质等多个层面的特性。文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自那时以后出版文化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在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中却较少运用。1991年大木康在日本发表《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究》,是第一部从出版文化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出版业的著作,剖析了晚明江南出版业中士人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2002年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出版,在其上编古代史部分中,作者将出版史与对学术史、文化史的考察相结合。同年在日本出版的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是一部体大思精之作,面世后备受国际学术界好评。此书打破了传统的出版史叙述框架,视野极为开阔,除出版史资料外,广泛征引了各种社会文化史资料,真正做到将出版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察,克服了出版史与社会文化背景“两张皮”的弊病。正因为如此,井上进能够从新的视角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例如书籍出版种类的变化与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宋代士大夫对于版刻兴盛的态度,官刻、家刻、坊刻之间的消长及其意义,版刻出现后为何抄本依然盛行等。
媒介环境学的创立者、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1962年出版的《谷腾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将人类的传播史分为口述、文字、印刷和电子媒体几个阶段,并重点讨论了印刷文化的特质。这一理论很快被书籍史的研究者所接受,使用口述文化、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等概念来考察不同的传播媒介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影响。克里斯托弗·李·康纳利的《文本的王国:中华帝国早期的书写与权力》认为秦汉的书写文化与口述文化界限分明,迥然不同。柯马丁则在对出土简牍文献的研究中注意到,早期儒家经典的写本保留了许多口传文化的特征。前述田晓菲和倪健的著作都揭示了抄本时代文本传播的流动性,中国学者陈静近年来也对抄本时期的作者观念、书籍传播特点等问题做了诸多探索。2016年出版的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对早期口述文化与抄本文化的关系、简帛时代抄本流传的特征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出版文化的力作。
关于印刷文化的研究成果更多,前面已经提到不少,兹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一个衍生的问题,即在中国历史上印刷文化何时取代抄本文化成为书籍生产和传播的主流文化。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刷书籍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取代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美国学者爱森斯坦提出印刷术的发明对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刻,带来了所谓“印刷革命”。中国历史上存在“印刷革命”吗? 中国的“印刷革命”发生在何时? 印刷出版业在宋代全面崛起,印本书籍种类齐全,流通广泛;但井上进和周绍明通过对历史上官私藏书结构和社会上所流通书籍样式的考察,认为直至晚明印本才在流通领域超过抄本,周启荣亦持此看法。贾晋珠、苏珊·彻尼亚克和魏希德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印刷书籍的普及使宋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新变化。中国古代的“印刷革命”、印刷文化与欧洲近代有何实质性不同? 这个问题将吸引学者继续探索。实际上,口述文化、抄本文化、印刷文化并非简单的演进替代关系,例如在明清的通俗小说文本中,就交织着几种文化的传统。
文化的视角必然带来多元文化史观,对出版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文化的特质只有在比较中方能彰显。长期以来中国出版史学界与外国出版史学界隔膜较深,甚少交流。在外国学者撰写的概述性书籍史著作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谬误频出,既反映了外国学者对中国书籍史的生疏,也说明中国书籍史学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随着中外出版史学界的交流日趋活跃,中外出版文化的比较研究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韩国学者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先后出版,主要关注印刷技术的比较。周启荣也曾撰文比较中西印刷技术。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外比较渐渐趋向于文化角度的比较。中、韩、日出版文化比较方面,2013年包筠雅和彼得·柯尼奇主编的《东亚书籍史》是一部入门读本,试图将东亚三国出版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2011年荷兰博瑞(Brill)出版社发起主办学术刊物《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为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与比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园地。中西比较方面,韩琦、米盖拉主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涉及技术与文化两方面的中西出版史比较。2016年出版的周绍明与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主编的《东亚与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反映了中西出版文化比较的最新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日益重视此问题,如王志毅的《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在讨论印刷术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出版与作品经典化的关系等问题时,均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
五、出版活动自身的文化意义
出版与文化的关系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出版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出版活动自身亦蕴含着文化意义,反映着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第一个层面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一般意义的出版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层面,对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刚刚兴起,最具发展潜力和挑战性。以晚明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士人为例,周启荣对晚明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活动进行研究,指出商业出版为科场失意的下层士人带来了“象征性资本”,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仕途之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成为读者眼中的“名公”“名家”,为这些士人带来相当的慰藉和满足感。柯丽德和方志远的研究表明,与通俗小说不同,晚明戏曲作品的创作出版,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商业利益,而在于彰显作者的品味与身份。马孟晶、林丽江、叶俊庆对胡正言、程大约、汪廷讷、周履靖的研究则发现,出版精美的高端印刷品,并在其中刻意显露自身的文人趣味及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成为商人跻身士人阶层、山人群体攀附上流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些研究将出版活动与社会心态、身份认同相联系,表现了浓厚的“新文化史”趣味。相应地,这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意无意地借鉴了“场域”、符号学等理论工具。
(本文节选自《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