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男,生于1965年9月,安徽金寨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史、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
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遽然兴起,日渐形成声势。何谓“新革命史”?目前虽然尚无定论,但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还原中共革命复杂曲折、丰富多彩的历史本真面相,应是核心要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以笔者近年关于鲁西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经验,深感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中,虽然口述资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对促进“新革命史”研究应当有所助益。
口述史料有助于让失语者发声。抗日根据地既有资料主要包括中共党政军文件档案、党史资料、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和相关回忆录等等,这些史料基本是革命者自身的话语,而根据地的芸芸大众则处于失语状态。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则可以记录普通老百姓战争与革命双重背景下的经历与体验。鲁西冀南乡村抗战亲历者的讲述,给我们呈现了文献资料里没有或者不够丰富的历史景象。例如他们对日军、伪军、土匪、八路军、共产党、国民党的印象,与文献记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又如他们关于水灾、旱灾、蝗灾、霍乱的口述,虽然与文献类似,但是更加生动、形象和具体。再如他们关于灾荒、饥饿、死亡的回忆,亲历者口述在场感的震撼力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口述史料有助于反映政策实践。“新革命史”论者批评既往研究的缺陷之一就是“政策—效果”模式,似乎只要抗日政府制定和颁布政策法令,根据地群众就会应者影从,并产生巨大效应和明显效果,这显然弱化了中共革命的曲折性和艰巨性。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则可以发现政策在具体实践之中,运行过程不仅非常跌宕,而且各地效果也存在差异。例如鲁西冀南乡村抗战亲历者关于根据地群众对中共和八路军物力和人力支持的口述应当更加符合历史实际,老百姓虽然尽力支持中共和八路军,但是他们也心存怨言,因为人力上轮番支应日伪和中共、八路军,老百姓不堪其烦;物力上多方应付,不堪其重。又如减租减息、公平负担等根据地最为重要的财经政策,因为具体内容复杂、宣传工作不到位、群众文化水平低等原因,其实很多老百姓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让交多少就交多少,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与抗战前缴纳田赋感受是一样的。
口述史料有助于弥补历史缺漏。尽管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学界提倡“从下往上看历史”,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因之一就是基层社会史料凌乱、稀缺,研究者不容易利用其进行历史书写。在既有研究框架中,无论是通史还是专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至多是作为革命史、地方史的背景或陪衬简单叙事而已,对于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不断的战乱岁月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总体印象其实是模糊的。而鲁西冀南乡村抗战亲历者的讲述,则给我们展现了根据地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例如日伪下乡“扫荡”,老百姓是如何“跑反”、村庄夜间是如何寂无一人的回忆,真实展现了战争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又如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某些方面有别于抗战之前,但是某些部分并未发生改变。他们必须还像战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即使是粗茶淡饭,但是他们也还是需要日日果腹,所以大多数时候,乡村还是会飘起袅袅炊烟;他们还是需要购买必须的日用品,也需要走亲访友,所以尽管日伪盘查严厉,他们还是会赶集进城;他们之中地主还是要出租土地,贫农还是要租地耕种,缴租借贷依旧进行……总之,通过老百姓的叙说,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根据地群众生存状态的多重面相。
口述史料有助于丰富历史细节。在既往根据地史研究论著中,大多按照“背景→过程→结果”的思路叙述,较少看到“人”的活动,也较少有“故事”发生。粗线条书写虽有其理路,但是缺乏生动材料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之一。鲁西冀南乡村抗战亲历者的讲述,则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鲜活生动的材料。例如他们关于基干民兵、县大队的描述,关于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农会等的回忆,可谓是活化了既往论著中的静态组织。又如他们关于挖道沟、拆城寨、掘地道的叙述,生动再现了八路军教授群众如何改造地形村形,打破日伪企图利用铁路、公路、碉堡组成格子网困死八路军的历史。再如他们关于1943 年“灾荒年”在八路军武装保护下,从范县、濮县、鱼台、嘉祥等地推粮救荒的回忆,能够让人真正体味什么是“雪中送炭”。又如房东关于陈再道、宋任穷、赵健民、陈赓等八路军领导一些细节的回忆,同样可以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和有血有肉。
除此之外,尽管口述史料还有助于订正历史记载错误、启发问题意识思考、促进转换研究视角、修正既有研究定论、发现以往研究盲区等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口述资料有其缺陷和适用限度。
口述史料必须经过鉴别才能利用。由于访谈人潜意识的价值预设、被访谈人历史记忆受社会环境改变,受访人容易选择性记忆,或者说只是说出符合主流社会认同的记忆,从而容易被人怀疑。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几乎所有受访人关于某个事情的说法高度一致,则应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大规模集体造假是不可能的。例如老百姓众口一词地说,“八路军跟老百姓关系好”“皇协军‘孬’”,应该说这是历史事实。又如由于受访人年事已高、文化低、身体欠佳等原因,可能记忆错乱,张冠李戴,将1956 年、1963 年洪水当成1943年大水,将1959—1961 年大饥荒当成1943 年“灾荒年”,如此等等,利用之时均需审慎辨析。
口述资料必须与文献史料结合利用。口述资料往往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表达的,如果不结合文献资料,则有可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例如在鲁西冀南老百姓经常说“日本人不‘孬’”“日本人待见小孩”等等。如果不加分析地拿来就用,不仅陷于历史研究的误区,而且也为日本右翼“史家”张目。事实上日军在鲁西冀南使用残酷手段屠杀了大量儿童,老百姓关于日军对待小孩异质性记忆需要具体分析。日军“待见”小孩是分情况的,战时和非战时不一样,打胜仗和打败仗不一样,战争的不同阶段不一样,对待不同年龄的小孩不一样,对待不同地区的小孩不一样……总之,只有经过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够发现日军“爱小孩”是谎言。
口述资料只能作为文本史料补充利用。口述资料虽然有可能使失语者开口讲话、有可能再现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但是除去选择性回忆、错误性回忆等缺陷之外,还有其他缺陷。例如鲁西冀南老百姓关于日军、伪军、土匪、八路军、共产党、国民党、自然灾害、灾荒、瘟疫等等的回忆,同质性很强,甚至叙说的主要语句都基本相同,这不仅为利用口述资料带来难度,事实上也降低了口述资料的价值。又如老百姓口述资料基本是“质”性的,而非“量”性的,尤其是有关数字时更是如此,如粮食亩产多少、中共和日伪征税多少、灾荒死人多少等等,不能把百姓所说的数字绝对化,它只是一个定性描述而已。再如有时候老百姓的叙说前后矛盾,尽管反复询问依然如此,这样的口述资料只能弃之不用。又如老百姓不可能涉及中共和八路军机密问题,所以他们的口述资料虽有价值,但是总体上看属于边缘性质的史料,只能作为文本史料补充利用。
总之,尽管口述资料可以为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开拓新思路,但是也有其缺陷和适用的限度,所以我们既不能小视或者无视口述史料的作用,也不能夸大其价值和使用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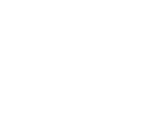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