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上海街景
编者按
近代文学研究表现出特别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取向,潘静如从近代文学学科特性和西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转向这两个方面,辨析近代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的由来,并结合具体的论著,辨析这种视角的两种取径,深入探讨其利弊得失,特别提示出文学作为审美性活动介入社会史、文化史领域的独特潜能。本文原刊《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近代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及其省察
潘静如
近代文学研究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视角。在一般的文学史教科书中,“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近代文化”被放在了统摄全书的位置上;评价学术论著时,“大文学史观”被认为是近代文学研究的无上品质,“‘历史化’和‘思想化’的文学研究……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关爱和《百年中国学术与文学》卷首袁凯声《“大文学史”视野下的百年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序第5页);而在研究者的自述中,“考察其间蕴含的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意义”(夏晓虹《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与使用》,《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几乎构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论著中,社会、文化并不是惯常的文学史书写中所谓的时代背景,它要超出于“背景”的范畴。
这样的研究取向,不难理解。近代文学的经典化不够充分,这是一个容易看到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在学科意义上,“近代文学”的发生、展开与“收束”,与士人或知识人对“现代中国”的追寻是近乎同步的。而“现代中国”,是一个综合了政治、社会、文化的未来图景。因此,除了作家、流派、文体、文学史等常见的研究范式之外,近代文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介入了社会史、文化史领域。这不是近代文学研究所独有的,像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张高评先生《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等著作都在几十年前就已问世。不过相对说来,古典文学经历了充分的经典化过程,也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美学脉络,这些视角往往是对相关文学史研究的补充与推进。近代文学则天然地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不仅是近代文学的土壤,甚至就是近代文学的“形质”。话虽如此,回顾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会发现当前研究的社会、文化取向,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风尚。早期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像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都有讲到近代的社会、文化,然而毕竟浮光掠影,其论述主要围着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性展开。这与当下的研究主流不无异趣。去理解当下的风尚,除了要看到近代文学学科自身的特性之外,还需要一点全球视野,它是这种风尚的重要源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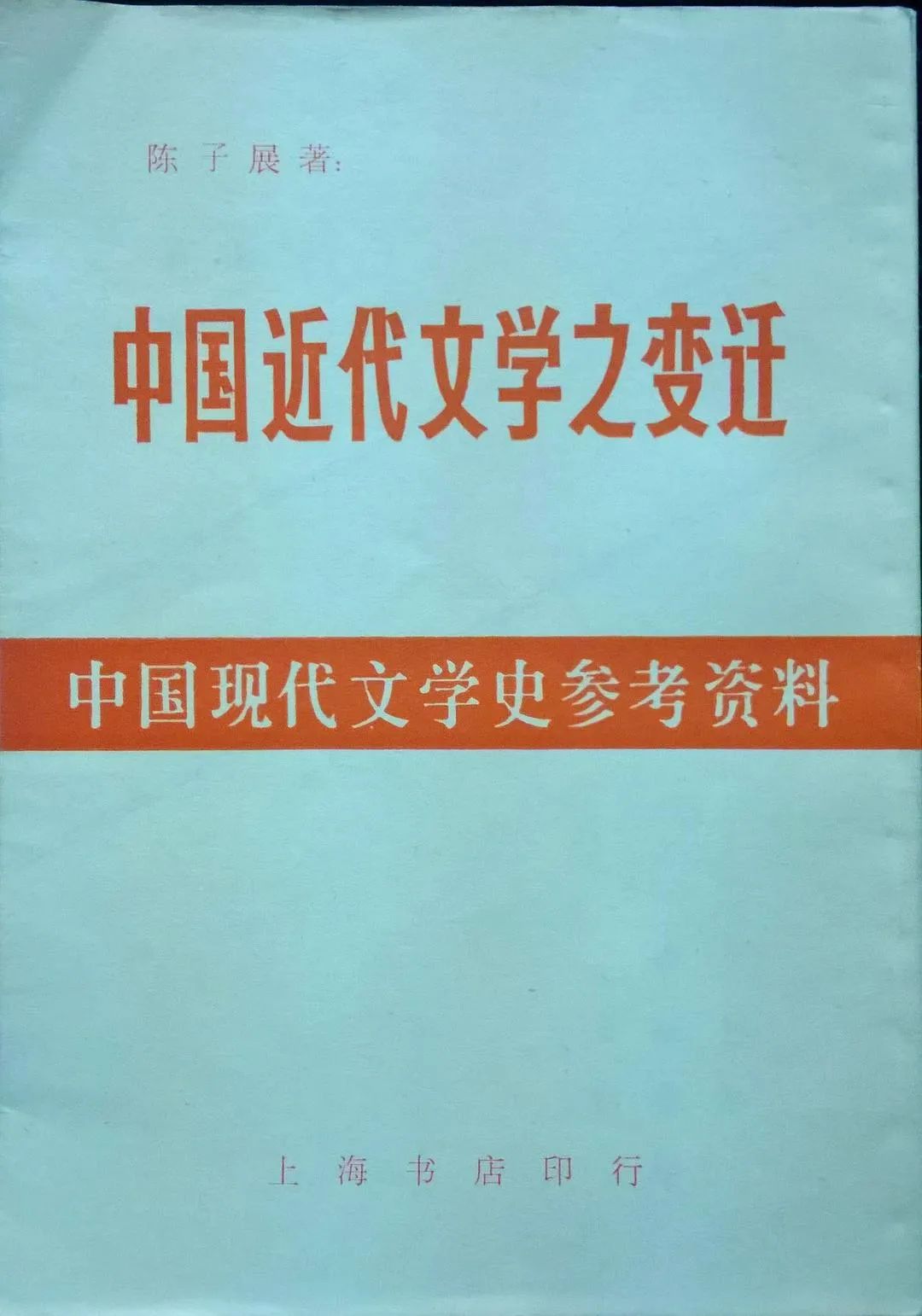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书店1982年版)
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个突出趋势是所谓“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孤立的,遍及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到了今天,从人类学到社会学,从翻译学到艺术学,从地理学到历史学,各个学科或亚学科都在讨论文化转向给自身带来的利弊得失。这些事实表明,文化转向已经是当今人文学科内占有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这恐怕得益于“文化”这一弥纶天地、无所逃遁的存在所具有的超强的整合能力及解释能力。既然是舶来品,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体现得最明显的首先是外国文学研究;论著标题中的性别、旅行、殖民、认同、东方、他者、想象等字眼排山倒海而来,我们只需翻一翻相关刊物就可以一目了然。流风所及,中国文学研究也颇有此一趋势。与“文化转向”相映成趣的是,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学界在厌倦了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原型批评诸如此类的理论之后,文学研究领域也近乎自发地形成了新的“社会学转向”,其意无非是希望勾连文学、社会学各自的丰富形态,生发出既深具解释力又充满开放性的文学研究范式;这种跨学科的文学社会学“无所不在而又一无所在”,诱人的同时也有两不沾、四不像之虞(参见James F. English. Everywhere and Nowhere: The Sociology ofLiterature After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New Literary History,Vol.41, Iss.2,2010)。去争论它的界限、学科或合法性,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行动,也就是如何基于这种思路展开具体研究,以达成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理想愿景。无论是文化转向,还是社会学转向,都意在展示文学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阔图景。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给圈养或驯养起来。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问:文学——或者更警醒地说,诗意——哪去了?所谓“诗意”不是仅指诗歌而言,而是包括了小说、戏剧在内的一切文学;它是一般意义上“文学”的代名词,或者说是文学的内核。这种担忧或疑问,是对文学的维护,有警示意义,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近代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似乎产生得最天然、也表现得很突出,然而“近代文学”这个帽子毕竟保留着。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它们在互相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张力。但是这一点,不宜笼统论述。我想,首先需要作一些界定或甄别。当下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维新、改良、革命、女性、翻译、公园、现代性、阅读史、教科书、进化论、印刷技术、传播媒介、稿费制度、消费市场、图像语言、交通行旅、知识体系、口岸文化、都市生态、日常生活、民族国家、东亚儒家文明这些轻重不侔、大小不一的视角或范畴,随时可以见到。对它们逐一批评,既不现实,也不理智。不过,可以对此作一个粗略的类型分析。一种是考察这些视角、范畴对全部近代文学及其形态的塑造;一种是考察近代文学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承载了这些视角、范畴及其背后更为复杂的内容,甚至根本性地施加影响于这些视角、范畴。二者都旨在呈现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前者的重心落在“文学观念”“文学生产”“文学形态”诸层面,后者的重心落在“文学书写”“文学阐释”诸层面。这两种取径在具体研究中往往是错综存在的,我们不能以辞害意,但一项研究的主导方法是容易看出的,它决定了研究者笔下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类型偏于哪一种。
假如有心人疑惑的是“(近代)文学哪去了”,前者的研究取径与此正不相干,因为它要考察的是近代文学是怎么来的,或者,近代文学为什么以这样的面貌或姿态出现。这些内容是“文学”自身所无法完全或充分呈现的。像张天星《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1833—19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胡全章《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述都考察了媒介、技术或与之相关的稿酬、版权等制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与塑造;没有这些媒介、技术或制度,近代文学的形态、精神就无法想象。这种研究取径无可指摘,也无可替代。后一种研究取径则多少与“文学哪去了”相关联;强调“多少”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分层次、分场合的问题。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文学的“诗意”,虽然有修辞、审美诸如此类的自家脉络,但都不是空中楼阁。它与社会、文化肯定有关联。问题在于,文学书写如何通向社会史、文化史?以小说而论,不论是小说人物的言说,还是第三人称叙事者的风景、场域叙述等等,都需要研究者加以甄别,不可能像一般的社会史、文化史资料那样称手,当作中立或纯粹的记录。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阐释一定符合作者的本意,但说阐释权完全在读者手中肯定是一种乡愿。对作者及其文本保持必要的敬畏是明智的。因此,在这样一种研究取径上,葆有文学的“诗意”反而愈加重要。因为只有注意到文学固有的“诗意”,然后再加以解读、阐释,才有更值得信赖的基础。其次,越过了这一门槛之后,研究者希望达成怎样的图景?文学涌动着时代的脉搏。对文学文本乃至文学活动进行研究,它可以与社会史、文化史互相映证、互相发明。这毋庸置疑,关键是这一论证过程是否绵密,是否精彩。事实上,不光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就连对文学性书写要求不高的生态史研究都很可能需要乞援于文学。举个例子,研究殷商史的学者就颇抱憾于甲骨文、金文这些档案或铭刻资料“不足以赋予商代历史图景以生命和精神”(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陈星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前言第2页);而去论证当时中原的植被、生态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收集的48个以“木”为偏旁的文字年久义湮,僵而无神,殊不济事,比不上几百年后《诗经》里“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等诗句来得有力(参见张光直《商文明》,第148-151页)。
这是文学“胜于”档案之处。反过来,当后世特别是近代的社会史、文化史资料已经多到令人咋舌的地步的时候,文学研究变而为社会史、文化史的注脚,虽然只要够精妙,仍无愧一流,总还未免有点弃长用短的意思。因为不论社会还是文化,总是包括了人的情感、欲望等元素在内,这是文学之所长。也就是,文学作为审美性、精神性的创作活动,它介入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潜能理论上要大于“互相映证”“互相发明”之境。
上述两种取径类型不同,但都是包含了社会、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它们不那么传统,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充满了趋时、炫技、尚奇、藏拙(就赏会文学的“诗意”、展现研究者的“灵光”而言)的毛病。这也难怪,流行的范式有依样画瓢的危险,是学院里论文生产的捷径,也是我们研究者“藏拙”的好帮手。但比较公允的态度是,看看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研究。与此相应,我们也不能放弃对这种研究的反思。这很难泛泛而谈。笔者试以都市、行旅两个视角为例,围绕学术界的具体论著展开讨论。这两个视角都可归于那种强调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范畴,但各自的空间、风景、体验及相关书写,又容易聚合出甚具辨识度的情调、审美或风尚。省察它们,具有一定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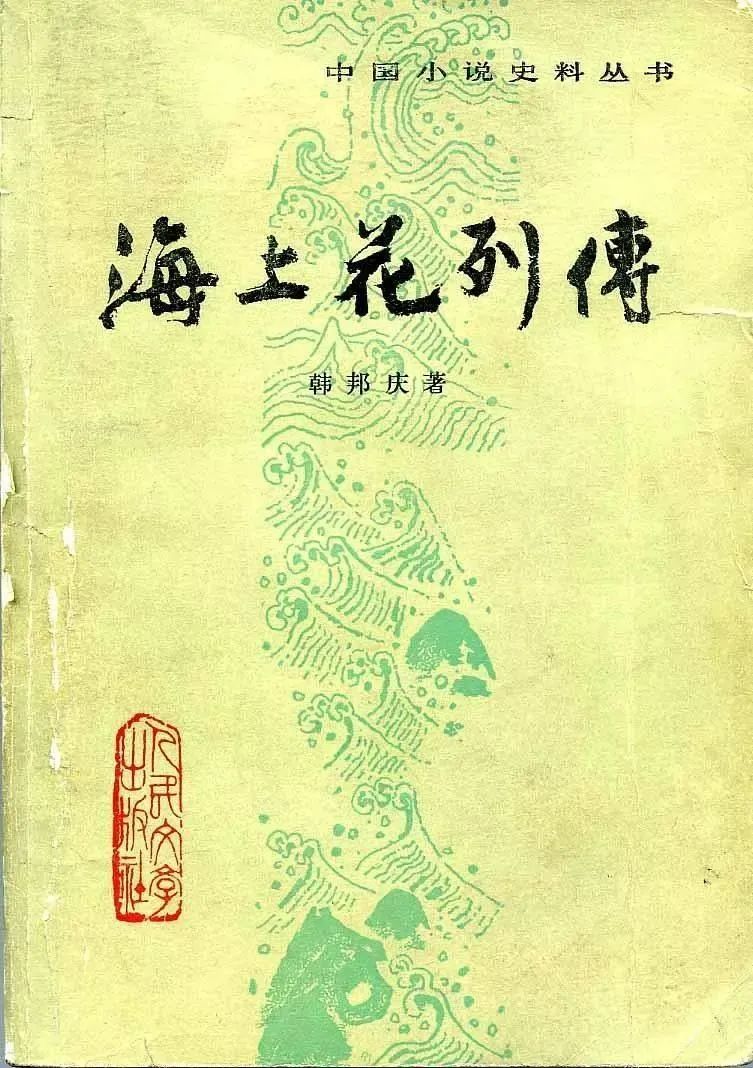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近代不同都市之间的差异很大,姑且以上海为例。在论著类型上,两种取径都不乏。比如,同样是着眼于近代上海与文学的互动,申浩《从边缘到中心:晚清以来上海评弹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接近第一种取径,它更关注都市上海是如何影响评弹的,具体说来,由于评弹的说唱文学性质,它关注的是上海如何影响或左右了评弹的场地、市场、表演等,当然也涉及到当时的社会“改良”浪潮对评弹的波及;而朱国昌《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更近于后一种取径,它考察的是晚清狎邪小说如何“叙述”都市上海,包括夜生活、都市空间等等。仔细阅读这两种论著,就会发现,申文几乎只注重都市之于评弹的影响,缺少逆向互动。相形之下,朱著也注意到相反的互动机制,层次也更多,将文学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纠缠形态展示得更全面。朱著特别强调“传统城市概念是一个偏重于地理意义上的认识”“很少把时间的概念加入进来”(朱国昌《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第13页),而“上海都市一形成就带满了都市特点的各种标记”“它的意识形态由地理的、政治的、军事的、权力象征的转变为商业的、金钱的、欲望的、时尚的,构成了都市完全意义的实体”(同上,第14页)。
朱文的这些论述暗示,在上海身上,“近代(现代)”与“都市”是一对孪生概念。带着这样的理解,朱著解读了《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九尾龟》《海天鸿雪记》等晚清狭邪小说。朱著从很多层面给我们作了展示,像《小说时空观建立起来的都市景观》《绝望的都市心理倾泻与世纪末描写》《娱乐空间、都市病与现代性》《“穿插藏闪”的叙事策略与都市空间视点》等章节都十分精彩。比如,作者指出《〈海上花列传〉例言》提及的“穿插藏闪之法”,不论是韩邦庆的天才闪现,还是精心创造,正合于晚清都市叙事表达方式的“枘凿”,折射了都市的空间结构,是现代叙事的最佳形式(参见朱国昌《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第125页)。换言之,它无形中契合了现代都市的璀璨陆离及由此形成的生存状态、情感结构。作者进而从小说文本上作了论述。这类研究颇能显出作者的眼光与文艺学功底。笔者过去研究清遗民时,关注过中外学界对近代上海的研究,也注意到这些论著颇瞩目于上海的“大都市”之病:19世纪末的它有幸与伦敦、巴黎一样同脏污、瘟疫、淫乱而斗争(参见Marie-ClaireBergère,Shanghai: 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9.)。
相关材料很丰富,但带来的阅读体验与认知都与朱著相悬绝。我想,那是因为都市(史)研究,与都市视角的文学研究,有其不同。后者植入了情感、欲望,把它们与夜色、空间、娱乐、商业乃至清帝国(或民族)的“世纪末”症结打为一片,复活了19世纪末的上海人文景观。哪怕是相比同类著述,如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 1850~1910》(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朱著对文学、爱欲与都市情致的把握都更为精到、细腻,逊色的倒是文献。在这个意义上,朱著把被剥离或忽视的“诗意”以及“人”之情感、欲望重新植入到近代的社会、文化之中。这是它不同于一般社会史、文化史之处。而文学自身也由此得到照烛:是都市上海催生了这类“海派文学”、近代文学,但文学也在“制造”上海,相关文化及所谓现代性都由此得以具象化,变得可感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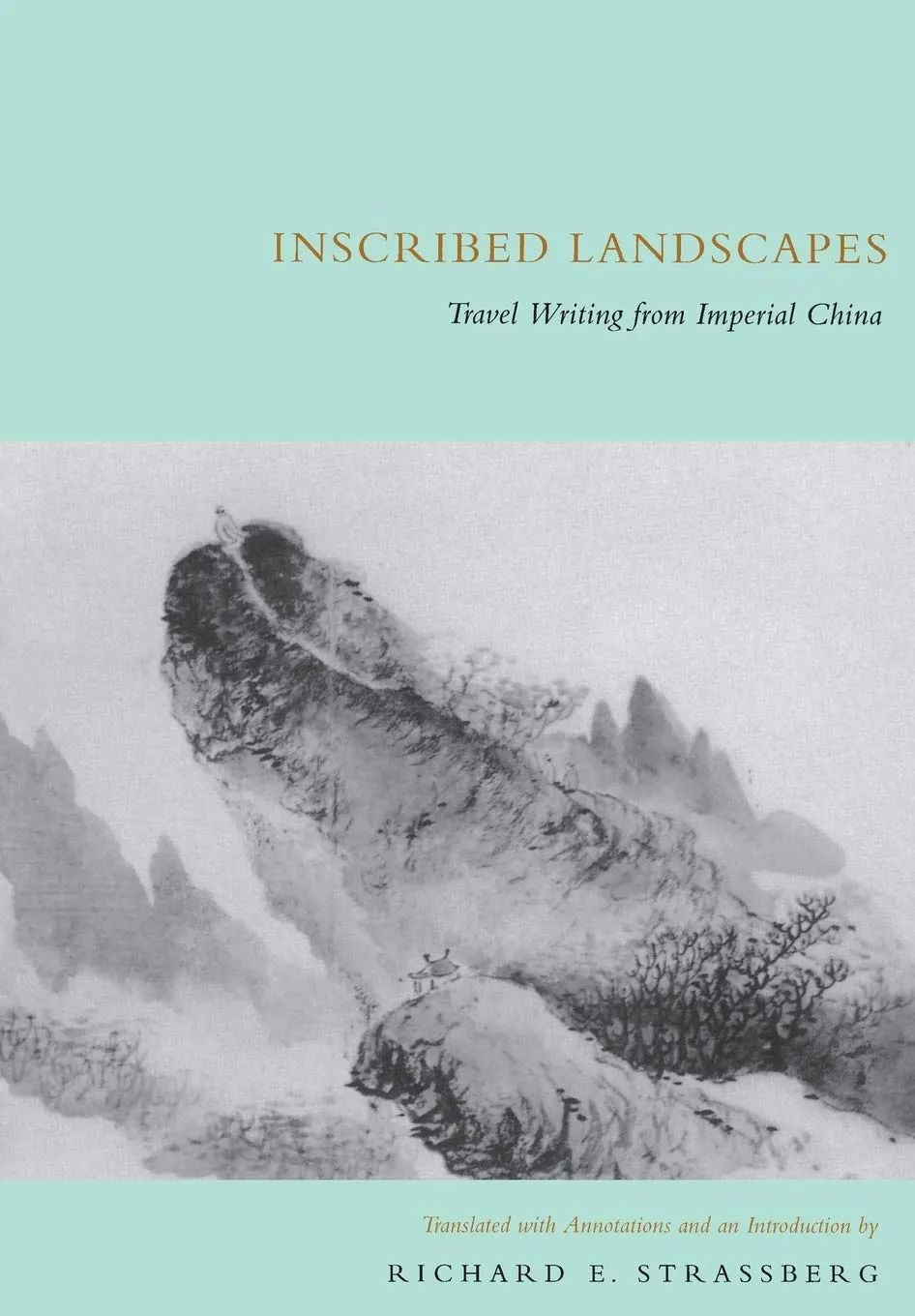
Richard E.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再如行旅,也是近年来常见的一种视角。它其实很对“中国学”的胃口,是前述西方人文学界“文化转向”趋势在中国学领域的表现。从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编译的《被题写的风景:中华帝国的行旅写作》(Inscribed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4),到汪利平的《待售的天堂:杭州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空间与旅游业》(Paradisefor sale: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1589-1937,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1997),再到田晓菲的《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莫亚军的《观览中国:现代旅行文化史》(Touring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CornellUniversity Press,2021)等,遍及了中国人在古代、现代、中国、西方的各类行旅写作。
石听泉编译的这部《被题写的风景:中华帝国的行旅写作》问世最早,一时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书评,可说充分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趣味。不过,国内的近代行旅研究,首先还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早期研究大抵以就事论事为主,考察各色人物游记的具体问题,并不热衷于把“行旅”标揭为特别的视角或方法。近年来这种趋势才开始明显。比如,杨波《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就以海外“行旅”或“游记”为视角讨论了晚清文学的变革。这篇文章意在把行旅或游记作为视角,对晚清文学变革作全面观照,像“新文体”“记游诗的异域书写”“小说救国神话的传衍”“从声光化电到改良戏剧”等,都被纳入了进来。未必豁若发蒙,但有助于提醒我们近代文学的发生,在每一种环节或路径上都带有整体性。其实,海外行旅的文学影响,在我们的第一印象或记忆里大概是诗词或散文的异域书写,郭文仪《清末文人西方书写策略及其地域特征——以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行旅书写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就很典型。文章分析士人海外行旅的“书写策略”,包括了修辞方面的考察,但主要还是落在文化层面,其引入后殖民文化理论里所谓的“凝视”就是一例。
文章接受这一点,又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一部分晚清士人“异化”西方,也带有“凝视”性质,包含着某种对抗。学术界过去何尝没有见及,只是习惯把它当成晚清士人猎奇或隔靴搔痒而加以批判。这一转换,就丰富了行旅书写的意蕴。与学术积累相对应,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更在方法论上对“行旅”“西方”“想象”作了探讨,强调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研究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杨著将“行旅”视为游记现代性发生的行动因素,“行动层面的域外旅行正作为一种功能性因素作用于晚清书写者,并在晚清思想图景的现代性转换中发生重要意义”(《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第11页)。“越界行旅”不仅是异质空间上的,还触发了关于时间的现代性认知,至于“火车、轮船的出行经验则从体验维度将现代性引入旅行活动的日常肌理之中”(同上,第12页)。经由这些研究,“行旅”作为视角的潜力与意义被不断释放出来;近代文学的发生,因此可藉由这个视角加以观察、审视。
但不管是都市、还是行旅,这些视角也有一些易于被忽视的问题。这些视角常常带有某种社会史、文化史理论的痕迹;作为预设或前置,它们可能回避很多问题,而且不著痕迹。比如朱国昌《晚清狎邪小说与都市叙述》早早就抛出近代上海的意识形态由“地理”等因素“转变为商业的、金钱的、欲望的、时尚的,构成了都市完全意义的实体”,后面的文本阐述与问题提炼也确实很精彩。而掩卷之后,稍加思考,便有未惬人意的地方。我们可能不禁要问:“商业的、金钱的、欲望的、时尚的”这些因素,在明末的南京、苏州,清中叶的扬州等城市及相关诗词、笔记、小说中是否有表现?程度如何?该怎样去理解?它们涉及到“古今之变”的立论依据及文学表现,不该被轻易放过。我想,面对这样的疑问,作者可以辩解他强调的乃是这些因素“构成了都市完全意义的实体”。读者是否信服以及是否会进一步追问“实体”的具体内涵,这里不必假设,但逼着作者“辩解”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所以,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理论时,我们试着从文学出发,又由近代文学而观照古代文学,避免过于断裂、斩捷的预设,是不是更好?将社会史、文化史理论作适当的悬置或存疑,不见得就会得出什么颠覆性结论,但近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保留此种警惕似乎是有必要的。
另外就是各类视角虽然新颖,构成学术界通常说的“学术生长点”,但实际研究中,会落入名实不符的境地。一方面聚焦不是那么准,一方面视野又没有开阔到最理想的程度。以行旅而论,虽然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作了逻辑上的检讨,但放眼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行旅”被作为视角提出时,却连基本的界定都会被略过:行旅是否有别于更宽泛的寓居?强调它的移动状态吗?围绕行旅对写作机制的影响?行旅的空间?或行旅书写里的文化互动?这些不界定清楚,就会影响文章的说服力与意义。比如杨波《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的焦点之一是“小说救国神话的传衍”,核心论据是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诚然写于寓居日本时,但它与行旅游记的关系实在不够醒豁。类似的细节问题,也容易出现在其他视角的研究中。浮泛、笼统或跳跃,往往消解了这些视角本可能具有的独特价值与解释力。另一个问题就是,谈文化总是预设了比较视野。考察近代国人的海外行旅,为了防止简单的目的论或二元论取向,达成更周密的省察,我们好像也应该对同时代洋人的中国行旅及其书写有所了解、映照或驳难。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当下,一些适用的研究论著获取起来并不难,比如西方人在华行旅及其书写的基本情况,就可以参考弗里切的《叙述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旅行者在“中央之国”》(NarratingChina: Western Traveler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fter the Opium War,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社会、文化视角是如此之多,其利弊得失,还有待进一步省察。可以看出,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引入这些视角,不但能弥补一般文学史叙事的不足,更能诠释“近代”之所以为近代的内蕴外缘,特别是有的视角贯穿了近代文学的很多环节或领域,能够有力地展示近代文学发生、形态或观念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因此,近代文学研究几乎不可能排斥社会、文化视角,这只在比较特殊的议题内才可行。但是,在研究写作中,如何真正把握好各类视角,避免仅仅把它们当作门面,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法论上,近代文学研究不宜完全充当各种社会史、文化史及其理论的注脚,而应以其幽微、深邃,呈现一般社会史、文化史所难以进入的世界,体现自身无可替代的意义。也就是,立足文学自身,在一些议题上,勘破社会史、文化史可能存在的习焉不察的偏宕,提供一种有别于一般社会史、文化史的认知。说总是比做来得容易,这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之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片来自网络)
版面:李成城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