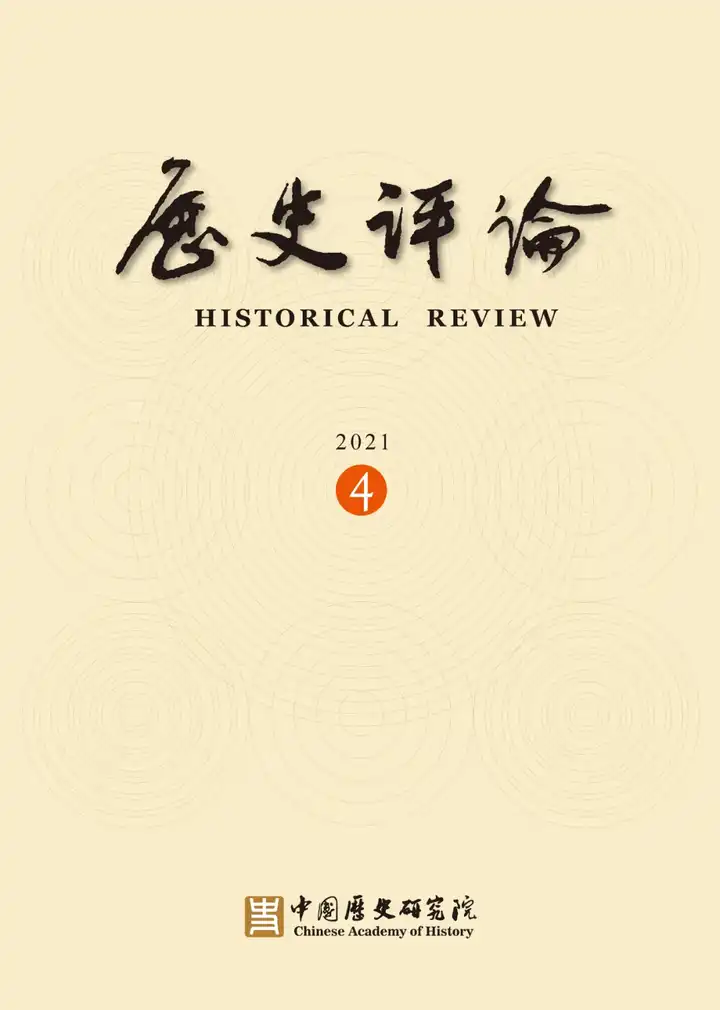
陈寅恪善于从民族关系、宗教角度以及地域分野出发,研讨政治格局、历史事件,并多将佛学与中国某些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评议历史人物,探索门第、出身因由。这种思路,具有可能建构新说的空间。但这种思路一旦过度套用,就会成为主观的穿凿和臆断,甚或陷入思维定式而难于自拔。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陈寅恪(1890—1969)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篇的史学家,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更因其名声乃鹊起于治史成就之上,享誉海内,被推至史坛之巅,影响深广,以至于无法回避。然而平心而论,陈寅恪既不像傅斯年等身居学术要职,也不像顾颉刚等竖起学派旗帜,亦不像郭沫若、董作宾等具备辨识甲骨文、金文的绝技,何以一时间广受称颂,奉若神明?况且陈寅恪之学术见解,讹误屡见不鲜,思路往往偏颇,没有一定的风云际会,怎能够安坐升腾而至于“巅峰”?
治史的历程和特点
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揭开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序幕,但在清廷君主专制体制下,学术发展仍然受到极大束缚和扼制。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使新思潮、新文化冲破千年桎梏,呈不可阻挡之势。这种时势,展示出社会革命和革新的前景,更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不仅有利于追随新潮流的研究者,而且有利于所有治学之人。例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被称为甲骨学“四堂”,各具杰出的学术成就,但就思想观念而言,四人的保守与前卫,是大不相同的,关键在于他们皆具有时代提供的研究条件,均在个人的学术基础上实现了抉择。
陈寅恪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家世显赫,祖、父在清朝为官为学,颇具名声,其兄弟多人留学海外,亲朋亦多名流。陈氏本人辗转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的名牌大学,读书治学而不谋取学位,专攻冷僻文字以及宗教、民族、人类学知识等,学识广博;仅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习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即历经7年以上。这种特殊的学术抉择,非常人所能够具备的见识、勇气与决心,得到友朋赞美和众口传扬,使陈寅恪尚无学术著述,就已名气高昂,1925年即被刚刚建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一举铺开历史研究的坦途。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除指导学员与讲授课程之外,最初正式发表学术论文是在1927年,并于年内连续发表3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文章虽篇幅不长,但充分显示出他的学术品位。第一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综合引证敦煌文献、藏文文献,参证梵文、蒙文语音,同时参考法国、日本学者的撰述,考订唐文宗时期高僧法成翻译佛经的事迹。陈寅恪认为,法成乃吐蕃人,将藏文佛经译为汉文,是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对照玄奘,他发出感慨:“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第二篇《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不足400字,然内容丰富,通过考证罗振玉所藏此件敦煌佛曲,穷纠缘起和流变,指出其与另几种佛经经卷、梵文文献、藏文文献所载故事情节一致,认为自己在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所见吐鲁番壁画即为“欢喜王观有相夫人跳舞图”,并指出同时期西北地区民间盛行“有相夫人”故事,曲乐、图画一应俱全。此佛曲体裁,乃“所谓马鸣大庄严经论之支流”,中国仍在流行的弹词或许由其演变而来。第三篇篇幅较长,引证更为广博,详细考订一部梵文佛典经卷残卷,曾为著名佛学家鸠摩罗什翻译。文章以此梵文残卷校订其他中文译本,分析译文语义,展示出陈寅恪的深厚造诣。陈寅恪撰写这样的论文,各项证据若随手拈来,而一般学者休言撰写创述,就是想真正读懂,也非易事。陈寅恪发表论著起始,虽然只是牛刀初试,却已具备他人望洋兴叹的独到水准。此后的论文,也多发挥了他的特长,即掌握多种文字的史料,熟悉世界多种文化的内在机理,了解多种民族的历史,善于捕捉史实细节予以考订和分析,并从中透视出宏观历史背景及其演化进程。
陈寅恪并不以具体历史问题的考据为治史宗旨,而是立足于考据,更新政治史、文化史研究,探讨一代或几代的治乱兴衰。1940年撰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对历史的思考已经进入较为宏观层次的标志,随着这部著作的面世,陈寅恪在当时已经无愧于史学大家的名位。1950年写就的《元白诗笺证稿》,在以诗证史的方法运用上树起典范,为学界普遍赞誉。陈寅恪的记忆力甚强,但并没有坊间传说得那样神奇,由于他对诗词的记忆比较清晰,故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越发将解析诗词作为史料运用的重点。这种治史方法,令陈寅恪晚年的学术生涯别开生面,使之在助手协助下,仍能撰成大部帙的《柳如是别传》,成为史学界发奋著书的又一奇迹。但宏观性的历史著作与考订具体史事和文献不同,它总是离不开一定历史观、价值观的制约,没有最先进的理论性修养,认识的偏颇则难以避免。因此,即使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的著述,也应予以客观审视,不能过度拔高。
“套路”中的穿凿和臆断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及治史方法有其过人之处,他善于从民族关系、宗教角度以及地域分野出发,研讨政治格局、历史事件,并多将佛学与中国某些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评议历史人物,探索门第、出身因由。这种思路,具有可能建构新说的空间。但这种思路一旦过度套用,就会成为主观的穿凿和臆断,甚或陷入思维定式而难于自拔。在陈寅恪的两部隋唐史名著中,存在因陷入定式而主观构建较为宏观性说法的状况,而且相当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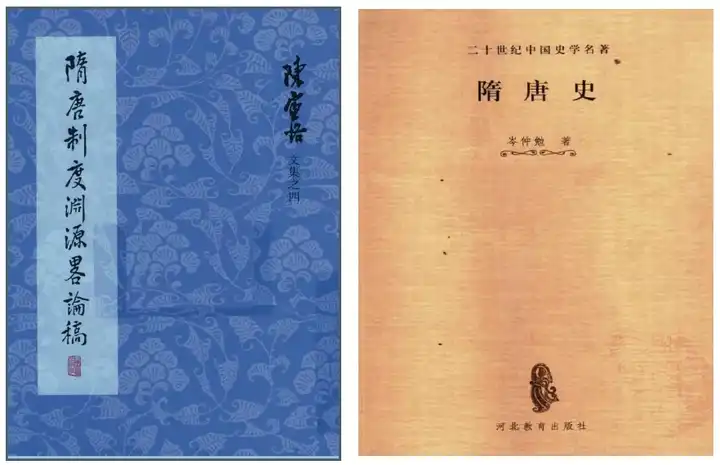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的代表作之一;《隋唐史》凝聚了岑仲勉数十年的治史心得 资料图片
岑仲勉于1955年出版《隋唐史》,批评了陈寅恪的诸多观点,涉及李唐家族先世问题、府兵制问题、唐代士族问题、唐代“古文运动”问题、所谓唐朝统治的“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牛李党争”问题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的核心论述,几乎全被岑著反驳。例如,陈寅恪认为唐朝之初,上层统治者为“关陇集团”,实行的是“关中本位政策”,其根据只是考订了唐朝皇帝李姓先人为陇西人而已;又说至唐高宗、武则天之时,因武氏不是关陇之人,于是大兴科举,重用科举出身的官员,用以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岑仲勉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以唐太宗时主要高官为例,指出其中绝少关陇之人,而多为太原起兵时旧臣;又举出武则天主政期间任职宰相的70余人,可确定为科举出身者仅22人,不足三分之一。这是很简单而有效的统计分析,陈寅恪仅以唐朝李姓皇族曾为陇西士族,就得出唐初上层统治者为“关陇集团”的结论,此乃出于主观预设,缺少客观证据,根本无法回应岑仲勉的批评。
至于所谓“牛李党争”问题,较为复杂,涉及诸多历史人物的细节。按陈寅恪说法,“牛党”指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则是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双方斗争延续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陈寅恪将之套入“门第”官僚与“科第”官僚的框架,认定李德裕为“门第”党首,牛僧孺为“科第”党首。岑仲勉批驳了陈寅恪的说法,指出:第一,“李德裕无党”,他反对牛僧孺的政见系出自个人主张,并无他人呼应,因此李未曾结党;第二,“牛党”并非以科举出身作为相互勾结的基础,被陈寅恪列入“牛党”的21人中,竟有15人既为旧士族又出身进士,仅6人非旧士族出身;第三,被陈寅恪强列于“李党”的8人中,非旧士族者就有5人,其中4名进士、1员武将;余下3人中2名是进士。益见所谓“李党重门第”之说,乃无根之谈。岑仲勉还对相关历史记载进行了细密考证,澄清许多真相;而对照陈寅恪的论述,则无可靠的史料依据。
岑著《隋唐史》面世后十余年间,陈寅恪无片言回应和答辩,学界偶有为之辩护者,皆不能有力回应岑仲勉举出的实证。至今许多过度拔高陈寅恪的论作,都回避了岑仲勉的相关批评,鲜有人从学理角度反驳岑著论点,足见相关热捧之文远非合理的学术评论。
至于唐代是否始终存在地域性官僚集团斗争?是否贯穿着士族门第出身与科举出身官员不可调和的斗争?这需要将具体史实考订与宏观背景结合方能得出可靠结论。从唐初即开始实行的科举制,除拓宽汲取人才的渠道之外,还造成以往旧有士族与庶族的合流,入仕之道以科举为正途,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就消除了官员按出身结党的利益基础。高官之子也主要通过科举入仕,个别由官荫解褐,这是朝廷对高官、功臣的特殊待遇,仅为选官体制的一点补充,并不关涉士族门第。陈寅恪的见解不能成立,是毫无疑义的。
陈寅恪有些学术议论,或是未经严密考察即随手写出,表现出十分主观的臆测,因而严重失实。例如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开篇即言:“裴世期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熏习。”又说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等,“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这是从佛学文献与中国史籍某些行迹相似的印象出发,遂将裴松之《三国志注》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书中夹带考异的做法,断定为仿从佛学“合本子注”的文献形式。
然而,得出如此观点不可或缺的前提,是首先需要证明裴松之等史家信佛或读过佛学之书,并且要证明佛教“合本子注”是这类文献形式的唯一样板,而绝没有别类文献提供更直接的启发。事实上,裴松之等史家并不信佛,也无任何材料表明他们曾经研读佛教之书。《三国志注》仿从的是韦昭《国语注》、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书;“集解”,就是将各种相关资料集合起来予以解释,西晋之后这种形式的经部著述甚多。
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的考异,乃直接得自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将考异写于相应正文之下作为夹注,不再另成一书而已。这是因为,《续资治通鉴长编》部帙宏大,考异如果另成一书则很难查核;相较而言,系于正文的选择,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陈寅恪惯于将佛教文化联系东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成思维定式,不经考订即直接判断,实为轻率。
这里之所以细致分析陈寅恪的学术局限,不是要全盘否定他的学术业绩,要点在于打破盲目跟风热捧陈寅恪等史学家的倾向。将陈寅恪的史学鼓吹为高不可攀、至美无瑕,这本身就是背离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陷入片面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泥淖。
“陈寅恪热”的兴起与时会
陈寅恪虽然一向学术声名卓著,但真正被无限度美化,乃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适应了一些人的某种诉求,热捧之风随之兴起,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走红当世的又一时会。但凡随风气而动的历史认识,必当予以冷静、细致的反思,使史学评论、学术发展进一步坚持健康的方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是否完全正确,也需要辩证地分析。平心而论,将这个理念限定在学术研究范畴,虽非至论但也不必厚非,不少学者也都提出过学术研究应当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要意旨在于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或许也含有某种立身处世的自我尊严。
但即使在学术范围,这也不可视为至理名言,片面强调精神“独立”是不妥当和有害的。学者难道可固执到连“见贤思齐”的古训也抛弃吗?人生之中,需要常有积极、进步的社会精神激荡于心,才能获得高超的见识。绝对化的“自由”思想是没有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之内,有的思想看似自由,而从其产生到存续,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或阶级根源,许多人的“自由思想”会发生冲突,导致谁也不能绝对自由,社会资源的限制也无法保障所有自由思想的实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捧陈寅恪的热潮中,也存在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念扩大到政治思想等多种领域的倾向,不仅可能滑向理论与立场偏颇的荒谬境地,更歪曲了陈寅恪的学者形象。
陈寅恪的家世条件和学术际会,使他较为容易地在学界取得一席之位,但同时也制约了他思想的进步,导致他成为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导致形成过多从人物出身门第出发研究历史的思维定式。有人赞称陈寅恪是“贵族史学家”,其实做学问表现为“贵族”理念,利大还是弊大?需要辩证裁定。研究历史如果恪守一种贵族意识,其影响求实和求是宗旨的贯彻,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陈寅恪是否真怀有“贵族”心态,并无确据,而将“贵族史学家”视为莫大优点,应当说评议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以此为例,可以说明史学评论必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亟须坚持唯物辩证法,避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而理智、冷静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仍应是长期坚持的准则。
就岑仲勉与陈寅恪对比而言,1950年后岑仲勉愈益加大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力度,并仔细揣摩其中的思想方法,从而汲取史学研究的养分,《隋唐史》一书即附有用辩证法分析历史问题的专篇。在《隋唐史》中,岑仲勉不仅体现出对历史研讨的周到,即不仅重视政治演进,而且尤为重视隋唐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此外,他还注意到古代史书不可全信,而加以去伪存真地考辨。例如,岑著揭示了司马光记述唐代历史,故意采用不实资料以贬低李德裕,批判了司马光基于保守派立场的记史曲笔行为。岑仲勉这种深入的求真作为,既发扬了古代史家直书、实录的传统,也贯彻了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准则。史学界与岑仲勉态度相似者不乏其人,例如郑天挺、唐长孺等,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上没有不自由的感触,反而是得心应手地获得很多创新成果。
陈寅恪的两部隋唐史著述,仅将经济问题放在国家财政框架内简单叙述,没有探讨隋唐时期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由于成书较早,情有可原。但自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未曾对旧作反思和修订,甚至学术上不再触及经济问题,则多少显示其历史观念的停滞不前。在偏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状况下,陈寅恪忽视了最重要的史学理念——记史求真的准则。他在评议古代史家时重于治史方法的分析,很少用是否求真的尺度予以衡量,如在评论司马光的“史料长编法”和宋代学术之时,其结论就存在从主观意愿出发而过度赞美、夸张的倾向。类似这种失误,都与片面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无关系。
盲从性的“陈寅恪热”,应当冷却,更不应借热捧陈寅恪而贬抑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不能作为学术旗帜,更不可借此怀疑与否定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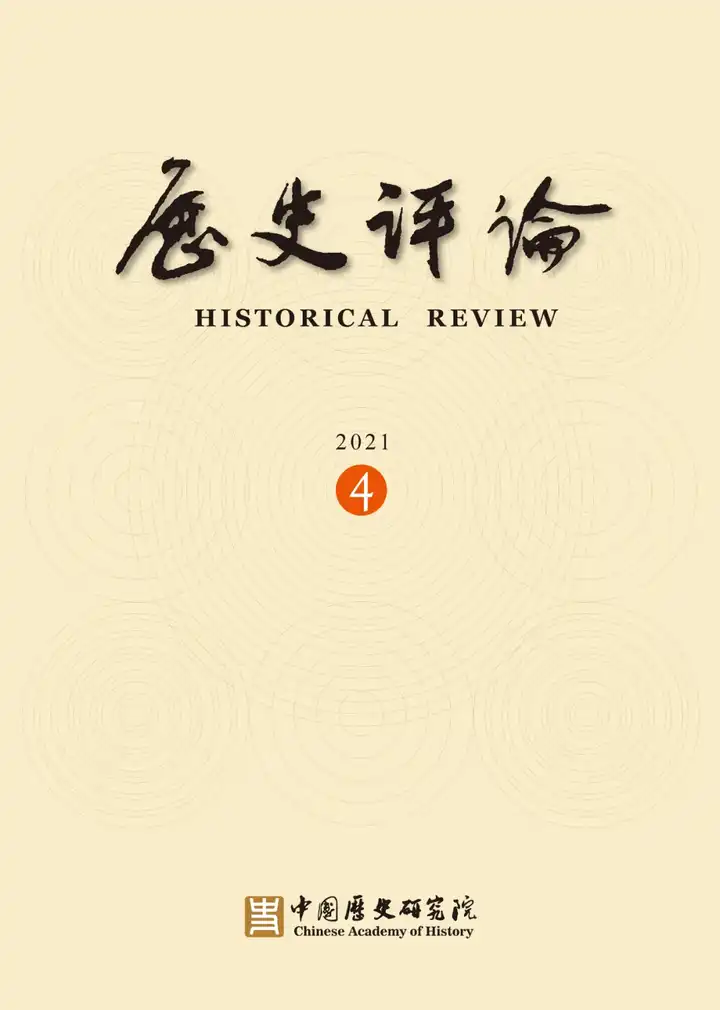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