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守甫 的回答基本阐释了在年鉴和勒高夫语境里这句话的意思,我要补充的是,为什么“大写的历史(Histoire)”的哲学会不断产生,而且为什么排斥理论的历史学家会不知不觉成为理论的玩物。
首先需要澄清几个概念:历史主义,历史哲学,普遍史,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实证主义史学(克罗齐嘴中的自然主义),以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经常喜欢谈的,结构与历史的张力。
历史哲学是一块混战的断层线地带,历史学家,哲学家(时不时还会有波普尔这类三方势力出来把局势搅得更加混乱)出于对对方的不了解往往不能展开正常的对话,因而造成严重的概念误用(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概念误用,是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乱用。从历史主义这个词的混乱可想而知(请先看我下面这个回答,不然不能理解我接下来的路径),我在个回答随便数了数,发现比我想得严重得多:
为了理清楚,我们需要在这些概念里分成两极,寻找近义概念,当然这种方法是很不严谨的,只能当做一种思考工具使用,更何况每一位学者使用这些词时意义各有偏重。除此之外,要注意的是,两极之间概念之间经常出现相互转化,两极仅仅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这些词汇靠近其中一极,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两极之间,因此频繁的误用自然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这一极:历史主义(这个思潮涉及经济学,哲学,法学,以及国家学,在这里只取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如德罗伊森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实证主义史学(自然主义,当然实证这个词是比较偏中性的,克罗齐用自然主义替换,我认为比较妥当,毕竟兰克的实证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断裂比较严重,至于中国史学语境下的实证主义就差的更远了)
关于孔德的实证主义,虽然可能有点多此一举,我还是把比较严谨的诠释附一下:
结构这一极:历史哲学(思辨的),普遍史(所谓的“大写的历史”),历史目的论(即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
我们先从普遍史的起源说起,有人把这个归为波里比阿,但我认为这与非常不妥,虽然波里比阿这里已经有普遍史的苗头,然而真正有代表性的还是基督教神学。弗雷森主教奥托(Bishop Otto of Freysing)的《双城:公元1146年之前的编年普世史》和雅克·贝尼格尼·鲍修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的《普世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奥托把人类历史进程分为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来讲述,明显受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窥测普遍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联系),他在《双城》中一方面描述了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这些世俗政权(世俗之城)的变迁,另一方面更着力描述了基督教世界(基督之城)的起源与发展变化。他提出,基督之城由虔诚的社群构成,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最初构成它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上帝的子民,然后这些人聚集在以色列,后来又由教会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形成基督教帝国。但是,奥托也认为,“我们的历史是基督之城的历史,但只要基督之城处在救赎途中的旅居地,就像‘把渔网撒进大海里’那样,其中所包含的人也会良莠不齐”。因此,在世界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中,基督之城与世俗之城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双城》中,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及其终结,就是这两个“城市”的变迁,而且其叙述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一切历史事件都成了人类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
鲍修埃的历史观像奥托一样把“神意”(DivineProvidence)看成历史变迁的主宰力量,并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历史目的论),并且按照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来叙述人类历史,这种二元性的叙述就是大写历史的经典特征,随后这种神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较经典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充斥地生产力决定论问题,可见于这篇文章。
近代历史学最大的转向就是编年史的消亡,即从黑格尔所说的,原初的历史(Original History)走向反思的历史(Reflective History)。在这个过度阶段,出现了语文学历史,诗性历史,讲演历史(克罗齐),并最终走向了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一个古老而又被注入新生力量的概念)、现实主义的历史(thePragmatical)、批判的历史(the Critical)和观念的历史(the historyof ideas) 。观念的历史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文化史说法,直到很晚才复兴,而批判的历史,比较接近德国实证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也是历史决定论的拥护者。
在梳理几个概念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异常的地方了,很多情况下,这两极概念之间是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兰克本人。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两极概念是相扶相依,浑然为一体的,克罗齐就是最早预见这个的人:历史决定论(历史)不断地在产生历史哲学(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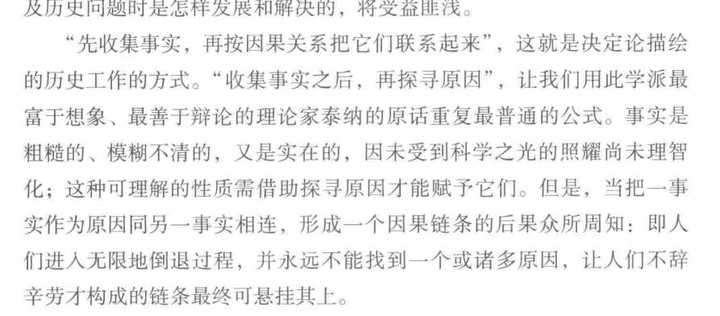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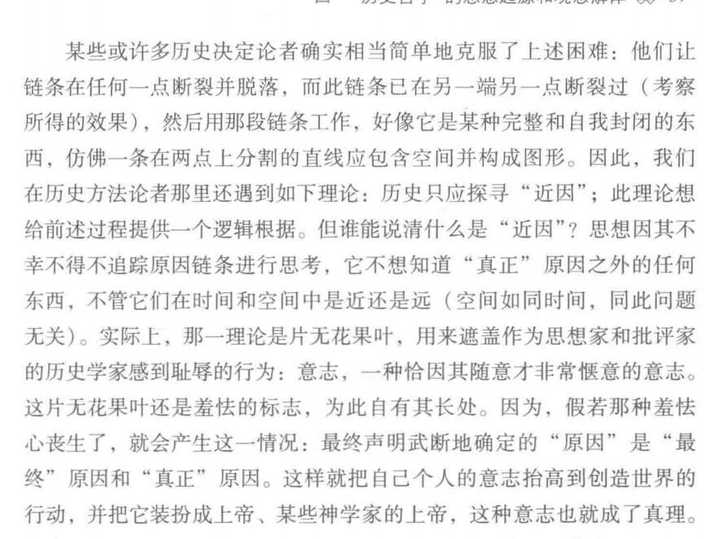
为了在事实之间努力生产链条(这是历史学家的立足之地,不然的话就会倒退到原始历史,回归到混沌的编年史母亲的怀抱之中),不动摇事实优先(这是历史学家的最后阵脚),历史学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越过历史决定论(历史),超越自然与原因,倒向对立的另一极:原因范畴的对立面,即所谓的目的范畴-历史哲学。因此,越是尊重事实,越是排斥理论,历史学家反而只会越往历史哲学,甚至是历史神学-上帝之手靠拢。这便是最荒谬的地方,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学最大的敌人,不是产生于历史之外的,恰恰相反,它是历史自身结构的运动中不断生产出来的冗余物,历史仰赖历史哲学这个最大的敌人成为历史。
如果说克罗齐的推理略显单薄匮乏,那么德里达则是从更根深蒂固的地方(虽然他并不谈历史)发现了这一点,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心不属于结构却又不知不觉被结构所替代,所控制的中心,二者之间一直维持着张力:
尽管它一直在现象的游戏中运作着,但它常常是被简约的,并通过赋予它一个中心或者给它指涉一个在场点、一个固定的源头这样完成这种简约”,在这一运动中,结构既能够启动又能取消这种“自由嬉戏”,“这种中心也关闭了由它所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自由嬉戏。所谓中心,就是这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织部分或子项的替换不再有可能”。因而这个中心不隶属于结构本身(结构阻止它,直到从理论上说替代它,控制它,同时又一直与它保持联系和一种张力关系)——是起源与终结、元力与终结目的。而结构概念仅仅存在于这个矛盾之中,却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中心”控制着各个可变要素,但是其自身本质处于“游戏”之外。“在中心,无数的符号替换在游戏着。这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场域的时刻,是中心或始源缺席中一切都变成了话语的时刻。
那么如何遏制去对抗历史哲学,这个由历史本身产生的敌人?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只有改变历史本身。想必题主也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关于如何使用历史的问题,有许多历史学家倒可能会站在福柯的立场上”。因为他为历史带来了不连续性,断裂,界限,序列,转换,而这一切最终把历史由围绕着中心的结构转化成为了一个弥散的空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是碎片化的历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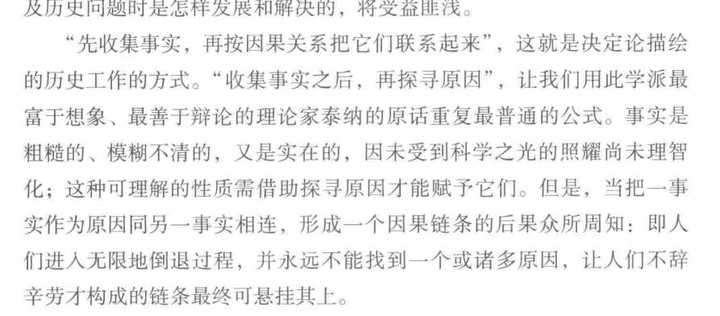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