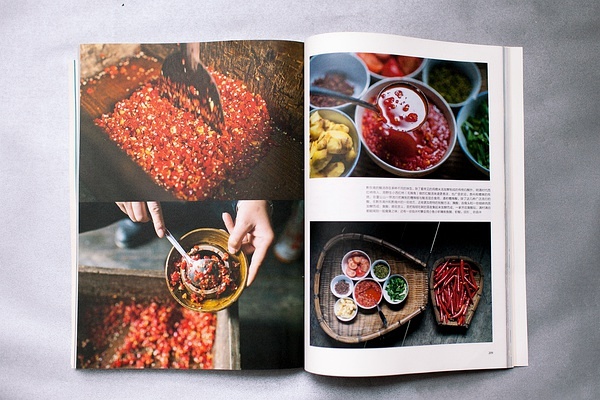
穿行于苗疆腹地撰文 萧春雷摄影 李贵云等三江并流黔东南黔东南有两个含义:一指贵州东南,是自 然地理区域概念;二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包括首府凯 里市和15个属县。黔东南位于云贵高原向 湘桂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地貌类型为低 山丘陵谷地,山多林密,溪涧纵横。我的 第一印象是,黔东南与福建的武夷山区、 戴云山区类似,都是以河谷盆地、山坡梯 田为主的稻作农业区。“贵州70%的土地是喀斯特地貌,干旱和 石漠化严重。清水江流域和都柳江流域是 最大的一片非喀斯特地貌,青山绿水,是 贵州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熊康宁教授 说。他是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 究院院长,专门研究喀斯特石漠化问题。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喀斯特地貌,就适宜 人居。“那么,为什么黔东南的发展比较落 后呢?”“我只能说,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黔 东南条件很好,水热条件好,森林植被 好。”他说,“在南方其他省份,这很平 常;可是在贵州,是难得的鱼米之乡。它 为什么落后?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比 如历史的、社会的,或交通的。那里是少 数民族地区,我记得以前去黎平坐车要两 天时间。”黔东南州有三条主要河流,平行东流:北 部的㵲阳河、中间的清水江流入湖南沅 江,属于长江水系;南部的都柳江流入广 西西江,属于珠江水系。
表面看来,清 水江与㵲阳河更亲近,一路并行,同归沅 江。其实二者差异很大。㵲阳河流域有喀 斯特岩层出露,作为湘黔道的一部分,汉 文化很早就进入了这一地区;而作为苗瑶 语族迁入通道的清水江,后来也积累了丰 富的汉文化,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苗、侗民族的共同家园,在文化上, 倒是苗岭山脉南北的两条河流十分亲密。 北面的清水江是仅次于乌江的贵州第二大 河,由黔南州的都匀市进入黔东南州,横 贯黔东南州腹部,汇集麻江、丹寨、凯 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黎 平、天柱10县市的水系,东出湖南,流域 面积广阔。南面的都柳江仅汇聚丹寨、榕江、从江和黎平等县诸水,流域面积较小, 最后南下西江。在这里,高大的苗岭并非阻 隔,反而是连接两个流域的通道。明清时期的苗疆腹地,指的就是黔东南清 水江、都柳江之间的苗岭山区。这里至今 散落着成千上万个侗乡苗寨。我们落脚的乌东苗寨农家乐的窗外是碧绿 的稻田、小溪,三四个赤条条的孩子正在 嬉闹玩水。这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了。乌 东是个大村,百余户人家坐落在山坡上, 吊脚楼鳞次栉比,但空空落落,偶尔才见 到一两个人影无声无息地飘过,估计很多 人出外打工了。乌东位于雷公山山腰,海拔约1300米, 两条小溪在村前交汇,再跳下万丈高崖。
村边有几丘水田,但多数梯田散落在村外 很远。雷公山是苗岭山脉主峰、黔东南最 高峰,海拔2179米,地处台江、雷山、剑 河、榕江四县交界处,也是清水江与都柳 江的分水岭。当地人称雷公山为牛皮箐, 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清咸丰、同治年间, 苗族英雄张秀眉起义,席卷整个黔东南, 最后败退到山高林密的雷公山,在乌东坡 兵败被俘,被押送长沙处死。从乌东到雷公山顶的公路很好,上山只花 了半个多小时。山顶气候迥异,灌木低 矮,山风呼啸,云雾湿漉漉的,仿佛拧得 出水来。最高处是一片空地,有个水坑, 也不知装的是雨水还是泉水,反正大家都 说是张秀眉留下的水井。四顾白雾茫茫, 一对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的中年夫妻说要 等太阳,在风中瑟缩。我匆匆下山。其实山腰才适合远眺。偶尔,强劲的山风 把云层吹破,眼前豁然开朗,但见群峰连绵,山谷旷远,屋舍、田畴与公路,像 串珠一样散落在青翠的山间。阳光宛如魔 毯,闪闪发亮,在林梢之上快速移动。袅 袅炊烟,为这片高远的天地增添了人间的 安详与温馨。清水江南岸的雷公山区,深山长谷,深邃 迷离,是明代生苗界、清代苗疆的心脏, 也是清水江流域开发最晚的地区。如今, 既然公路已通达雷公山顶,山川的神秘涣 然冰释,吸引我们的,唯有生存于斯的民 族和他们的文化了。
正因为开发最晚,雷 公山地区的苗族传统文化最为丰厚。清水江:重要的苗瑶通道“在国家力量进入以前,没人知道清水 江。”林芊老师说,“徐霞客下河游过 泳,但他不知道是清水江,在游记里称为 龙头河。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只把 剑河到锦屏这段河流称为清水江。原住居 民的视野更窄,只知道他眼前的这一段叫 作剑江、马尾河、鸡贾河、平定河、凯里 河、重安江,没有整条河的概念。清雍正 时期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才出现清水江全 流域的称呼。清水江文化内涵很少。苗 族、侗族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但没有对清 水江的赞美,没有母亲河的观念,甚至没 有河神、水神。清水江是孤独的河。”林芊是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主笔完成 的著作《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 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 的视角》,第一次全景描绘了清水江流域 的开发进程。在他看来,清水江是很晚才 被人们发现的一条江。他的叙述让我想起,苗族是山地民族,他 们关于山河的概念与汉族不同。汉族在平原盆地耕作,舟楫往来,河流是连接各个 区域的力量,十分重要。苗族定居深山, 远离大河,连接各村寨的是一条条山道。 莽莽苍苍的苗岭,才是他们的真正家园, 大山南北都柳江与清水江的民族文化景 观,也因此连成一体。
在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我采访了 著名学者张新民教授。所谓清水江学,是 以学术界发现的明末以来数万件“清水江 文书”为基础,建构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学 科。张新民先生在这一领域居功至伟。他 告诉我:“清水江流域现有的民族都是后 来迁入的,苗族和侗族都不是原住民族。 从考古的材料看,春秋以前,清水江流域 的文化是从上游往下游走,战国以后从下 游往上走。我们无法确认他们的族属,但 显然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包括原住民族文 化、南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三种成分。”我在探究黔东南地区现有民族的来源时却 遇到问题。请教过几位相关学者,都不愿 意回答,有位学者善意提醒我这个问题很 敏感。我不得要领,只好阅读学术论著, 自己慢慢厘清。黔东南地区的民族情况大 略如下。汉代北盘江流域有个夜郎国,是我们知道 的贵州最早的地方政权,属于濮人、僚 人。许多学者认为,今天的仡佬族是僚人 的后裔。但夜郎国的势力似乎不及清水江 流域。汉唐时期,苗瑶语族生活在湘西武陵地 区,壮侗语族生活在岭南,都还没有进入 贵州。大约唐以后,苗瑶语族沿清水江西上,壮侗语族沿融江北上,两大民族集团 在黔东南地区杂居,汉人闹不清楚,所以 古籍里统称“百苗”“峒苗”“溪洞”。
明清以后,苗瑶语族族群逐渐分化出苗、 瑶等现代民族,壮侗语族族群分化出壮、 侗、水、布依等现代民族。黔东南州如今人口460万,苗族占42%, 侗族占29%,汉族占18%,然后依次是布 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等,各 民族形成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苗 族散布全境,但在清水江中游地区占据绝 对优势;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条大江下游的 黎平、天柱、从江、榕江、锦屏、三穗等 县;汉族集中于凯里市和㵲阳河流域的黄 平、镇远和岑巩县。黔东南许多地方流行一句民谚,“汉家住 街头,侗家住水头,苗家住山头”,颇能 反映三大民族的居住特点:汉族聚居在城 镇,侗族临水而居,苗族深入大山。㵲阳河:汉文化进入苗疆镇远古城就在㵲阳河畔,河水蜿蜒,穿城 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均 为明代所建,远观仿佛一幅太极图。城内 有街巷、牌坊、亭台、楼阁、会馆、祠 庙,对岸的青龙洞建筑群依山就势,翘角 飞檐。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这样一座浓 郁的汉式风格城池,颇让人意外。但仔细 一想,也不奇怪。贵州在中国的位置,按古人的说法是“不 内不边”“西南之奥区”,大意是既非内 地,又算不上边疆,所以受到中央政府的 忽视,变得神秘。
的确,广西和云南边疆 都更值得重视。偏偏早期内地通往云南的 两条路都绕过了贵州,一条是成都经昭通 到昆明的川滇道;另一条是宋代的湘桂 滇道,很远,从湖南先南下广西融水、宜 州,再西上昆明。不过唐宋时期云南在搞割据,也没多少人去南诏国、大理国。元朝把云南收归版图,新开辟了一条湘黔 路,从沅陵、芷江、岑巩、镇远、重安、 贵阳、安顺至昆明,大大缩短了云南与北 京的距离。这条经过黔东南的驿道,纵贯 㵲阳河流域,紧邻苗疆,所以元朝就在镇 远设府控守。镇远历来有“滇楚锁钥,黔 东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清 时期,随着汉族兵士、商人、佃户和流民 大量聚集,以镇远城为中心的㵲阳河流域 率先被开发。元代黔东南地区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 个行省管辖。贵州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建省的,目的也是为了经营云南,保 障通道安全。贵州的开发,黔西、黔北最 早,黔东南最迟。我们看明朝的地图,黔 东南地区仅分设都匀、镇远、黎平和平越 军民四府。西边的都匀府镇守清水江上 游,北边的镇远府威慑清水江中游,东边 的黎平府控制都柳江和清水江下游。三座 府城,是明中央政府在黔东南周边打下的 三根铁桩,围起一个等腰三角形,正好是 清水江南岸的崇山峻岭。
这片化外之地, 明人称之为“生苗界”,从来没有国家力 量深入其中。黎平位于贵州东南角,是中国侗族人口最 多的县,号称“侗族之都”。作为一座控 守黔湘桂边界、历史悠久的卫城、府城, 黎平城内的汉化程度相当高,走在青砖灰 瓦马头墙的翘街上,看城门城楼,恍然置 身于江南城镇。明代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在边疆地区 设置了很多卫城、所城,屯军驻守。黎平 古城最初为五开卫城,附近的隆里古城则 是一座千户所城。隆里古城坐落在宽阔的盆地上,城内以衙署为中心,街巷井然, 徽派建筑,有东南西北四座城楼。明军亦 兵亦农,耕田种菜,俨然一个汉族集镇。 许多军户落地生根,绵延至今,依然保持 着传统的汉族生活方式。黔东南的每一座卫所、府县,不但是壁垒 森严的军事据点,还是汉文化的样本和传 播基地。军士们带来内地的作物品种、先 进的耕作技术、产权和交换的观念、祖先 崇拜和神明信仰,都对当地民族产生了巨 大的冲击。如今,无论苗族还是侗族,都有了姓氏、 祠堂,甚至郡望——多数姓氏均声称来 自江西省吉安府。数万件清水江文书的发 现,证明明清时期汉族的财产、契约和 法律观念,已经渗透进当地民族的生活之 中。《黔南识略》记乾隆年间的黎平府 说:“苗有六种,洞苗已向化久矣,男子 耕读与汉民无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 汉人通姻。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西 苗近亦多薙发读书应试,惟妇女服饰仍旧 习旧俗。”少数民族都开始裹小脚、参加 科举了,足见汉化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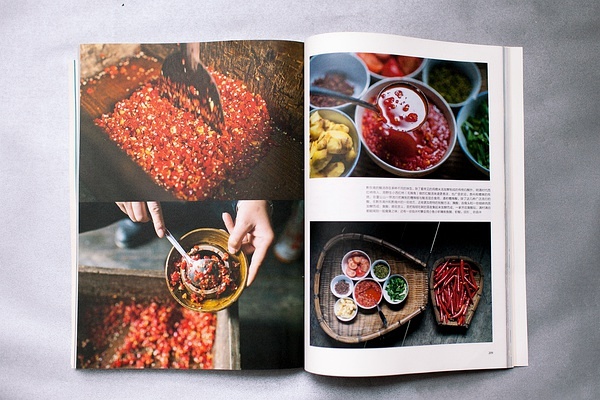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