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载李学勤《文物研究与历史研究》,见《中国文物报》1988年3月11日。曾收入《追溯・考据・古文明: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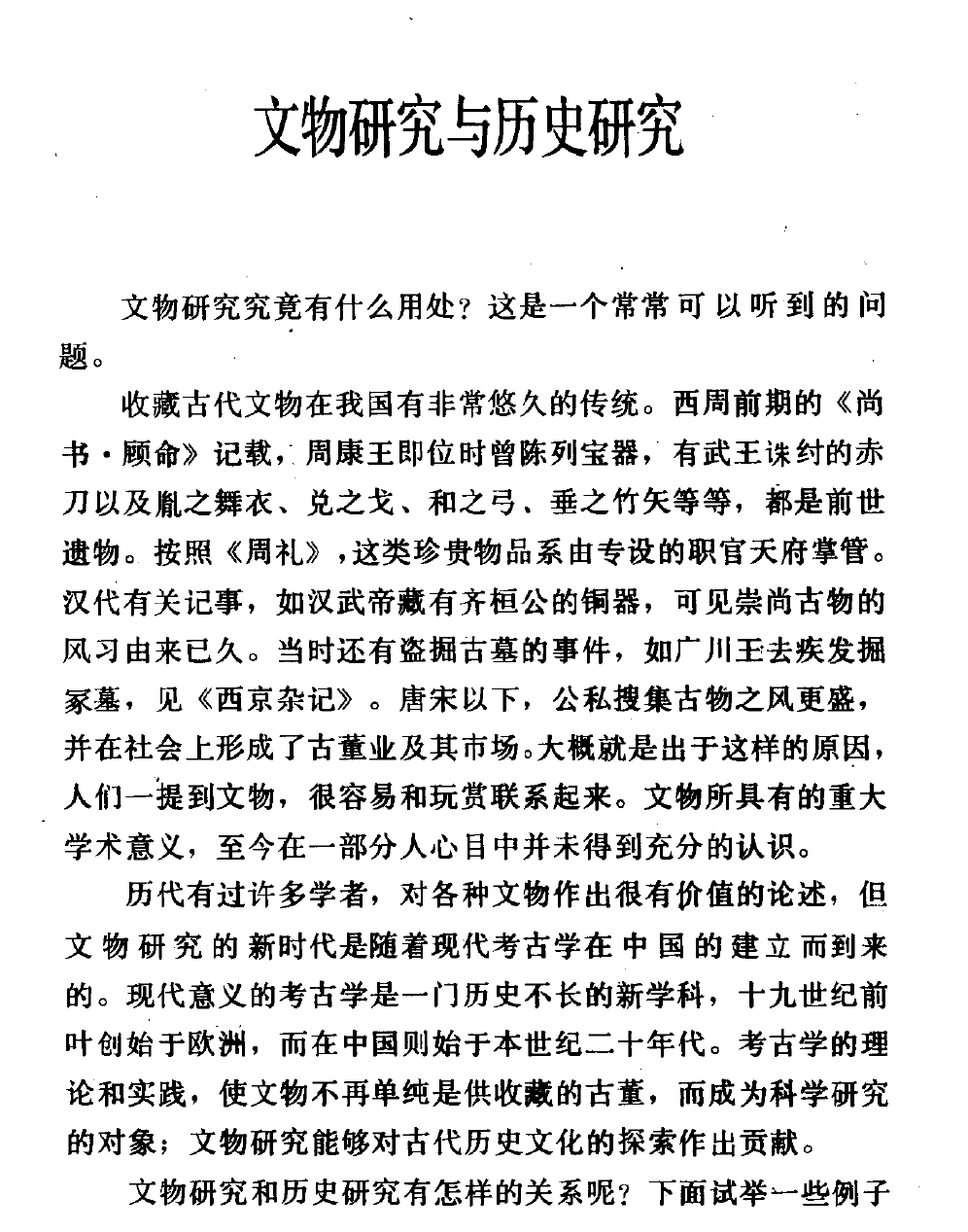
文物研究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听到的问题。
收藏古代文物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西周前期的《尚书·顾命》记载,周康王即位时曾陈列宝器,有武王诛纣的赤刀以及胤之舞衣、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等等,都是前世遗物。按照《周礼》,这类珍贵物品系由专设的职官天府掌管。汉代有关记事,如汉武帝藏有齐桓公的铜器,可见崇尚古物的风习由来已久。当时还有盗掘古墓的事件,如广川王去疾发掘冢墓,见《西京杂记》。唐宋以下,公私搜集古物之风更盛,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古董业及其市场。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一提到文物,很容易和玩赏联系起来。文物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至今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历代有过许多学者,对各种文物作出很有价值的论述,但文物研究的新时代是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而到来的。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是一门历史不长的新学科,十九世纪前叶创始于欧洲,而在中国则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使文物不再单纯是供收藏的古董,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文物研究能够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作出贡献。
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怎样的关系呢?下面试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文明的起源
从有无文字的历史记录来看,人类历史可分为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史前时期远古荒昧,尚无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学及人类学、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原史时期虽有文字记载,然数量较少,存在许多空白,文物考古材料在研究中有重要作用。历史时期已有较多文献,但文物仍可对文献记载印证补充。文物研究对于这三个时期的研究所居地位不同,而均有很高的价值。
考古学对史前时期研究的意义,是大家容易理解的。我国广大疆域上的史前史,正在田野工作中逐渐被揭示出来。上古传流下来的种种传说,在疑古思潮中曾被认为伪造。尹达同志几年前为《史前研究》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指出这种观点的不确。他说,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中国文明是世界有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环绕这一课题,可以提出农业的起源、金属器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城市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我们的考古工作业已给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不少可贯的线索。
以近年确定的裴李岗文化为例。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发掘证明,这种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其农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参加发掘的学者认为它可与西亚的新月形地带相比,“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①。
最近报纸上登载了河南舞阳贾湖发现龟甲刻划符号的消息。龟甲属裴李岗文化,刻划符号清晰明确,比西安半坡等地仰韶文化陶器的刻划符号又早了许多。我们曾经说明,根据近期外国学者的研究,古埃及文字可能是从陶器符号发展来的。新发现的龟甲符号,可能同后来商代的甲骨文字有某种联系。这种龟甲不象殷墟卜甲那样经过烧灼,但烧灼并不是用甲骨占卜的唯一方式,还有所谓“冷卜法”②,所以不能率尔否定裴李岗龟甲可能与甲骨文间存在渊源关系。
文物与文献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保存了大量文献,以致在世界上被称为历史的民族。古文献是否可信,每每有人置疑,这就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去论证。文物常能作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据。
以文物印证文献,早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大家都推崇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功绩,他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通过研究殷墟甲骨,证明《史记·殷本纪》基本可信。由于甲骨研究和殷墟发掘,商代的存在成为不争之事实。谈这一点,今天或许有人感觉奇怪,可是在疑古思潮的年代,古史成为朦胧的空白,商代的确立实在是重建古史的奠基石。近年新发现的周原甲骨文,又证实《史记·周本纪》所载商周关系也颇可信,周君确是商朝的诸侯之一,作过西伯。至于《夏本纪》,看来总也有被证明的机会。
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的证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
例如《逸周书》中有《祭公》一篇,曾为《礼记》所引用,内容为周公之孙祭公谋父临终对周穆王的劝诫,很重要,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篇中好多词语可与金文对照,如“用克龛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龛”字用法同于史墙盘“龛事厥辟”;“我亦维有若祖祭公之执和周国,保王家”,“执和”即史墙盘、师询簋的“
龢”;“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也可对比毛公鼎“欲汝弗以乃辟函于艰”。这篇文字为西周原作无疑。
整本的书有反复为出土文物遗存证明的,《左传》是一个佳例。《左传》所记人、地、事迹,多与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器物铭文相合,是这部要籍近来很少人再加怀疑的主要原因。《周礼》和《左传》一样,长期蒙受怀疑的厄运,其内容也在文物研究中得有越来越多的证明,也许不久会为学术界多数所承认。
可以和文献印证的,当然不限于有文字的文物。考古发现的许多种器物,在遗存中见到的不少现象,都能与文献比较,从而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比如在好多地点新石器文化人骨所见的拔牙习俗,已有论著以之同《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的“凿齿”联系起来。晋郭璞注《山海经》,说:“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主张“凿齿”即拔牙的文章多予否定。实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些玉器上,屡见口中出齿如凿的人面形象,虽无五六尺长,与郭璞所说还是一致的。揣想当时风俗,在拔牙后有时要安装某种獠牙,有其宗教性的含义。这种习俗,或者在考古工作中能够得到证实。
文物中的文献
不少关于中国书籍历史的论作,把甲骨文、金文、碑刻等都罗列在内,这些其实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的书籍。在文物范围中确有一部分是古代的书,如简牍、帛书、卷子抄本之类,对于研究历史自然有其特殊意义。七十年代以来,各地先后发现很多批战国至汉代的简牍和帛书,陆续整理发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讨是很大的推动。有些发现的影响,也许和汉晋的孔壁中经、汲冢竹书一样,要到若干年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可能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看法的修正。很多年来,关于古书真伪论辩纷纭。现在我们有机会目睹古代书籍的原貌,不难看出古书的形成都要经历较长的过程,有不少改动变化。如果用静止的观点去“审判”古书,不免造成误解。关于古书形成和传统的新认识,或许使学术文化史的好多部分要重新考虑。
新发现的简牍帛书主要在战国到汉的时期,从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周汉之际文化传流的真相。秦代焚书坑儒,历来被指为学术文化史上的大事,但其作用究竟如何,因为材料太少,前人未能深入论述。过去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其卷一论汉初学术,尽力钩稽,也不过薄薄数页,语不能详。竹简、帛书的新发现,刚好补充了这方面的缺环,在人们面前展开了汉初学术怎样在秦火之后重现繁荣的绚丽画卷。
这一类发现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应推云梦睡虎地竹简中的秦律和律说(《法律答问》)。此部分简只有五百余支,内容却十分丰富,以法律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简文的公布立即使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国内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研究秦简的论著,盛况可以想见。令人兴奋的是,近来在江陵张家山又出土了汉律,内涵的重要不在秦律之下。最近,这批汉律的整理释文工作已基本完成,其发表将在学术界得到强烈反响是可以想见的。
科技史与思想史
文物研究与科技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彼此的研究也可说是互相依存的。科技史上的许多新论点,都来自考古文物的研究。读者只要翻阅一下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便能知其大略。
藁城台西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是极有兴趣的事例。钺的铁刃经鉴定为陨铁,从而在考古和冶金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近来有学者指出,根据这件钺和其他一些有关器物的特点,陨铁器的加工、制作在当时曾延续一个相当时期,并逐步有所改进,这可能对冶铁术的发生具有某种影响③。这个例子表明,我国科技史的研究不能不与文物研究相结合。目前因物质条件限制,我们还不能对文物进行全面的科学技术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方面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文物研究同思想史的关系,还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曾说过,如果以为“考古学的收获仅仅代表历史上的物质文化,这个观点恐怕是失之片面的。被称为锄头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所得(除出土的古代书籍外),固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开的。无论是建筑遗址,还是墓葬发现的各种器物,都寄托着古人的思想和观念。”④
今年是龙年。大家最近已看到有关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有用蚌壳排成龙形的报道。这种龙夭矫攫拏,已具备后世龙的各种因素。濮阳在历史上称为帝丘,有很多传说记载,早期龙在那里出现,殊发人深思。这在思想文化史上有很大意义。
去年秋天开始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1985—1986)”,展出了浙江余杭反山的良渚文化玉器,其工细精美,令观众叹绝。所陈有一件白色琮形器,高17.5厘米⑤,侧视如琮,俯视如璧。按《周礼》所载,璧用以礼天,琮用以礼地。此器结合璧、琮二者,正象天圆地方,似乎有关的观念和礼制当时已经有了。类似的象征天地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晚周秦汉的六博、铜镜、日晷等物。
走向新的学科
当前我国文物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沟通尚嫌不够,在高等教育中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博物馆专业间的横向联系也有待加强。把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对双方都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建立有开拓意义的新的学科。
在几年前《文史知识》编辑部召开的一次会上,我提议过开展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什么是比较文明史,不妨用一两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从来是个聚讼的问题。十九世纪比利时学者拉沃莱的《财产及其原始形态》,则专设《英国与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一章,主张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英国同出一辙。他使用的方法是比较研究,我们想对他的看法表示意见,也必须利用文献、文物作比较研究。有关历史的很多问题,如人类各种科技发明、各种艺术形式是在哪里创始的,有怎样的传播途径,怎样的影响变化,都有必要在各种古代文明间互相比较。
文明的比较当然要注意其间彼此往来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周围各国家民族的比较应受到特别重视。不过,即使是互相没有直接联系的古代文明,也可进行比较,例如中国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和美洲的古代文明,如详细加以对比,都会有所收获。近年已有外国学者作过若干试探。
可能建立的新学科当然不止比较文明史,在这里不能缕述。
总之,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现代考古学本来是以撰写历史为职志。中译本刚刚出版的英国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在回顾了考古学兴起发展的历程后指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观念,考古学又只能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水平,因而永远存在着出现新古物学的危险。”⑥这位考古学史专家的话,值得我们引为借鉴。
脚
注

①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②李亨求:《渤海沿岸早期无字卜骨之研究》,台湾《故宫季刊》第16卷第1、3期。
③华觉明:《陨铁、陨铁器和冶铁术的发生》,《中国冶铸史论集》附文一。
④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379页。
⑤Orientations,1987年12月号,第48页。
⑥《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321页。
经典重读栏目往期文章可进入公众号,点击往期回顾-经典重读中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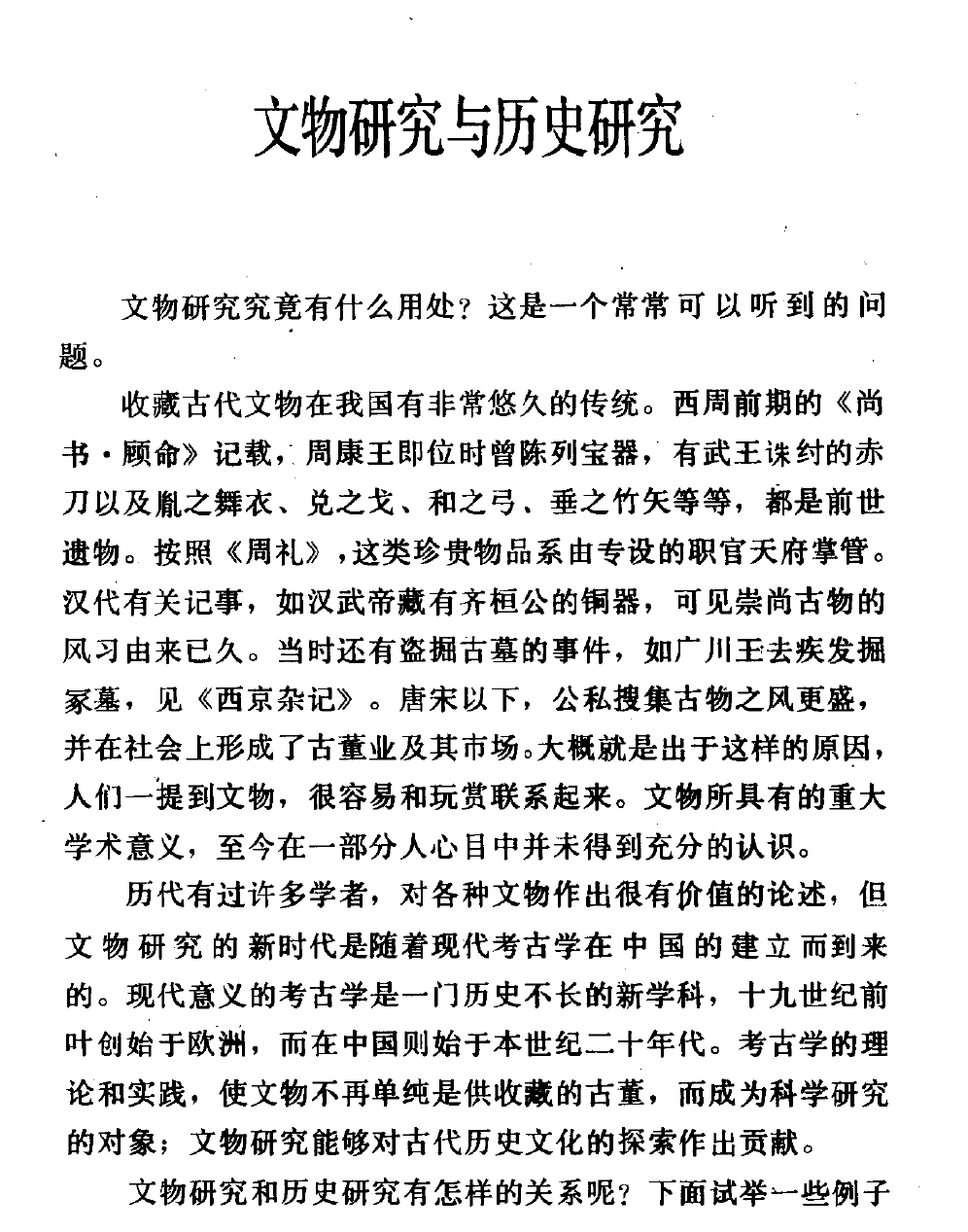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