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园鸣谢
刻在骨子里的神灵
段永朝
本文为段永朝老师为
推荐序

作者:尼古拉斯. 韦德(Nicholas Wade)
【按】电子工业出版社近几年,出版了大量优秀图书,包括多克.希尔斯的《意愿经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以及尼古拉斯.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黎明之前》、《天生的烦恼》和《信仰的本能》。经征询出版社同意,在本公号转发去年为《信仰的本能》撰写的推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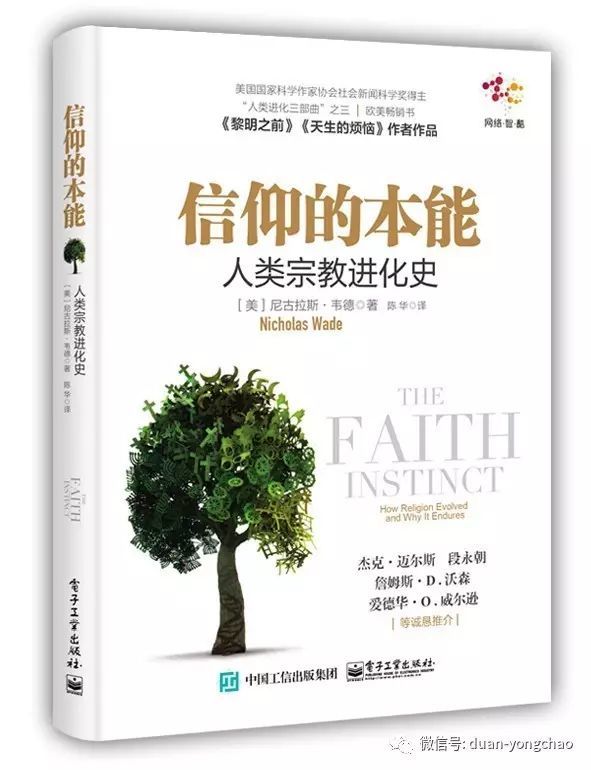
尼古拉斯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中文版,终于出齐了。它们是——《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和眼下您手里这本《信仰的本能:人类宗教进化史》。
基因、人类、进化与信仰,这几个词汇显然不是这几年才热起来的。比如基因这个词语首见于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的《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人类”这一词语,如果用类型学角度看,应归功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35年提出的,关于植物、动物命名的“双名法”;进化,则因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风行世界。信仰,这个词难以追溯词源学意义上的出处,但从传说中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编撰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埃及亡灵书》中,已经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人类对冥冥之中神灵的敬畏、虔信和膜拜。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年——很难说从哪一年开始,悄然出现了这样一股思潮和冲动:重读、重思,乃至重新诠释这些耳熟能详,凝固在教科书中的语汇。
这背后透着什么样的觉醒,亦或忧虑?
一、基因
1987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有一篇重要的论文,作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他的两个学生(RebeccaCam , Mark Stoneking),论文的题目是“线粒体DNA和人类进化”。
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彻底转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率先从古人类化石中提取出DNA的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Bryan Sykes,将依据这一方法做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形象地称作“夏娃的七个女儿”。
在人类与他的灵长类远亲分道扬镳的旅途中,在寒冷的冰河期与温暖的间冰期,人类先祖穿越中非大峡谷抵达尼罗河三角平原,辗转来到两河流域、爱琴海周边,又长途跋涉远赴恒河、南亚,来到黃河岸边的一次又一次迁徙中,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回答,太多的谜底需要揭开。
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从此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精准度大大提高的工具:DNA。在《黎明之前》这部书中,韦德写道:有DNA这个工具在手,我们可以为达尔文所预见的框架添砖加瓦。
萦绕在人类脑海中数千年的问题,又一次涌上心头:传说中的伊甸园在非洲,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体毛是什么情况下褪去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催生了语言?第一拢篝火、第一爿篱笆墙,第一处村落如何形成?人类又如何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意味着什么?
原始部落中的财产、婚配、祭祀、舞蹈、音乐,是何种形态?它的生发机制和文化寓意是什么?群体如何形成?维系族群秩序的凝聚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亦或二者兼有?又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基因,基因的遗传、突变、嫁接,如何扮演人类进化道路上那只神秘的“上帝之手”?
一大波又一大波问题袭来。
对今天的普通大众来说,对基因问题着迷,除了那些不断冒出来的好奇的问题之外,为基因问题所困还有一个因由,就是转基因,以及基因编辑。
2015年度诺贝尔“生命科学突破奖”颁发给了发现基因组编辑工具“CRISPR / Cas9”的两位女科学家——珍妮弗·杜德娜和艾曼纽·夏邦杰。传统的基因重组、嫁接技术,似乎开启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有了更加精细的画面。基因敲除技术、特异突变引入工具、定点转基因理论,已经为人工合成生命展示了诱人的前景:新生命、新物种,乃至生命的永生,令人展开无限的遐想。
在人们依然被复杂、神秘的基因学搞得头晕眼花、且心神不宁的时候,将这一术语与本能、进化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将会引发怎样的嬗变?
二、本能
如果说,基因是从“科学”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一个用语的话,“本能”则是从“人文”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
一次应激反应、一次脸红心跳,当我们说这是人的“本能”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用韦德的第二本书《天生的烦恼》中的观点来说,本能即意味着“与生俱来”。但是,停留在承认某些特质与生俱来这个层面,远远不能解释人类个体与群体、历史与演进中的复杂性。需要面对的,恰恰是“本能何以在演化中铸就?以及如何铸就的?”这样的问题。
1960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里,一项由吉布森和沃克(Gibson & Walk)主持的实验正在进行。36名6-14个月大的婴儿,被放在一个铺着格子床单的床上,床上有一块透明玻璃,玻璃延伸出床边,与地面形成一个类似悬崖的落差。格子床单垂着铺到地面。
孩子的母亲在“悬崖”这边呼唤婴儿,看孩子能否顺利地爬过来。
实验的结果令人深思。只有3名孩子非常迟疑、犹豫地爬过了床沿,其余的孩子都以各种方式回避这个貌似“悬崖”的危险地带。
孩子是如何知道他即将面临深渊的危险的?难道“如临深渊”真的是一种刻写在记忆深处的本能反应?动物心理学家们按照同样的思路检验了小鸡、小山羊、小绵羊,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猜测:避免失足落崖,真的是生命的本能。
对本能的研究,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长期游离于机械论者的视野之外。在机械论者看来,这个世界总是可以拆解成说得清、道得明的零部件,按照一定的原理装配到一起。机械论者认为这个世界像钟表一样精确、可靠。直觉、本能、意识等等,这些无法直接拿在手中的东西,完全不入他们的法眼。
更要命的是,曾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这种精确、可拆分的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与物种演化联系在一起,断定物种的进化是按照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的。
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反对的,恰恰是这种机械的、还原论的世界观。除了反对将本能与机械的世界观挂钩之外,韦德还有更大的抱负,他试图解释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地带:宗教的来源。
三、信仰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理解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艰深的事情,或许因为缺乏直接的体验,又或许因为缺乏文化底层的纽带。即便有一些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无神论者也只能将其归之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甚至轻言迷信而不屑。当然,信仰与宗教也还是两回事情。
韦德的三部曲一路写下来,最终触及到这个“坚硬”的难题:将信仰与本能联系在一起,是否可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书的意义就在于“证明本能的宗教行为的确是人类本质进化的一部分”(p18)。并且,这种行为至少在五万年之前就已经印刻在我们的神经线路之中。
这一“刻写”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韦德的分析,对那些走出非洲、处于大迁徙中的氏族部落的人们来说,与超自然的神灵直接接触的方式,不外乎稀奇古怪的梦境、神情恍惚的嘶喊、癫狂的舞蹈,还有丝竹鼓器发出的音乐声。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以万年为尺度的艰难进程。这依然是宗教的胚芽,是野性的、初朴的宗教情感。
宗教得以成型,有赖于祭祀、占卜的仪式化,有赖于祭司阶层的出现。韦德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平权结构,在定居之后出现劳动分工,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威权体系了,祭司出现了。祭祀代替了舞蹈,大祭司垄断了与神灵晤谈的通道。
伴随祭司阶层的,是占卜体系的出现:“在狩猎采集者中,宗教行为要求群体的所有成员全副身心投入,参与整夜激昂的仪式。定居社会的宗教则冷静得多,注重牧师所叙述得交易,经常对异议者或异教者施以高压。牧师们还试图压制宗教得狂野一面,认识到它们对现存体制的威胁。”(P150)
韦德认为,宗教思想是进化来的。宗教思想有其生物学基础,韦德列举的证据包括梦境、恐惧、恍惚的心智状态、原始舞蹈和音乐等等。这些初朴的意向,最终与作为人的道德感纠缠在一起。韦德强调,“宗教和道德共享同一个来源于进化行为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植根于情感。”(P29)
宗教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强势纽带”,在于其以仪式感、神秘感、崇高感,霸占了“道德情操”。“一种新型的行为进化而来,它促使个人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新的行为即是宗教本能,它把道德直觉强加于人,使得他们对违反直觉的后果深感恐惧。”(p49)
在这一点上,韦德的观点与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类似。涂尔干认为,宗教是针对神灵的实践和行为的统一系统。换句话说,信仰和行为统一成一个道德群体,这就是大家共同服从的教会。
不过,与涂尔干略显空泛的、思辨色彩浓厚的论证相比,韦德充分借助了现代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新近成果。他花费大量笔墨,讨论了道德的生理学基础,以期将“信仰植根于本能”这一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不管韦德是否达成了这一宏愿,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显示其学术探究的可嘉勇气了。
四、进化
为了寻求宗教进化的生物学证据,韦德可谓下足了功夫。但是,要圆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同时接受这种一种局面:善恶本能在生物基因中同时并存。宗教情感结合道德情操的演化,似乎在暗示从本能、天性来说,善的力量本能地压倒了恶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点点。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为此争吵了数百年。祭司、国王、修士、教皇、占卜者、游吟诗人们,为此争吵了数千年。
在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之光的旗帜下,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断言,“我们的晚饭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赐,而是来自他们的私利。”这一断言为私利正名、为财富壮胆,信奉勤勉、辛劳的清教徒们,获得了理论的强力支撑。然而,以今天的观点看,韦德在面对“自私的基因”时,也不免左右为难。
按韦德的断言,“因遗传形成的神经线路是宗教行为的基础,这在狩猎采集时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P69),然而,宗教如何在适应这种漫长生物演化的进程中,保持其内在的“本能”呢?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都认为宗教不具有这种内在的适应性。
韦德不同意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比起不信超自然力量的人和群体,愿意相信这种力量的人民就会形成更为和谐的社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对超自然信仰的倾向就会为自然选择所偏爱。”(P87)韦德进而问道,如果宗教具有适应性,那么它是如何进化的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但出现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出现在群体层面。这一结论得到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支持。
韦德断言,“5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的时候,所有宗教元素已经存在,被古人类的所有后代所继承。”(P87-88)这一结论虽然有待更多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试图将宗教动因与本能挂钩,着实体现了当代学者试图拯救宗教的内心冲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宗教在产生社会资本中的作用被低估了。
被法兰克福学派猛烈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在步入20世纪后不免步履蹒跚。虔诚的基督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与日本佛教人士池田大作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后以《展望21世纪》为题出版。两位饱含宗教情怀的学者,对宗教精神的失落充满了忧虑。如何重建信任,不仅是说重新对信任树立信心,而是说重新理解信任,重新回到辽远的过去,从宗教萌生的远古土壤中去寻求灵感和帮助。
宗教精神的复兴,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五、未来
与其说韦德提供了一个结论,不如说韦德提出了一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视角。这一点从本书第九章的标题“宗教的生态学”可以体会。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象征着高级宗教介入世俗世界的开端。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两千余年的世界文明史,孕育出东西两大系列六种高级宗教,包括东方的印度教和佛教,西方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共同本性是:宣称有某种超越人类精神的终极存在,立志祛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原罪,提供解脱世间痛苦的途径。
高级宗教与世俗帝国的冲突,成为主宰文明走向的一股强大力量。基督教会初创时期与罗马帝国的冲突,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轫于犹太圣经传统的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是信奉一神教的高级宗教。近2000年的演化史中,除佛教之外的这些高级宗教,无不演绎着一出又一出的征伐和屠戮。他们都声称遵从圣经的谕示:“上帝赐福于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及大地,去征服海中之鱼,天上之鸟,及地上的所有走兽。”(《圣经创世纪》1:28)
对道德的诠释、对秩序的向往、对威权的捍卫,成为高级宗教证明其正当性、合目的性的内在动力。韦德对此评论说,“宗教的基础是与超自然力量的谈判,促使神灵颁布该社会领袖们认为最为适宜的规则。”(P219)
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争夺耶路撒冷,以及以拯救的名义灭绝阿兹特克人,这一切都是在以教精神的感召,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人们不禁要问,宗教为何如此令人恐惧?团聚社会的同时,也让人癫狂?无论教派之争,还是信仰之战,每一个宗教团体的人们,都坚定认为真理在握,上帝在自己这一边。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教运动之后的近500年来,基督教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腐朽、堕落的教会阶层遭到唾弃,子民通过自己的方式阅读、解释、认同圣经的道路被打通,节俭、勤勉、辛勤劳作的新教徒,找到了亲近上帝、承接恩典的新的方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灵魂的新教伦理,成为现代国家崛起的精神支柱。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的100年里不幸堕入了宗教冷漠、疏离的时期。韦德注意到,在欧洲,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口比例,法国从1975年的22%,下降到1998年的5%;德国则从1975年的26%,下降到1998年的15%。上世纪末,伦敦《经济学人》杂志曾堂而皇之地刊登出一幅上帝的讣告。
韦德承认,“宗教退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P283)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结论。宗教真的没必要了吗?韦德认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宗教的根本元素不是神学,而是道德。“与教会失去直接政治力量相比,它在道德权威的衰落就比较难以接受。”(P284)
“能不能有无神的宗教?”(P286),比如佛教。韦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提法事实上在汤因比的历史思想中曾经不断出现,也是脱胎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过程神学”的某种折射(《过程神学》,小约翰.B.科布 / 大卫·雷·格里芬)。所谓“过程思想”,即认为上帝永远不能单独创造,而是一种与被创造物的共同创造,在这种持续创造中的上帝的作用,随着每一能量事件的自我创造,把最初的目的赋予每一能量事件。
韦德这样问道,“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宗教转变成更为适合先进时代呢?三个一神教的产生是为了适应许多世纪前的社会条件。他们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永远持续,除非它们变成一些莫扎特的著名歌剧,让人百听不厌。但莫扎特并不是音乐世界里的完美终点。”(p290)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汤因比对佛教千余年平和、宁静的传播方式所感染、打动。在为中文版《展望21世纪》所撰写的序言里,两位对话者表达了这样的观察:“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其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
汤因比本人更是毫不犹豫地将21世纪称为“中国的世纪”。然而,我在读毕韦德的三部曲之后,却久久不能释怀:为什么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从莱布尼茨、白晋、张诚到马戈尔尼,从汤因比、荣格、海德格尔到普里高津,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智慧的打开度的时候,我们却与世界一再地擦肩而过,对整个人类的进化洪流与脉络显得如此陌生?
20余年前,伴随“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深深地卷入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今日之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网络大国。然而,对整个世界似乎依然陌生。作为无神论者的我们,是否有能力在思考人类文明演化的重大历史窗口期,有分量地涉足这些重大的话域?我们是否有能力秉持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广度,在事关基因、本能、信仰和人类未来的重大话题面前,添加我们自己独立的声音?每当念及这些问题,都令人难以平静。
作者在这部书、也是这三部曲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抄写在这里:“也许宗教需要经历第二次转变,其规模相当于从狩猎采集者宗教到定居社会宗教的转变。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宗教保持了它为共同目的团结所有人的力量,无论在道义上还是为了自卫。它应该触及所有感官,提高思维。它应该超越自身。它能够设法面对情感和理性,我们的相互需要,和通过理性探索所了解的人类知识。”(p291)
这个世界正在掀开新的一页。
这一页,事关我们刻写在骨子里的神灵。
我们——是全部,不是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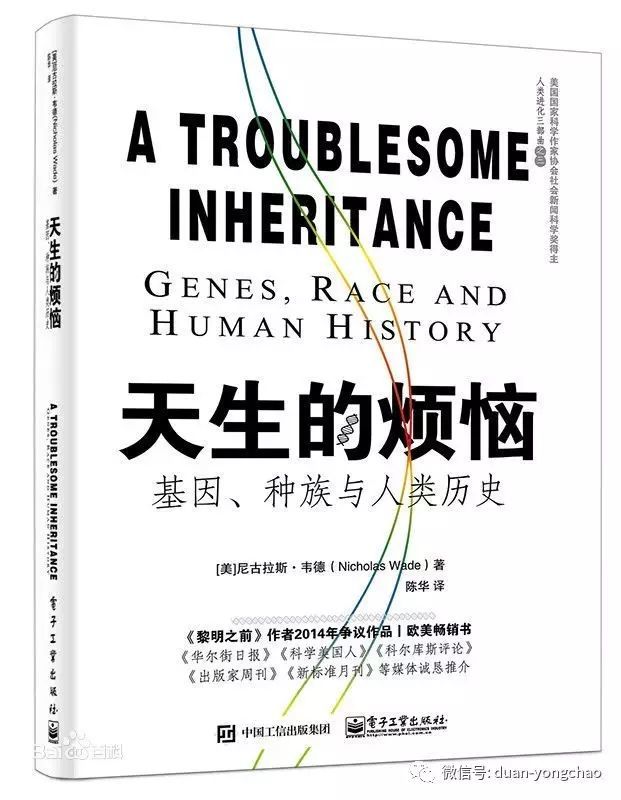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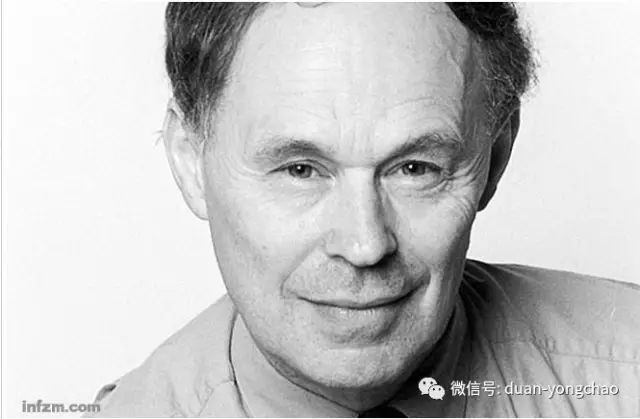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