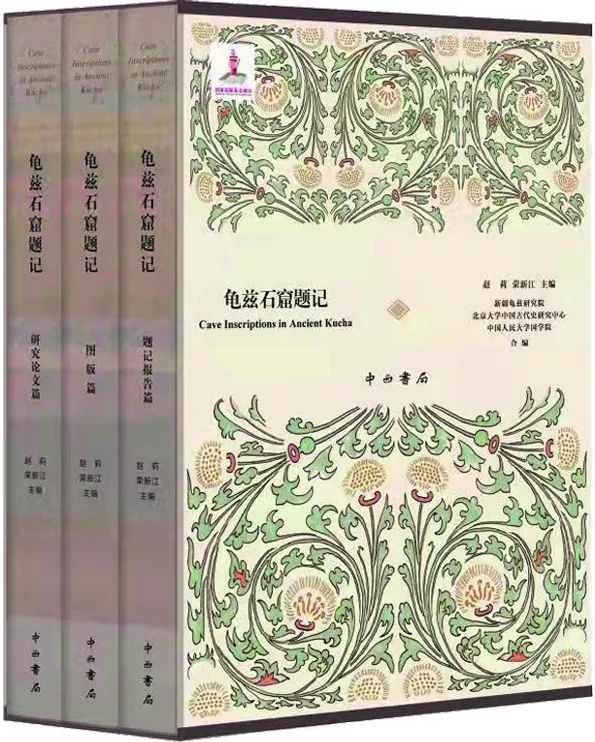
学界朋友送来赵莉、荣新江主编《龟兹石窟题记》一书,洋洋洒洒三大卷,装帧精美,编辑上乘。本人因为十年前编著《库车史》一书,对于古代龟兹历史文化略知一二,所以怀着极大兴致迅速初读一遍,感触良多。应该说,该书具有填补古代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应是近年来我国西域史文献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一
初见于我国汉代史书的“龟兹”地理范围,应指今塔里木河北缘的阿克苏地区一带区域,大致包括今天的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龟兹历史是我国新疆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禀赋使其成为汉唐之际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和连接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枢纽,从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所在到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治所,龟兹地区作为中央政府统辖天山南北各地军政事务中心,在维系西域同中原地区的联系、巩固汉唐诸朝对西域及以西各地的管辖治理方面皆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龟兹地区佛教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唐人行纪中所谓“管弦伎乐,特善诸国”[1]的记载真实反映了龟兹乐舞在西域诸地中的巨大影响。宋人沈辽诗歌中“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2]则揭示了龟兹乐舞传入内地的实际盛况。龟兹乐舞艺术的繁盛和东传扩散,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明宝库。
近代以后,西方探险家们陆续盗掘大量新疆文物至海外,新疆地方历史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其中,库车、拜城等龟兹地区出土的一种古老文字聚焦世人目光,引发学术界延宕一个多世纪的聚讼。经过语言学家们研讨后认定,这种文字用的是印度的婆罗谜字母,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Centum语组,有甲乙两种方言之别,甲种语言主要使用于焉耆—吐鲁番一带地区,乙种语言则限于龟兹地区。鉴于唐代玄奘书中曾在今天阿富汗北部和中亚地区见到所谓“睹货逻国”(今译作吐火罗)所用语言,[3]故人们分别将其称为“甲种吐火罗语”和“乙种吐火罗语”。据研究,所谓“吐火罗语”(Tokharian)在语言分类上与同属印欧语系的主要东方分支印度—伊朗语的距离较远,而同分布在欧洲的拉丁—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关系较近,所以一经发现便迅速引发欧洲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众多学者围绕着定名问题争论了近一个世纪,至今聚讼纷纭,没有定论。我国学者季羡林等也曾参与讨论。实际上多数专家经过研讨后倾向于认为,“焉耆语或者龟兹语”这种出土于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字就是当时人们使用的文字。[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考古队声称发现了真正的吐火罗语,所以198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文改成“焉耆—龟兹文”。[5]
近代外国探险家们从新疆地区盗走的焉耆—龟兹文残卷绝大部分收藏在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博物馆,其内容有文学作品、宗教文献和其他一些世俗文书,由于语言学方面的优势,以往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一些欧美学者。目前已经陆续刊布了一些相关成果,更多偏重于语言学方面的研讨。
焉耆—龟兹语言的发现和研究结果显示,很早以前曾有一支操印欧语言的部落向东迁徙到今天的天山南部地区的焉耆、龟兹等地居住下来繁衍生息,他们与当地居民交往融汇,且信仰佛教,故而留下诸多以焉耆—龟兹语言书写的文献材料。唐宋之际,随着我国北方草原葛逻禄、回鹘等众多游牧部落族群迁入到这一带区域,经过各族交往交融,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完成了新族群的构建过程。[6]
目前发现的焉耆—龟兹语文献主要是木简和文书残片,比如195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哈密市出土的弘扬佛教教义的文学剧本《弥勒会见记》残片,[7]再有就是残存在古代龟兹各地分布的众多佛教石窟题记,亦即在石窟壁画的榜题以及由石窟居住者、参访者在墙壁上留下的墨书或刻写漫题。据新疆龟兹研究院披露,这批题记、榜题广泛分布在克孜尔、库木吐喇、森姆塞姆、玛扎伯哈、克孜尔尕哈、托呼拉克艾肯、温巴什、台台尔、亦狭可沟、阿艾、苏巴什等石窟中,这批材料国内外学界知之甚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文物工作者先后分三次对这批焉耆—龟兹文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释读和研究工作,出版了一批成果且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2009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商定“新疆现藏吐火罗语文字资料调查与研究计划”,共同合作以对新疆现藏所有婆罗谜文字资料,包括木简、陶片、经页残片、壁画题记等进行统计、释读及研究。[8]今天所见的这部《龟兹石窟题记》即系共同出版的成果。
《龟兹石窟题记》三大本分为题记报告篇、图版篇和研究论文篇。“题记报告篇”主要是对带有题记的洞窟、题记的位置的描述,以及对题记的转写、转录、翻译和注释;“图版篇”主要提供石窟现场资料与窟前清理出土文物的图片,同时辅以国外所藏相关资料;“研究论文篇”则收录课题组成员撰写的相关论文。[9]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对龟兹石窟题记中的龟兹文资料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探讨。据悉,参与《龟兹石窟题记》一书的学者专家囊括近年来活跃在西域研究领域,尤其是龟兹研究方面的国内外知名的一批中青年才俊、学术翘楚,这其中有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考古学和佛教等各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这不仅印证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本身的综合性学科特点,同时体现了我国西域史研究水准不断提升的国际化程度,确实可喜可贺。
二
据研究,龟兹文在西域地区使用的大致年代是6~8世纪,[10]如龟兹研究院收藏的龟兹文木简年代多数确定为唐代安西都护府治理时期,这些石窟题记反映了克孜尔石窟从兴建到衰落的过程。特别是在石窟中发现了唐代史料时常提及的安西“耶婆瑟鸡”的龟兹语形式,还有一些龟兹王供养人的新发现,这些都为确定克孜尔石窟即耶婆瑟鸡寺提供了有力证明。在这些石窟题记中还出现了一些之前未发现的龟兹王的名号,这就与此前木简中发现的龟兹王的探索相连接,[11]同时给学者们深化始于民国时期议论不绝的有关龟兹王“白姓”问题的研讨提供了广阔空间。可能这还涉及更为深远的汉唐诸朝对于龟兹地区管辖治理下文化的引入融汇问题。这些珍贵的题记释读将是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有力补充和印证。
石窟题记具有不被传抄或者重新誊写的特点,反映了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情况,因此这批材料对众说纷纭的龟兹语流变的年代问题提供有力说明,甚至可能为以往人们仅从写本残卷断定的所谓语言分类、分期提供证据。对此,《龟兹石窟题记》“研究论文篇”中已经有人提出很好的推测。[12]龟兹文题记里还披露出来一些汉语借词,诸如“副使”“税粮”等,反映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时期中华文化背景下该地各族语言交流交融情况,或许可与之前该地出土的汉—龟二体钱材料形成鲜明对照。
佛教思想是龟兹文题记、榜题中占比较重的内容之一。之前国外学者施密特、皮诺等人都有研究,我国佛教思想研究专家霍旭初先生在“研究论文篇”中有更为详尽的梳理和论述。著者以为这些图像及其榜题大部分描述的是过去印度诸国国王供养“过去佛”的故事,皆在弘扬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根本思想。该石窟供养人借此标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初步断定这些石窟为龟兹王或王族所开凿,时间为公元7世纪,也就是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此间龟兹地区王族竞相出资开凿修建石窟,为一时风尚,应是真实反映唐朝时期该地佛教空前繁荣的重要标志。[13]
古代龟兹地区多族群聚居导致其文化多样性特征极为鲜明。据研究,龟兹地区诸石窟题记中除了婆罗谜龟兹语,还发现了汉、粟特、回鹘、察合台文等多种语言题记,尤其是被誉为“汉风”壁画风格的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榜题中遗留不少人名或者僧官称呼,以及一些有纪年(一种是年号,一种是干支纪年)的标识,这些线索对于探索石窟寺的年代以及同时期其他重要史实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14]显然目前《龟兹石窟题记》中所展示的古代龟兹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确实反映了地处丝绸之路中介的古代龟兹石窟璀璨夺目的文化多样性特点,这些古代遗存是悠久绵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珍视,并认真加以整理、释读、研究和利用。
三
龟兹历史文化在我国新疆地方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内涵极为丰富。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所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龟兹,是中西、中印文化学术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四大文明交汇,各种宗教兼容,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古迹与文物遗存,也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将现代文化理念和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研究龟兹学,对科学地开发西部,繁荣经济,推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5]
鉴于此,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于古代龟兹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探索一直延续不断,相关成果颇多,已然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主力军。但是不容讳言,古龟兹文资料的研究探索仍是我国学界的软肋,除了季羡林先生,国内知者甚少,个中原因自不待言。所以,2013年初本人主编出版的《库车史》中就曾预言,由于古代龟兹历史复杂性,特别是有关龟兹文献识读研究的缺失从某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对于古代库车史料完整性的认知。[16]今天《龟兹石窟题记》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资料短板,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整体了解和认识古代龟兹地区历史的科学水准。
新材料的发掘无疑有助于促进学术发展。在新疆地方史研究中,汉文史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这不仅在于自从西汉王朝开辟了对于整个西域地区管辖统治的历史之后,历朝历代,尤其是统一时期,汉文都是新疆地区各族使用的通用语言之一,还在于中华民族一直具有修史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央王朝都非常重视新疆地区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刊布,一部官方修撰的二十四史,大都有关于新疆地区的篇章,这些汉文史料在对包括古代龟兹史在内的新疆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常识。[17]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残留至今的古代龟兹地区的诸族古代文献,诸如龟兹语文书虽然只是断简残片,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内容更为广泛细微的资料信息来源,并因稀少尤显珍贵,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于唐代龟兹地区历史文化的全面认识,同样可对人们研讨迁居该地的回鹘人的经济文化衍变提供重要的资料参考,更是对相关汉文史料的有力补充,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丰富性,补充和扩展我们对于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史研究的认识,充实和丰富新疆地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内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面对这部由我国学人主持完成且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龟兹石窟题记》,我们仍不免感慨万千。古代龟兹史资料的发现和最初的研讨皆伴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一段难以言状的屈辱经历,如果说,民国时期学人针对外国列强盗劫敦煌文物而悲愤地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那么龟兹者,何尝不是一部令人心碎伤心的学术史。所以这部巨著的问世不仅告别了以往有关龟兹语文书的收集整理因为各种原因都残缺不全的境况,还意味着那个完全任由外国学者主宰定义龟兹文化的学术时代的结束,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这一切。《龟兹石窟题记》的整理出版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深信,经过科学整理后的这些珍贵史料将不再仅成为少数专家学者利用的小众话语,更应为准确全面阐释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滑动查阅
[1]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
[2]沈辽:《龟兹舞》,转自《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3]《大唐西域记校注》记:“睹火逻国,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字渐多,愈广窣利。”第100页。
[4]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考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15页。
[5]李铁:《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第58页。参见彼诺:《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耿昇中译本见于译者《法国西域史学精粹》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
[6]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参见张国领,裴孝增主编:《龟兹文化研究》(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7]据该书题记所记录,此书是由一名叫圣月的佛教大师从印度语译成古代焉耆—龟兹语,后由一名叫作智护的法师从古代焉耆—龟兹语译成突厥语。参见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75页。
[8]赵莉,台来提·乌布力:《新疆龟兹研究院藏吐火罗文字资料概况》,《文物》2013年第3期,第18~20页。
[9]赵莉,荣新江:《龟兹石窟题记》“序”,中西书局,2020年。
[10]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11]庆昭蓉:《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王》,见《龟兹石窟题记·研究论文篇》,第26~31页。
[12]狄原裕敏:《略论龟兹石窟现存古代期龟兹语题记》,见《龟兹石窟题记·研究论文篇》,第54~69页。
[13]霍旭初:《库木吐喇第34窟图像榜题及相关问题研究》,初刊《西域文史》第11辑。复刊登本书“论文篇”,第118~131页,略有修订。
[14]台来提·乌布力:《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题刻和榜题》,《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15页。
[15]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三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6]田卫疆主编:《库车史》“序言”,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17]相关论述可见庆昭蓉所著:《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4~415页。
(作者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伊犁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俐
审核:陈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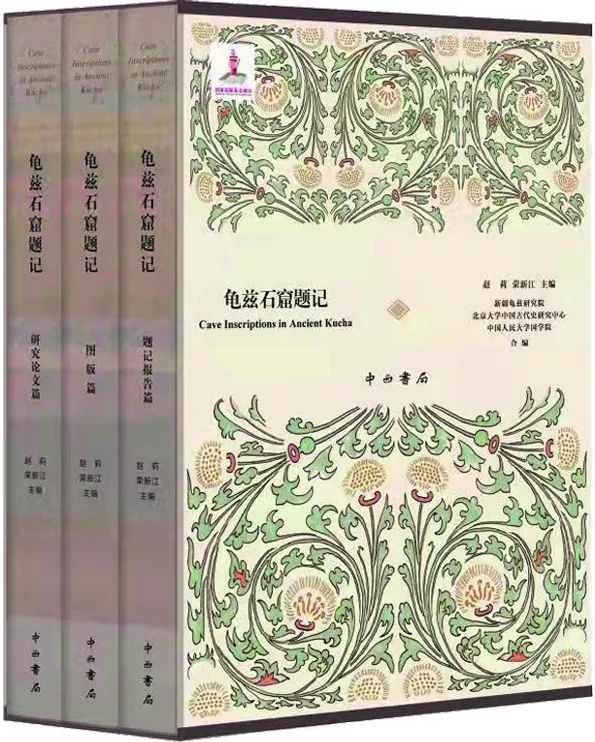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