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主要选自《《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

彼特拉克代表作(彼特拉克十四行诗)
“今天有一种通行的共识,那就是‘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指的是从1400到1600年间欧洲在文化、政治、艺术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剧变和转型。”(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58页)
“伏伊格特和伯克哈特这样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功劳,就是把人文主义一词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他们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第6页)
实际上,号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并不“人文”,当时欧洲人还处于基督教的神的枷锁之下,一切等待神的启示,没有理性精神,没有脑子。
克利斯特勒说道:“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根本算不上一个哲学思潮或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和文学沾边的东西……当时的人文学校虽然包含了一个哲学范畴即道德,却将诸如逻辑学、自然哲学、玄学、甚至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法律学以及神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领域统统拒之门外”,“在我看来,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千方百计地想要将自己与整个时期的哲学、科学及教育结合在一起;而眼下的确确凿事实,却好像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反面证据。”(克利斯特勒,《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思想》,第7页)
娜希亚·雅克瓦基指出:“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神或哲学思潮上的人文主义;它与各种思想观念的撮合,比如说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都是后人世界观及理想主义的发挥,与那个时代精神毫无瓜葛。”(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第64页)
我们熟知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艺复兴历史实际上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人的一种虚构、想象、愿景。
“米什莱是第一位将文艺复兴界定为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家,这一时期代表了与中世纪的关键性决裂……在他的笔下,文艺复兴发生在16世纪。作为一个法国民族主义者,米什莱热衷于宣称文艺复兴是一种法国现象……米什莱笔下的文艺复兴主要受其所在的19世纪环境的塑造。事实上,米什莱的文艺复兴价值观与他所珍视的法国革命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相似:拥护自由、理性和民主等价值观,厌弃政治和宗教暴政,尊奉自由的精神和‘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在他那个时代未能实现,他在失望之余,就到历史上去寻找这样一个时刻:自由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大获全胜,并且预示了一个摆脱暴政的现代世界。”(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0页)
“米什莱创造了文艺复兴概念,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则将之界定为15世纪的意大利现象……在布克哈特看来,15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人’,也就是他所谓的‘现代欧洲的头生子’。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论述: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以彼特拉克、阿尔贝蒂和莱奥纳尔多为开山,以古典文化的复兴为特征,到16世纪中期结束。布克哈特……高估了当时对宗教的态度,在他看来,那种态度是怀疑性的、甚至是‘异教的’。……与米什莱相似,布克哈特想象中的文艺复兴就像是他个人境况的翻版。布克哈特是一名知识贵族……他后来把文艺复兴想象成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艺术与生活是统一的,共和主义受到赞美但也受到限制,宗教受到国家的抑制,这听起来就像他对所钟爱的巴塞尔理想化的幻想。尽管如此,由于他认为文艺复兴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布克哈特的这本书一直是文艺复兴研究的核心著作。”(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1页)
“英国人沃尔特·佩特在15世纪的画家例如波提切利、莱奥纳尔多和乔尔乔涅的艺术中看到了‘一种反叛和反抗当时道德和宗教观念的精神’。这是对佩特所谓‘感官和想象的快乐’的颂扬,是唯美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甚至是异教性的。他发现,这一‘为了智识和想象而热爱智识和想象’的思潮,最早可上溯到12世纪,最晚可追溯到17世纪世纪。许多人对佩特的这本书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这本书是堕落的和敌视宗教的,不过,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佩特的观点塑造了英语世界对文艺复兴的看法。”(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页)
“米什莱、布克哈特与佩特创造了19世纪的文艺复兴概念,这种概念更多地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艺术和文化的成就显示出看待个体性的一种态度,显示出‘教养’的意义。这种界定文艺复兴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于15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并未提供精确的历史论述,而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欧洲社会的一种理想形式。这些批评家颂扬有限的民主、对教会的怀疑态度、艺术和文学的力量以及欧洲战胜其他所有文明。这些价值观加固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基础。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时期,欧洲咄咄逼人地坚持自己有权支配美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佩特等人创造出文艺复兴的一种幻象,似乎为欧洲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既提供了起因,也提供了证明其合理性的理由。”(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页)
也就是说,那种认为文艺复兴“高大上”的形象是19-20世纪托古改制所赋予的,就像黄洋在《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对古典希腊的评价一样,是一种想象,一种理想,一种现代性的虚构,一种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世俗和理性的新奠基神话。区别在于,有些欧洲学人以古典时代为平台,有些欧洲学人以文艺复兴时期为平台,有些人欧洲学人以17世纪为平台。
这就好像黄宗羲所借用的“古者”一样。“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岳麓书院,2008.5,第6-7页)
黄宗羲这里泛用“古者”来指代想象的、理想化的、虚构的目标模式的社会,而西方学人则直接以某一具体的年代为目标模式的社会。
既然古典希腊是一种“想象、理想、虚构”,那么,“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什么?来自何方?
如果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就那么现代性,18世纪启蒙运动是干什么?那么,什么是启蒙?
康德于《柏林月刊》1784年第4卷12期发表文章《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西方还笼罩在不成熟状态——宗教愚昧之中,还是“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启蒙了的”时代,还不具备“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是“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开放了”而已。
刘小枫说:“‘普遍历史’概念出现在西方中古后期,可以说表达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世界史’概念出现在17世纪晚期,但直到19世纪才取代‘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德意志,到19世纪中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和哲学取向,这既与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形成有关,又与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相关。”(刘小枫,《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编者说明》,华夏出版社,2017)
所谓普遍历史就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其实就是圣经的宗教史观,也就是说,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不是现有认知的、19世纪米什莱、布克哈特和佩特等所想象的、在13世纪开始被文艺复兴所打破,而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经过持续两个世纪“中学西渐”和“中国风”的沐浴熏陶,西方逐渐“中国化”,破除“障碍”,呈现“开放”,摆脱“不成熟状态”,摆脱“无能为力”,敢于、也学会了运用人类的理性,终于在18世纪迎来思想意识领域的启蒙运动——神圣启示转型为世俗理性,摆脱宗教社会,迈入世俗社会。然后,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建构了理性世俗的伪古典文明新传统,以取代宗教启示的希伯来传统。当古典希腊罗马基本建构成型,再于1855年开始建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逻辑连贯、完美,最重要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符合西方知识生产的历史。
《欧洲与无历史之人》的作者埃里克·沃尔夫说:“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叫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在误导。”((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2页)
也就是说,现有所认知的西方文明谱系为: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西方文明的真实历史形成谱系是:穴居野人→部落社会(13世纪之前)→基督教欧洲→中学西渐、中国风、中国化→启蒙运动→民主覆舟运动、工业革命→伪古典文明→文艺复兴。这才是真实的西方历史顺序,西方现代性的获得系源于“中学西渐”。“中国风”在伪古典文明之前,伪古典文明在差不多与民主覆舟运动和工业革命同时,古典学诞生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先遂行“中学西渐”,后建构伪古典文明,再之后诞生“文艺复兴”,即中学西渐→伪古典文明→文艺复兴。伪古典学和文艺复兴是“中学西渐”、“中国风”引发西方巨变之后孽生的世俗化产物,其使命一方面是妄图掩盖和取代“中国化”对西方崛起辉煌的决定性、革命性影响,把空间横向传播关系的“中学西渐”篡改为时间纵向传承关系的“文艺复兴”;另一方面是西方世俗派对抗、取代基督教对西方崛起辉煌的解释。即想象、理想化、虚构的古典学和文艺复兴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瞒天过海、李代桃僵以掩盖西方“中国化”的历史事实和用以取代“基督教”传统的一种世俗的新传统。
“教科书是观察文化的重要窗口。教科书不仅仅是图书,它是制造舆论的文化精英的半官方声明,用来使受教育的青年相信他们所说明色历史和现状都是真实的……19世纪早中期的教科书把欧洲中心的隧道历史往往相对公开地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后来的教科书不再把《圣经》作为历史事实的渊源。历史的动因明确地植根于一种理论,认为基督教徒创造了历史,从而也是白人创造了历史。”(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页)
伪古典学和文艺复兴都是一个基于理想、想象、虚构、空想的唯心体系,极少事实根基,是已“中国化”的西方世俗主义者想象和虚构出来用以对抗基督教的产物,只是以一个世俗神话取代一个宗教神话、一个世俗谎言替代一个宗教谎言罢了。即如黄洋所言:“一个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一个和启蒙精神相合的世俗的、理性的传统。”(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第2期,第52-67页)
西方能够最终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与洪堡的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即培养古典学信徒。基于此,洪堡的教育改革在西方世界是非常伟大的。
有人问,18世纪西方人建构古典伪史、世界近代伪史到底是蓄意伪造还是无心搞错了。我想,在中国这一边主要是满清篡改明史;而在西方这一边主要跟社会思潮密切相关,西方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思潮以及对内对抗基督教而托古改制式的理想、想象、虚构在西方伪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决定性作用。
在阅读和学习西方伪史时,切不可根据西方整饬和编辑好的“历史”顺序去认识,而必须从知识生产的角度、从学术史的角度去研究和认识,才能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西方伪史。从学术史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西方伪史,才能全面和深刻理解西方编造伪史的缘起、根据、思想、方法,才能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其伪实证、伪科学、伪学术的本质。
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利玛窦来华之前,西方一切理性、世俗、科学的著作和艺术都是断代错误或蓄意伪造的。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根本不存在。
另外,关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伪史,详见拙文《西方人文主义伪史是如何炼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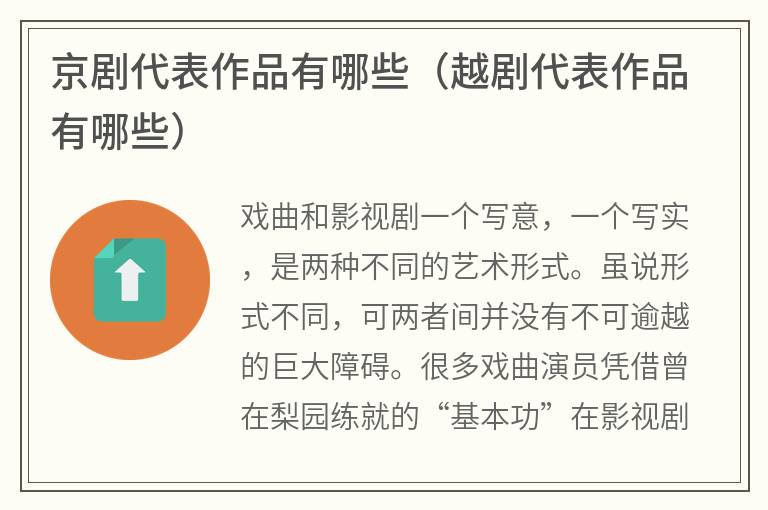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