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商周与秦汉属于不同的大的历史阶段,这两大阶段既有重大差别,又有承继与演变关系。赵化成先生的《周秦汉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聚焦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1200年的历史,通过“陵墓制度”“都城建制”“农业手工业”“艺术及其他”多个维度,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地下墓葬、地上都城资料,对从商周到秦汉的历史性变革、承继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展现出周秦汉时代独具魅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书注重长时段的观察,取得了独特的学术成果。诚然,相关的一些研究尚未完成,由此留下了一些遗憾,读者可继续关注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文集《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或可弥补本书的部分不足。
以下为赵化成为《周秦汉考古研究》所作后记。

赵化成,陕西汉中人,1974-1977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80-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1984年起,先后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汉唐教研室主任、考古学系主任、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东周秦汉考古,主讲课程有《秦汉考古》《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秦楚文化研究》等。合著《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参著《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编著《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文物出版社,2021)等多部著作,在《文物》《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等国内外刊物、论文集上发表80余篇学术论文、考古简报、报告、书序等。
这篇后记,涵盖了两部文集,一部为《周秦汉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另一部为《秦与戎: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最初为《周秦汉考古研究》(简称《研究》)撰写了一篇后记,后来编辑《秦与戎: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简称《探索》)时,因大病在身,已无力再另行写作。两部文集的选编虽各有侧重,但后记需要说明的问题与过程有较多相似性,因此,我将原来的后记作了部分改写,用在两部文集之后。
《研究》和《探索》两部文集是笔者从历年来发表的近百篇论文、参著图书、考古报告、简报、书序、书评等选编了部分略具代表性的论述而成。所选文章绝大部分为独著,少数为合著,而合著者笔者均为第一作者。两部文集的编辑出版承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倡导、策划和资助,以及同行好友、学生弟子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早年所发文章多无电子版,所附图片也不合格,学生弟子们帮助复制、编辑、绘图、翻译、校对等,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我生病的状态下,承担了更多的编辑、修订、配图、校对等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两部文集的选编各有侧重,尽管《周秦汉考古研究》中有“秦”,而《秦与戎: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更以“秦”为主,但不同的是,前者的“秦”是关于秦考古学文化跨朝代长时段的观察,而后者的“秦”则是专门探索两周时期以及大一统前后秦的历史与文化。这两部文集大致体现了笔者从考古入门到学术成长的道路,因而有必要对这一过程做点交代。
我的家乡陕西汉中,是一处为大秦岭与大巴山环抱、汉水润育的小盆地。高祖刘邦初被封为汉王,都汉水之滨的汉中,随着汉一统,汉人、汉族、汉字、汉语、汉服、汉学……这些带有“汉”字标签的词汇无不与我的家乡有关,而汉中也终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当年,家乡汉中一中(前身为汉南书院)为全地区最牛的中学,有铁门槛之称。有幸考入该校自然值得高兴,我和同学们憧憬着读完中学上大学,当工程师,当科学家,当文学家等。然而,学没上几年,“文革”来了。先是停课,后发生武斗,接着下乡插队,所有梦想都淹没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尴尬之中。之后,我被招工去了当地镇供销社。面对这种无奈的命运安排,只有发呆的份儿。
后来有机会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当年也经过了全县统考,并且成绩名列前茅)。在填写志愿时,自感理工科基础不好,不敢问津。在镇供销社几年,一直舞文弄墨,算读过一些书,那么就选文科吧。文科专业也很多,选什么呢?我的中学同学前一年进入西北大学无线电系,他告诉我,考古专业不错。我也觉得,考古远离现实纷扰,还可以全国到处跑,于是半明白半糊涂,三个志愿全部填写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才知道,这个有点奇葩的选择竟然救了我,因为家庭出身,我差点被刷掉,也因为考古专业在汉中无人报考,我才被特别录取,也算是歪打正着吧。相比之下,我的诸多中学同学尽管在各行各业都很优秀,但有机会上大学读书的则很少,留下了终生遗憾。
在西北大学几年,“文革”各种干扰不断,但面对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大家倍加珍惜。我还记得我先后读过百余本历史、考古、古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抄写了数千张卡片。尽管漫无目的,但我初步认识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考古。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班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临潼姜寨、陕西周原等著名大遗址的田野考古实习,并参观考察了陕西、河南、山西、湖南等地诸多考古遗址及博物馆。其中,1976年我在陕西周原遗址参加了两次考古发掘实习,合起来差不多一整年,且有幸与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在西北大学及周原遗址田野实习期间,有幸聆听了宿白先生开设的《中国古代建筑》课程,以及邹衡、俞伟超、严文明等先生的多个讲座,为先生们博大精深的学问、缜密的逻辑思维所折服的同时,也为日后报考北大研究生埋下了心灵种子。
毕业后哪里来哪里去,我回到了家乡汉中博物馆。博物馆建在据说是刘邦在汉中的宫殿建筑旧址上——古汉台。在家乡四年,尽管也做过一些考古工作,如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师一同徒步数百里考察了褒斜栈道,在博物馆前辈的指导下研读了褒斜道石门石刻,与同仁共同发掘了多座汉魏墓葬等,但大多数时间为各种杂事所缠绕,包括用整整一年下乡当农村工作队员。其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拜邓公之所赐,1980年秋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俞伟超先生读研。
大概因为我是陕西人,俞伟超先生那几年也正关注西北地区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于是让我多关注陕西及甘肃地区的秦文化和羌戎文化资料。研究生第一年,课程之余我收集并整理了陕西数百座秦墓资料,就秦墓的分类与分期写出了长篇论文,尽管没有发表,但对于东周时期秦文化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寻找更早阶段的秦文化奠定了基础。记得曾与梁云聊天,说到赵姓与梁姓皆出自嬴秦一族,而我们都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追寻秦人先祖的足迹,冥冥之中莫不是上天早有安排。
读研期间,除完成课程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中度过的。1981年夏秋,在俞伟超先生的带领下,与七七级、七八级部分同学一起,参加了青海循化苏志卡约文化遗址的发掘,之后协助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整理大通上孙家寨等地近千座卡约文化墓葬以及民和核桃庄300多座辛店文化墓葬资料,主要工作是陶器的类型学排序与分期: 在一大片空场中,几百座墓葬的陶器按照早晚变化序列依次排开,这种场面是何等的新奇与壮观。其间,还聆听了俞伟超先生《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等系列讲座。实习加讲座,大大丰富了我对西北青铜时代文化及其族属的认识,为尔后早期秦文化及西戎文化的探索作了铺垫;而有关考古学基础理论、方法的实践与培训,更是受益终身。
1981年底青海实习结束后,在俞先生的安排下,我即独自前往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作了短期考古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1982—1983年在礼县栏桥发掘了寺洼文化墓地、在甘谷县毛家坪发掘了两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198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在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那时,因为田野考古任务繁重,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大多都推迟毕业,而我则延期了一整年。
毕业后,我留校当老师。接着,俞伟超先生离开北京大学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早期秦文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只好暂时中断,而我也因为课程需要,重点转向战国秦汉考古教学与相关研究。俞伟超先生虽然离开北大,但可以经常见面聊天并请教学术问题,正所谓学问是聊天聊出来的。同时,我常去拜访请教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先生,也深受他们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熏陶。
20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秦公大墓被盗掘,一批铸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及金饰片流散于海内外。对此,我深感震惊与遗憾。如果当年能够在甘肃不间断地进行秦文化的调查与发掘,或许有提前发现秦公大墓的可能。幸好,自2004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的领导与支持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今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合作的“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启动,并组建了联合课题组和考古队,大家推举我为课题组组长(近年退休后已改由他人担任)。之后,在甘陕一带连续不断地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重点发掘了礼县西山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六八图遗址、清水县李崖遗址,近年又再次大规模钻探与发掘了甘谷毛家坪遗址。此外,还调查发掘了与秦文化密切相关的张家川马家塬、秦安王洼、清水刘坪、漳县墩坪等西戎墓地。其中,2006年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0—2011年清水李崖遗址的发掘由我任领队。总之,五家单位经过十余年的精诚合作、不懈努力,在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发现,取得了多项重大学术成果。其中,李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从考古学文化层面揭示出嬴秦人来源于山东东夷族群已成定论,可以说俞伟超先生当年交给我的这一任务已基本完成,先生在天有知,当会感到欣慰吧。
在大学当老师,学术研究是一方面,而主要精力则用于教学及带学生。除课程外,我先后多次带学生田野实习,包括三峡库区忠县崖脚遗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山东东平陵遗址、甘肃清水县李崖遗址等处的考古调查与发掘。2007年我获得了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后又获得了“北京市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两部文集中,《周秦汉考古研究》,除我的专业方向秦汉考古外,还涉及商周,主要是两周时期。俞伟超先生在世时曾反复告诫我们: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发展既具有阶段性,也具有连续性,欲读懂秦汉,须对商周有较多的了解,也就是说长时段的观察与研究很重要,这也正是包括俞伟超先生在内,诸多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之一。此外,俞伟超先生除了擅长具体的、微观的考证外,更注重制度性、规律性的宏观分析。例如,先生的《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一文,以高屋建瓴的宏大视角,开启了中国古代埋葬习俗与制度研究的新思路;而《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则回答了历史时期大一统条件下如何定义和把握考古学文化的问题。遗憾的是,先生英年早逝,类似的大课题刚开了个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因而这部文集的一些研究就是秉承先生的遗愿而展开的。21世纪初,我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汉唐教研室几位老师和考古界同仁共同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汉唐陵墓制度研究”,历时四年,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参见课题结项报告)。其后,部分老师与同仁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而我所承担的“从周制到汉制: 商周秦汉陵墓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子课题,由于涉及面广,迄今只发表了陵园制度、墓形制度、葬具制度等研究成果,而墓地制度、葬品制度、祭祀制度、外藏制度、观念信仰等系列研究还未最终完成。但笔者曾就这一课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年的硕博研究生中开设了专题研究课;此外,在全国多座高校及考古研究所做过多次讲座。而退休后,2020年,学院又邀请我以此题目为硕博研究生及年轻老师新开设“考古名家讲座”,半学期做了8次讲座。借此机会,笔者系统整理并补充了过去研究,较过去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然而遗憾的是,今日身患大病,已难以继续写作。为此,我已嘱托学生弟子今后继续深化研究,期望将来能够与学生弟子以专题讲座形式合作出版。
《周秦汉考古研究》收录较杂,分为四个部分: 陵墓制度、都城建制、农业手工业、艺术及其他,总计25篇。这个分类,只是大致划分而已,未必都合适。所收一些论述成文较早,一些观点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与认识的深化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但这是学术研究的必经过程,因而,除技术性的修订外,大部分保持原样不变(凡有新修订者文末均已说明)。
《秦与戎: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大体以考古学文化年代早晚为顺序,文集编排没有再细分类,原因是诸多文章涉及时段较长,而秦与戎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此外,文集排序也考虑到了发表年代的先后。例如关于嬴秦族的来源与早期秦文化的探索,论文发表的先后体现了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及认识的过程。自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的深化,早年的一些认识需要修订甚至否定,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之路。遗憾的是,笔者拟撰写的《秦史与秦文化》专著以及几篇新论文,如《毛家坪遗址年代分期与文化性质的再认识》《西戎(犬戎、猃狁)与寺洼文化》《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关系新论》等,皆因大病在身,已经无力完成。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从事秦文化,特别是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并取得了诸多重要学术成果,祝愿他们继续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推动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2023年8月改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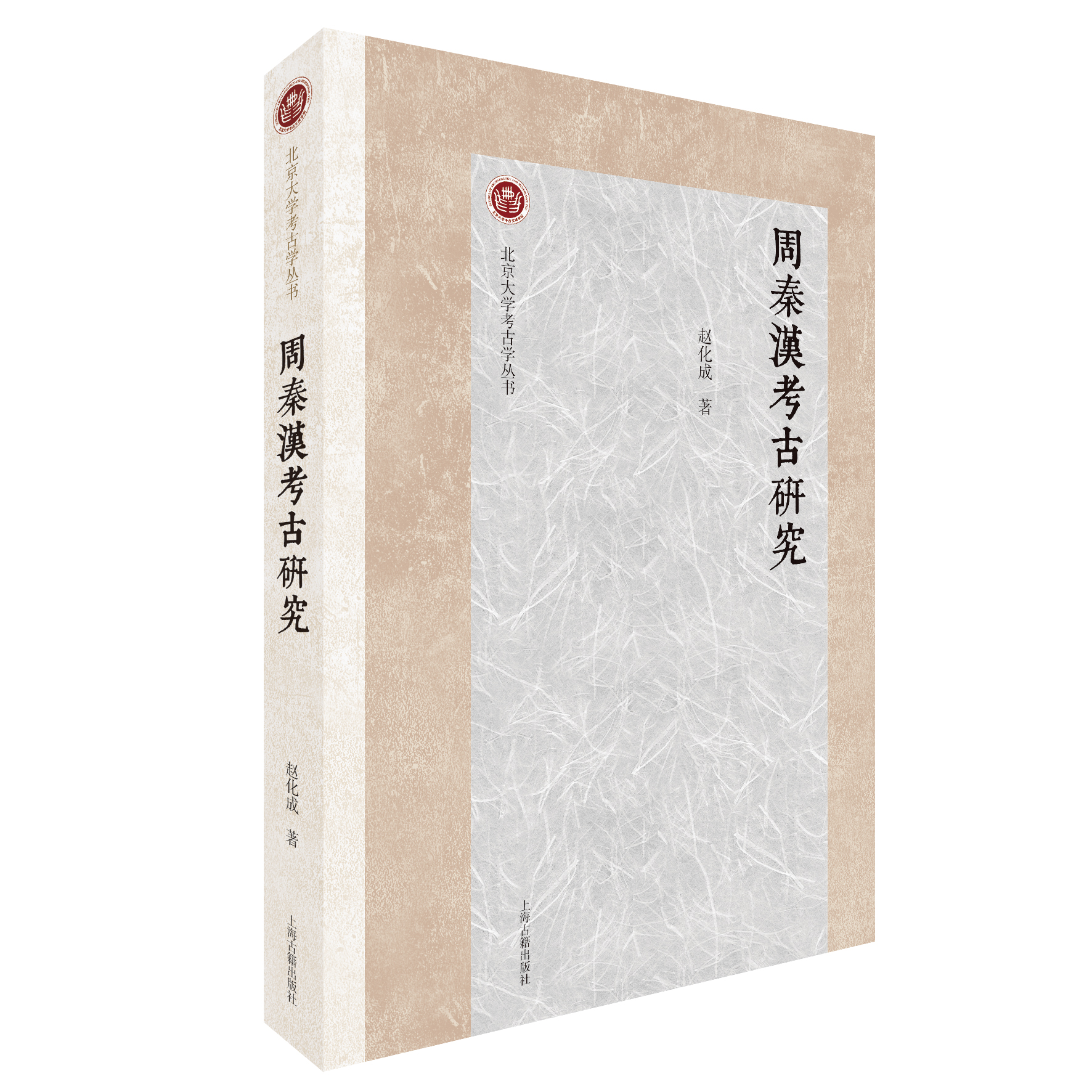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周秦汉考古研究》后记。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