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12日,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医生书记”廖正步和同事为村民义诊。2021年5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廖正步和蒋在强、代涛、黄燕、黄世峰等四位同事一起,被选派到巫溪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驻村工作中,他们经常带着医药箱走村入户,在察民情、听民意的同时兼任乡村医生 图/新华社
本来夫妻吵架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一个有权威的村干部过去吼两句就没事了。如果完全按照规范化来做,要登记、要签字、要处理,什么都要一步一步来,实际上可能只是做好了台账,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韩茹雪 发自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贺伟彧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
“县官不如现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它是长期以来基层治理的真实样态,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基层社会的共识。这是一件好事吗?县级行政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实际上,“县官”既是政务官,又是事务官。好的“县官”既要贯彻上级政策,推动执行落地,又要对下有所体察,为地方办实事。“县官”作为制度设置的一部分,是科层体制上的一个环节,不能是乱作为的“土皇帝”,也不能是不作为的“太平官”。“县官”如何治县?“村官”如何管理乡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在全国近20个省市展开调研,累计时间超过1300天,完成25万字的《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这本书被认为是显微镜下的县乡政治剖面观察,深度描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
全书从县域治理的内部视角出发,分为“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县域治理的自主空间”“基层干部的激励与发展”等四个部分,共38篇文章。书中没有引用任何学术著作和论文,所有材料都来自调研的真实案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该书作者杨华,希望站在县乡这一端口,对中国基层政治生态运转的逻辑有所认知。

▲杨华 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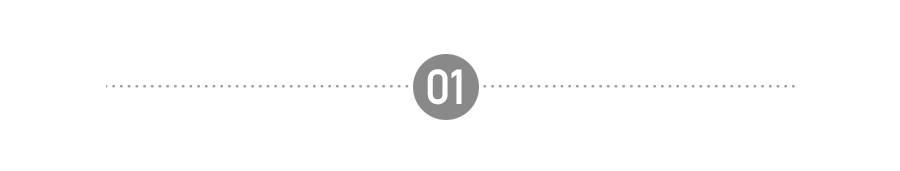
每一个体都有他者的影子
南方人物周刊:在体制内做调研,如何从处理入场忌惮的问题去展开工作?
杨华:体制内的入场和我以前做农村调研的入场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我在农村做过长时间的调研,包括家庭、婚姻、社会关系、老年人养老、老年人自杀等等。
农村调查的入场大部分一开始会有所芥蒂,建立信任需要时间。时间不会太长,也就一两天。一般是从乡镇介绍到村里面,首先要经过村支书,我们会把调查的想法、主题和方法告诉他们:我们的调研是作为学术研究,作为社会实践,不会对当地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前期需要村干部找人安排访谈,基本是先跟村干部了解基本情况,再访谈村里的其他精英。
取得村民的信任其实不难,一方面村民对大学生、大学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尊重,一种仰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朴素感情。另一方面访谈要在村里待几天,比如我上午访谈,早上就在村里走一圈,了解这里的地理风貌,更重要的是让村民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来了。农村本身是熟人社会,信息传播很快,转悠一两天,人们就知道有一群大学生和老师来做社会调研了。他们知道了有这些人,到时候去找他访谈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甚至有人主动反映情况。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是来做调研的,不能对个体的问题进行反映,我们做的是总体性的调研。要给人家一颗定心丸,不能许诺任何东西。
因为调查时间长,并非一天两天,而是10天、20天,基本上大家是不会撒谎的,包括村干部。问他们情况,要么不说,要么说实话,因为撒一个谎之后再圆谎就很难。我们调查时间够长,不是单一信源,要调查各方。
体制内调研其实是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的。因为现在的基层干部,包括普通的科员和镇长、书记,都是读过大学的,极少数没读过大学,对大学里面做科研也是有了解的。所以他们不会在访谈中给出偏离事实的叙述。
当然,访谈有技术与技巧,一对多或者多对多座谈的方式一般来说效果不太好,因为座谈邀请单位内很多人一起接受访谈,有同事、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很微妙。在座谈的时候,他不可能把一些话说得很透彻。之前采用过座谈的方式,这种方式讲一般的现象可以,如果谈到某项具体工作,比如某项工作各参与单位都来人了,就会变成一种汇报,因为他们习惯了体制内上级下来一个调研团的汇报方式,把他们自己这块的工作汇报完就完了。讨论也是围绕工作本身的,而且这种讨论相对比较浅。后来我们一般不采取座谈的方式。
个体访谈一般就能聊得比较透彻,尤其是体制内,这些人有思考能力、有实践经验,对很多事情思考过,也需要一个这样倾诉的出口。这样的讨论,不仅是访谈收集信息,还能激发他的热情。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把“县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杨华:先前我们有广泛的基层调研基础。上面的政策下来,比如低保政策、扶贫政策等等,我们去农村做相关调研,了解这些政策和资源在农村是怎么展开执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之后,政策执行下去,又会出现哪些政治社会现象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基层都有全面的了解,但总觉得欠缺一些东西,因为只了解了政策执行的这一头,要了解更深,就要和上一级的乡镇去聊。执行这些政策的乡镇干部、乡镇党委书记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他们如何与更上一级对接,这时候,在了解乡镇之后,就要去了解县一级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是怎么制定这些政策的,要把县、乡、村打通来理解。
2018年以前,我们在农村调查,没有专门对乡镇、县一级进行调研。2018年以后,我们觉得很多政策如果不了解县一级,不了解县、乡、村这三级,是没办法深入理解的。
从进入县乡调研之后,乡镇与县一级作为一个主体进入调研的考察范围,每一个都要去思考、去调研。要勾连县、乡、村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时候我们考虑的就不仅仅是政策和资源本身的问题,也包括体制机制、人事财政等等。

▲县乡调研合影留念,左为杨华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筛选调研的样本?
杨华:没有样本,也不需要样本。
这类研究实际是调研越多、数据越多,思考就越多。我能到哪个地方去调研,就到哪个地方去调研。比如有一个机会联系了某个县的领导,我就到他的县去调研,或者到他的单位去调研。每个地方的调研,对于丰富自己对县乡基层治理的理解,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每一个调研,背后都有其他县、乡、镇的影子,调研越多,对县乡治理就理解得越透彻。但不可能完全理解它,调查本身是无止境的,只能说这一次比上一次了解的东西更多、更深入、更接近现实。
东部和中西部,大城市的郊区县和普通的农业县是不同的,各有不同的治理生态,呈现出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但差异背后肯定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到不同地方去调查,不断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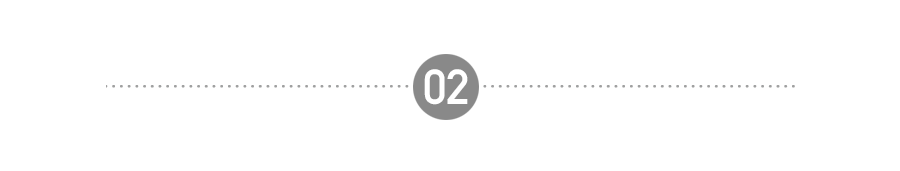
基层社会的复杂与差异
南方人物周刊:通过哪些例子可以理解基层社会运转的复杂性?
杨华:以江浙一带的“创二代”进入体制内为例。了解基层社会运转的复杂性,这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比如中原地区的县域政治生态和江浙沿海一带不一样。江浙沿海的政治生态和基层经济相关,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企业家在那里,那么基层政治可能就与这样的资本相关,资本就会渗入体制的方方面面。
“创二代”进入体制内是一个很小的侧面。更大的群体是江浙沿海那些创业一代,就叫“创一代”,这些人很多原本是农民,他们这一代通过创业成了千万、亿万富翁,非常之多。在江浙沿海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他们的子女叫“创二代”。
“创二代”一部分继承父辈事业,也有一部分进入体制,可能工资不高,甚至可能是编外人员。即便是编外人员,也可以连接体制和他父辈的产业。“创一代”往往希望在体制内找一个出口,无论是他的子女、女婿还是子侄,要支持某个人进入体制内。
南方人物周刊: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呢?
杨华:主要是为了保护他背后的企业,保护他背后的厂子,即便是在最基层。我们在县乡调查,尤其是在乡镇调查,不少职能部门都能影响企业的发展,而当体制内有人的时候,可以方便联通这些关系。
简单来说,企业越大,要联通的关系越广。这些企业家大多在乡镇创业起步的,就想把他的子女通过各种考公务员、事业编或者编外用工方式进入体制,这样就与体制产生了关系,希望能够保护企业。
一方面,进入体制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并非寻租方面的,因为现在相对规范,更多的是在保护企业,得到了相关信息,就能跟政府部门顺畅沟通。另一方面,进入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队伍,背后有一个企业支持,可能会走得更顺畅。不是通过送钱实现晋升,在现在的法治规范下不可能那么去做。

▲2022年7月,杨华及其团队在东部沿海某县敬老院采访县域养老情况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不同地区的治理生态差异表现在哪里?
杨华:在这样的横向比较中,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财政资源的丰裕程度。比如东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它们从省到市到县三级的地方财政非常丰厚,这样丰厚的财政对治理的影响非常大,它可以投入大量的治理资源进去,从而创造非常多的治理事务。但“下面”没有那么多人,公务员编制是锁定的,就会有大量的事业领域人员进入,因为县乡财政状况好,出得起这个费用。
这就容易出现人员臃肿的现象,大量的事务被制造出来,大量的人要填充到这些事务岗位去,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但是地方有钱。体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事情可以用钱去解决。比如体制机制创新的工作,不用花费功夫去做这个,只要出现一个事情,就增加资源、增加经费、增加人员去解决就行了,结果是越来越臃肿。
本来通过群众工作机制创新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因为有钱就变成用钱去解决。群众工作有些就不做了,和群众的接触也少了,干群关系也不紧密了。
与财力丰厚的东部地区相比较,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的财政都是国家转移支付而来,省、市、县财政都比较弱,在部门预算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不会去创造工作。很多工作不可能通过增加钱来解决,它就会去创造一些工作治理的机制,通过良好的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很多工作要去直接面对群众,从而出现体制机制创新和面对群众工作能力比较强的结果,这样的治理成本相对较低。
当然,不同地区资源匹配不同,治理事务也不同,比如东南沿海可能比中西部地区要复杂。它不再是简约治理,而是凸显了治理的复杂性。这种方式不断复制,最终让治理事务更加复杂。

▲2021年7月,杨华及其团队在中部某乡村访谈当地老党员、老干部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具体到地方的条块关系,当下“块块”如何对“条条”整合?“条条”如何通过“块块”实现自己的部门成果?
杨华:不同的政治任务要通过“条条”(具体业务部门)来实现,也与一些“条条”密切相关,相应的这些“条条”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显。比如说在扶贫的政治任务面前,扶贫办就会成为县一级的最重要部门之一,推动这个“条条”的业务工作就成为县一级的重要工作。

基层形式主义与基层干部的科层化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基层形式主义?
杨华:现在有的基层干部做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被问责,“避责”可能成为首选。只要这个事情可能产生问题,就可能不会去做,导致很多事情做不了或者推动不了。
从决策层面来讲,比如乡镇党委书记要做一个决定,原先是大家讨论过后觉得事情可行,就会从可行的角度提建议,这个事情的决议就做好了。现在责任到了参与的每个人身上,书记提议做某个事情的时候,涉及到相关分管领导的时候,他们要承担责任,就会掂量一下:事情在我这里出了问题,我要担责任怎么办?在乡镇班子成员讨论的时候,就会从很多方面去说这个事情,涉及到自己的部分,提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很难被决策通过或者说议而不决。
问责体制的好处是对基层干部的行为有重塑作用,“合乎规范”的特性增强,每个人都在法律范围与政策规定内行事。一个事情没有政策依据,他可能就不做了,做了也没有用,甚至可能出现负面影响、需要承担责任。另外,它也能对基层社会起到一种重塑的作用。
以低保为例,过去村干部往往会优亲厚友。如果不给,亲朋好友就会说,当了村干部就不认人了之类的话,即便有些村干部想保持公正,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也是很难做到的。人们会形成这样的论调,这是国家的资源,给谁都是给,不给我这个亲戚朋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现在监督强化了,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做村干部会被问责。亲朋好友也不会像原来一样索要低保,极大减轻了舆论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村干部好做了。这样的逻辑扩展到乡镇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要按照规范做事,人情的东西会变少,最终塑造了讲法律、讲规范的基层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基层干部能不能完全科层化、规范化?
杨华:在基本的制度和规范的基础上,基层干部要有一定的自主性,不能完全科层化。基层社会有其自身特点,现实中做群众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事情是个体化的,没有办法全部通过规范的东西去做。因此在基层乡村两级一旦完全规范化,很多工作就做不了,基层社会就会悬浮在基层群众之上。比如说乡镇有各个科室,乡镇可以自由调配,每个人有岗位工作要做,也要做其他的事情,按照人事相匹配的原则进行机制创新。到了村一级更是如此,村一级本身的工作量非常少,主要是跟群众打交道,了解群众的方方面面、和群众建立感情,而不仅是通过窗口去解决问题。
一旦乡村一级被完全规范化、科层化,成本会非常高,而且很多问题反而解决不了,会积累情绪。比如说,规范化之后,要到窗口去解决问题,要按照规范化和村民打交道。但现实是,和村民打交道本身就不规范化,比如说半夜夫妻吵架,要不要去解决?按照规范化,半夜不是工作时间。本来夫妻吵架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一个有权威的村干部过去吼两句就没事了,邻里矛盾、婆媳矛盾有时候也是如此,就是在熟人社会里“给个台阶下”。按照规范化来讲,要登记、要签字、要处理,什么都要一步一步来,实际上可能只是做好了台账,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本来村干部是不脱产的,不是体制内的人,而是村里的一员,很多事情按照村里的规矩来解决。比如半夜有人找,他可能披着衣服就去了,也了解村民们的情况,有的吼两句,有的说两句好话。有的人吼了两句之后,第二天还得拿酒跟他们一起去喝,吃个饭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非规范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细小琐碎的问题,如果通过科层化的办事程序,成本会显著提高,而且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基层的形式主义有什么具体表现?
杨华:比如乡镇要求村一级干部要坐班,要坐在村委会里面等着村民来办事情。政策的出发点是好意,怕平时村干部忙自己的事情,村民找不到村干部,确实也存在这样的现实状况。
但其实这是农村的常态,因为村干部就要有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产业,要耕种土地、要做生意,村民找来办事的时候可能找不到,白天打来电话可能晚上才能去解决,上面可能觉得没有及时办理。或者有要办手续的,村干部不会来一个就跑一趟乡镇去办,可能积累了一个星期一起拿过去办,乡镇觉得这不及时。最终出现要求村干部坐班的现象。
但村级事务本身比较少,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坐班。坐班没事干怎么办?那就要制造一些事情。比如做台账记录,每天要记录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做的就是“做台账”这个事情。实在找不到事情做,又有要求不能工作时间玩手机、看电视,有些干部就坐在那里聊天看报纸。
本来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做,在日常生活中解决村民的问题,现在硬要坐班,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没有什么工作事务,不就成了形式主义了吗?形式主义就是记流水账,每天几点打卡上班,几点打卡下班,这中间不能看手机,聊天聊多了也没话说,成了最大的形式主义。
另外一个形式主义,就是各种创建活动。
我在北方的一个乡镇调查,上级要求乡镇中学每年都要搞创建,其中一个乡镇中学就买了一个高档的打印机还有一台几万块钱的摄像机(照相机)。乡镇为了搞安全文明创建,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学校每年做不同的材料,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每次,要打印十几大本,都是彩印。上级来检查,指出哪个部分要整改,这十几本材料又要重新调整后再打一遍。他们三年之内打坏了三台打印机,用坏了两台高档摄像机,就为了搞创建。
如果让他们做其他工作,比如调解工作,可能用一个上午能调解好,他在调解工作中有获得感,他在这项工作里有创造性,他就觉得有意义。但是让他把调解工作做成材料,他可能就有怨言。因为他要一个星期来做材料,而且要按上面的要求来做这个材料,做这个材料过程中还要纠纷双方签字,他又要跑到下面去一家一家签字。问题是签字的过程当中这个案件又会反复,本来不去招惹他,不让他签字,这个事情就没了。你再去招惹他一下,他就有事情了,就使得这个案件没完没了。

▲2022年5月6日,广西融安,岗伟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晨晖(右三)、驻村工作队员江益芝(右五)在议事亭和村民们交流 图/新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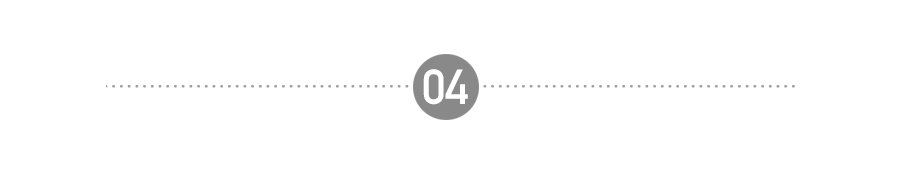
不存在完美的调研结果
南方人物周刊:回看这本书,从调研到最后出版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杨华:遗憾肯定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访谈本身会有很多遗憾,比如一开始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问题不深入。到后期了解很深入了,又发现没时间了,需要返回。比如对某个问题,调查过程中,资料收集齐全了,相关想法也有了,但回去写报告的时候发现这也不齐全、那也不齐全。比如说,主要领导没有访谈到,比如我从村民、村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中层干部、副职领导都访谈到了,对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得很深入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乡镇党委书记没有访谈到,这也是一种遗憾。
出现遗憾,要通过接下来的访谈调查来弥补。但即便如此,每次都有每次的遗憾。这是调查本身的遗憾,不可能有一个调查是完美的,一定会有遗憾。
第二种是这样的访谈中,比如说一些潜在的规则,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现实的复杂性超过了最顶尖的作家的想象力。这是社会为文字工作者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但很多人没有把握住,没有“下去”(基层)。我和我的团队下去了,认真做调研,有时候自己觉得够了,外面也会觉得做了很多,但其实真的不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