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则读后感,或称笔记,来自阅读署名房宁、周少来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2010年06月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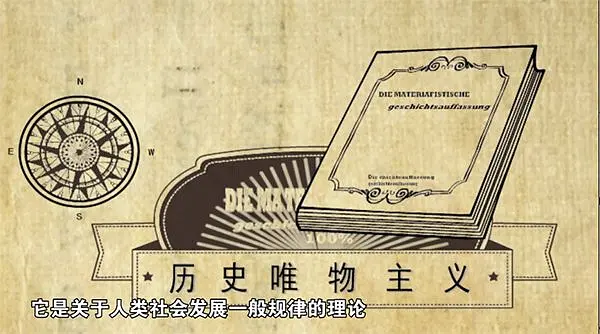
“马克思往前走了一步,把社会理论变成了社会革命理论——他是颠覆社会现代秩序的。”(任剑涛 语)
这一段时期,之所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了兴趣,一是因为过去目中所及得多的是“国家与革命”一词,“国家与社会”属于革命之后如何搞建设的问题。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还没解决。二是最近相应地阅读中注意到 “国家社会主义”(指希特勒)和“社会国家主义”(指斯大林)这两个名词,对“国家与社会”有了更多辨析的欲望,三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家主义”的讨论文字比较频乃,也比较突出。四是我讲鲁迅的故事选修课,联想到一个问题:鲁迅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三个主词前的偏词,到底是“国家”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还是“社会”的(=五四时期“文人圈子”里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这涉及到鲁迅的功能和意义问题。五是有一些相关国家和社会的断语或箴言,如:“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社会,所以基本的设计就是国家主义的假设”(任剑涛);“国家与革命,才是理解鲁迅的支点所在”(张武军)等,该如何定夺它们。最后,记起了自己曾写过的一则读书旧笔记:《国家与社会——国家不出知识分子和知识》(豆瓣,)。在里边,当时陈述了利比亚卡扎菲治下,将社会沙化在前,致国家崩溃灾后:
国家与社会之间均衡坏塌,最终导致恶果,利比亚即是例子。卡扎菲消灭民间组织、遣散社会、沙化社会,没有有效、有资历的社会组织,只有独大的国家;一旦国家坍塌,社会被破坏在前,已经没有能力和效率去率而组织乱民、恢复正常国家。反之,突尼斯虽是总统专制,社会没有被解散,社会葆有有机质,有正常、多元社会组织;一当国家在位集团(管控)崩塌,社会中原有七个(自治)组织(联手)共同组成“立宪联盟”,代表了社会大多数,担待了临时国家职责,迅速重订并通过宪法、恢复国家秩序,生活动荡极小。(吹笛:《国家与社会——国家不出知识分子和知识》)
总之,学者任剑涛说:“国家与社会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故需要学理上辨清、常态下构建,常态化地形成国家与社会合理、有机和高效的互动关系,这是人民幸福生活常态化的一个充分问题。
下面的内容,主要来自房宁、周少来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的阅读和剪接,再加上自己的引用和引申,加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问题的了解。回想1949年以来,中国疾风暴雨似地是退隐了孱弱社会,凸显了强盛国家,结果是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再到了1978年以来,按照这篇署名房宁、周少来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的表述,是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刻。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发展为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体制。伴随着这一进程,国家的治理模式、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自主空间扩大,大量社会组织涌现,社会自治程度大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段的问题是,这样的表述概念模糊、专词含混。大约这并不属于学理表述,也不属于公共表述,而是一种政党表述。不过,感谢此文对中外社会史有一个大体回顾,便初步有了如下西方社会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认识。笔记如下,作为今后学习的入门——
1)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引出市民社会和“社会自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首先产生于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随着社会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出现了游离于政府体制和企业之外的 “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社会”成员的主体是那些具有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看作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其活动的基础。但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进程可以看出,西方“市民社会”的实际形态主要是由相对独立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构成的,它们在国家政权治理体制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自治。
2) 一战后“国家主义”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国家主义
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以及西方国家遭遇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动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右翼思潮在西方兴起,甚至出现了法西斯德国这样一批在所谓 “国家主义”旗号下专制统治的国家。
关于“国家主义”两种形态,有一篇短文介绍,说它一是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市民社会以国家为轴心,是把棍子扎成捆的“法西斯”。这在德国是希特勒,在中国是蒋介石。1927年新国民党奉行“国家主义”以后便是这样做的,“国家”收编了“社会”。原来自治形态的社会团体和地方社群,都挂靠在国家制度之下,如党国。而社会成为附庸,市民的空间极度萎缩。二是社会国家主义,干脆是国家取代社会,利出一孔,思想经济文化统统被国家计划,市民统一于国家意志成为公民、人民,市民社会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出现。这在苏联是斯大林,在中国是毛时代,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改开前,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种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管理集中度高,社会生产和生活有高程度的同质性。在城市,人们基本上都隶属于某一个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在农村,人们都属于人民公社组织。可以说,那时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是高度重合的,即人们活动于国家体制中。(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3) 二战后欧洲的民主化运动,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二战后,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在思想学术界出现批判“国家主义”、重新诉诸“市民社会”理念的思潮。比如,倡导通过划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来推进欧洲的民主化;呼吁在美国复兴“市民社会”,以抵御日益扩张泛滥的官僚主义。结果是,在西方社会工会、妇女、青年以及人权保障、环境保护、社会服务等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对限制国家政权的影响和实行有限的社会自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美国为例——
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是,从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年当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的拐点,当政治的调整机制不够了、乏力的时候,有体制外的、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直接参与,表现出来的是群众运动或者是强大的舆论批判,然后进一步推动根本性的改革。所以并不是说一有群众运动就说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问题了。回顾历史,60年代的群众运动里,那次是声势浩大。那个运动在促进种族性别的平等、深入社会改革、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的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还有结束越南战争、缩短战线、缓和冷战……(资中筠:《关于美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说明:标题是这里另拟的)
概之,房宁 周少来的这篇文章肯定地说道:现代西方社会中“市民社会”理念以及社会自治实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4)改开中国,自主性社会成员和大量社会自治组织出现,国家与社会开始了一定程度“分离”虽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首先出现于西方社会,但更需要深刻把握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改开前,我国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种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管理集中度高,导致社会生产和生活高深程度的同质性。在城市,人们隶属于某一个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在农村,人们都属于人民公社组织。可以说,那时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是高度重合的,即人们活动于具有统一性的国家体制中。
改开后,市场经济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首先,人们的身份发生很大变化,“走出了单位的‘城堡’”。其次,身份变化导致被统一管理和单一组织固定下来的社会模式被打破。第三,身份和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的自主性、独立性空前增强。第四,于是我国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自治、群众自我服务的社会组织。总之,人们由隶属于国家统一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员变成了“体制外”的高度自主性的社会成员。从“国家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这种巨大改变,构成了我国国家与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分离”。
这种“分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成为推动大量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基础。这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必然要出现的重大历史现象;一个需要认识的基本问题。(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5)结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抵,是“国家”为“必要的恶”,“社会”为无条件的“善”
学习西方社会的经验。
首先,西方社会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发展“社会的力量”来消减、遏制国家政权以及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的压迫和管制;是通过社会的自治,使人群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 “中国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机构,一方面是解放个性、发展个人创造力的问题。”(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包含的这个人自由与国家重建两大目标,在今天专家学者们看来,当年显然没有奠基好——
1917年新文化运动欧化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启蒙”没有完成,只因随后忙于“救亡”跳过了这个环节。其实,“启蒙”首先是启蒙国家机制要重建,“救亡”首先是救独立主权,而不该是忙于国家权力的重建。换言之,“启蒙”要启蒙国家机制重建,启蒙国家权力要分割,社会要制约国家;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重建,导致国家吞噬社会。启蒙要启蒙社会理论,厘清权力来源和权力分配。(摘引自 任剑涛:《政治思潮的西学东渐》)
原本人类近现代史的性质,同是从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日常秩序的维持要依赖于清晰的权力来源和权力分享。但由于中国“屈辱历史”意识形态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逻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表述如左:“我国的国家体制,本质上是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自由和扩大人民权利为宗旨的。形式上是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表述不仅很绕口,亦东方智慧地留有后门。即它既有崇高的道德高度,也有无限的解释空间。这句话里的“为宗旨”、“通过”、“推进”和“保证”等词性的意思,直言就是“我们应更加看重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致性”,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当下中国的历史叙事,首先是革命史,其次才是近现代史。国家的权力来源和运作是依据革命史,如常言“吃水不忘挖井人”和“领袖挥手我前进”,而不是近现代史,如西言“民主和宪政”支撑的。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为地置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中——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把“社会”无条件地视为“善”。如果那样,就脱离了我国的现实,落入简单幼稚的窠臼。(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即斯大林社会国家主义模式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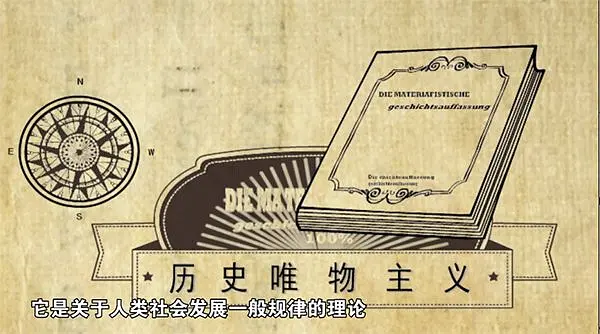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