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一天,应朋友之约步入东总布胡同一栋老房子,与朋友们吟诗写字。晚饭后,我沿着东总布胡同向西步行,穿过一条繁华的街道,进入西总布胡同。城市现代化,一点点剔除一座城市遥远而温暖的陈迹,机动车,乱搭乱建,把这条屡屡出现在文人士大夫书信和日记中的地标性胡同日趋通俗化了——没有可以连通历史的人物居住,些许权贵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通过这里,没有旧日时光的暗示,也找不到“一人之谔谔”的面孔。
过去不是,过去这里居住了很多学识渊博、人格伟岸的人,章士钊是其中之一。
我进入西总布胡同,是到章士钊住过的老房子凭吊。章士钊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后,他的子女继续在这里居住,章含之辞世,房子被国家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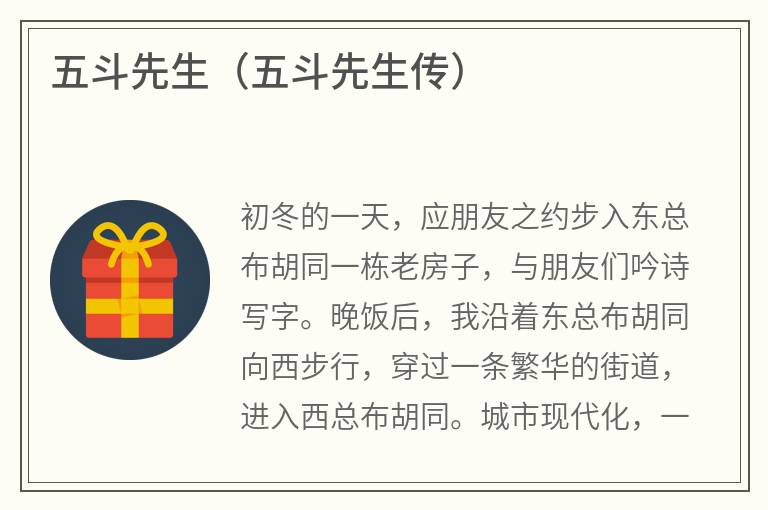
五斗先生(五斗先生传)
我在章士钊住过的老房子门前伫立,平复一下复杂的情绪,就从原路返回。
我一直被章士钊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迷住,曲折、凄迷,拟或是显赫、风光,都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他是政治活动家,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他与所有左右中国命运的政治家有交情。他是学人,在大学任教,主编杂志,撰写文章,沉迷书法,宛如一位生机勃勃的文人,深入思考,植根现实,参与社会进程。
“苏报案”中的章士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端倪。《苏报》,1896年6月26日在上海创办,胡璋主办。1900年,陈范接办。1902年,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苏报》及时报道,以“学界风潮”为栏目,深度报道退学风潮的缘由,深得读者赞赏。1903年,《苏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聘请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刊发进步文章,主张政治革命。《苏报》的立场,自然引起当局警觉,清政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为由,于1903年7月7日将报馆关闭,逮捕章太炎。邹容不畏牺牲,自动投案,以示不屈。1904年5月,章太炎、邹容被租界法庭判处3年和2年徒刑,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办报。《苏报》被封之后,章士钊、陈去疾等人续办《国民日报》,又因“放肆蜚言,昌言无忌”,再一次遭到清政府的查封。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具体实践,成为中国读书人勠力进取的证明。毛泽东记得《苏报》,也记得章士钊、章太炎、邹容。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章士钊养女章含之谈及章士钊,对“苏报案”中的章士钊给予积极评价。
这位曾受惠于章士钊的政治巨人,语重心长地对章含之说:“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见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士钊“爱管闲事”,究竟给毛泽东写了多少封信,不得而知。不过,为了高二适,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自然载入史册,至今被人探究。
二
章士钊为高二适的事情致函毛泽东,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这件事涉及彼时的学术争鸣,关乎对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历史认知。1964年至1965年间,南京出土了《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两块碑的碑文是用隶书写成,率真、苍茫,别有一番风味。“王谢”是指王兴之和谢鲲,前者是王羲之堂弟,后者则是谢安的伯父。作为东晋的贵族和政治强人,他们的墓志出土,引起考古学家和书法家的重视,在这两块墓志中开始破解积存的历史与艺术难题。碑文是隶书,郭沫若便以此为由,做出自己的判断——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郭沫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刊于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
时为江苏省文史馆的馆员,在学术界和书法界较有影响的高二适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很快,他写就了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他试图以此文与郭沫若讨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其实,对《兰亭序》的质疑,郭沫若不是第一人。清末学者李文田率先指出《兰亭序》的“漏洞”,他说《兰亭序》“文之题目与内容,与《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本所征引不同,是梁以前之“兰亭”,与梁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还不算,李文田又作四首七绝,烘托自己对《兰亭序》的判断,其中一首写道:“唐人未甚重《兰亭》,渊圣尊崇信有灵。南渡士夫争聚讼,后来都作不刊经。”
郭沫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无人抗衡,敢于与他商榷,的确需要胆识。
高二适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国情不陌生,他知道国内报刊不敢刊发《〈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章士钊。
章士钊比高二适长23岁,民国期间,高二适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文章得到章士钊的赞赏,还向于右任做了推荐。正为标准草书谋划的于右任看了高二适的书法,称之为“书有家”。抗战期间,章士钊与高二适住在重庆,两个人“朝夕相依,最为投合知己,唱酬挟策不绝,留下诗篇颇多”。
1949年以后,高二适被冷落,得到章士钊的关心。他手书推荐信让高二适面见南下视察的董必武,可惜不遇;继而谋调高二适进中央文史馆,还是不果;最后推荐高二适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在重庆,高二适曾任立法院秘书,“反右”期间,又是章士钊力保,高二适才得以避免“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高二适的家被抄,图书字画被洗劫一空,章士钊依旧不忘旧情,不断询问,所抄书籍字画才完璧归赵。高二适之子结婚,章士钊吟诗祝福;高二适夫人病重,章士钊知道后寄款50元。这样的友情,延续着章士钊对高二适的理解,他阅读了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支持高二适的观点。在西总布胡同的住所,章士钊提笔致书毛泽东,他知道,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是不会发表的。在信中,章士钊诚恳地说道:
……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与章士钊熟悉。1920年,毛泽东为湖南革命运动,也为了一批革命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找到章士钊筹钱。章士钊责无旁贷,依靠自己的影响,帮助毛泽东筹集两万银圆。1946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与章士钊见面,征询意见,章士钊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劝毛泽东迅速离开重庆,以防万一。深厚的交情,真挚的友谊,使毛泽东对章士钊另眼相看。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和高二适的文章,提笔回复:
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书郭沫若: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立)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主席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文物》杂志。
仅半年的时间,《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
这场论辨,被学术史称为“兰亭论辨”,影响重大。如果没有章士钊,关于《兰亭集序》的讨论不会存在。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所说:“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
三
文人士大夫在信函中思考国家大事,讨论社会问题,抒发生命情感,阐明审美理念,是历史性的常态。同时,由于文人士大夫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书法训练,笔墨功夫深厚,所书手札氤氲古典气息,雅逸、洒脱,文墨俱佳。但是,不等于说,文人士大夫都可以列入书法家的行列。有的人刻苦临帖,对书法史了如指掌,作文抒怀,墨清字畅,却不以书法闻名;有的人临帖,注重笔法的变化,艺术的追求,谙熟书法创作规律,即使是写一通简单的手札,也会倾注一番心思。章士钊属于后者。
章士钊称得上书法家。
1881年3月20日,章士钊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出生。祖上世代务农,直到祖父一辈,田产渐增,始有“读书求科名以传其子孙”的治家理念。章士钊兄弟四人,得到家族的悉心培育,接受系统旧式教育,于书法一道,用功亦勤。祖父、母亲辞世后,章士钊为生计所迫,逐步走向社会,先做家庭教师,然后走出湖南,到武汉闯荡。1902年,他往南京投考陆军学堂。考试作文题目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深思熟虑,题旨明确,文辞斐然,深得陆军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自然录取。只是反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在江南陆军学堂读书的章士钊不甘寂寞,因反对学堂无理开除学生退学,率领三十多名学生离开南京,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走上了废学救国的道路。在上海,被《苏报》聘为主笔。“苏报案”后,章士钊成为职业革命家。
文章独树一帜,书法风神兼备,他在不同的政治组织里穿行,此起彼伏,但他的文章和书法,一直被津津乐道。
他是《甲寅》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创刊于1914年的《甲寅》可谓一言难尽。章士钊在创刊号发表《政本》,抨击袁世凯的专政理论,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十年后,他又在《甲寅》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也许,一位名人的成长,悖论伴随始终。
1927年,淡出政治舞台的章士钊想到《甲寅》。因经济问题停刊的《甲寅》是章士钊的另一条生命。他计划卖字筹款,让《甲寅》起死回生。毕竟是声名远扬的章士钊,他的字得到拥趸,“以三月之力,书萐子千柄,集资万元”,办刊经费解决。
这个细节,是我们观察章士钊书法的一扇窗口。这个细节,也是我们认定章士钊作为书法家的根据。
“以三月之力,书萐子千柄”,萐子,即扇面,是雅俗共赏的书法形式。对于书法,章士钊是专家,他能游刃有余地写萐子、中堂、条幅、斗方、碑志,这些常见的书法形式,是他与广泛社会和不同人群对话的中介。然而,更能发现他的书法才情、文学感觉、思想个性的毛笔书写,是他的手札和诗稿。这是士大夫的文化深度和生命标签。
四
民国时期,章士钊的手札就在政学两界不胫而走。彼时,手札是人与人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政治人物,文人学士,社会名流,依靠手札研讨问题,交流心得,表述世俗琐事。章士钊是复合型人物,他活跃在政治舞台,游走于学术界、新闻界、法律界之间,结交各界名流,可谓一代通人。
章士钊手札,恪守传统,词语雅驯,书法掷地有声,延续晋唐宋明以来的文化薪火,成为新一代的书法景观。章士钊的行书有金石气,这得益于他对六朝书法的青睐;他的书法更具书卷气,这是读书吟诗的涵养。读破万卷,放眼世界的章士钊,自然气宇非凡,挥笔写字,也不会在一隅拘泥。从他的书法中,可以看到历史遗韵,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强烈的生命特征、情感形态。因此,读章士钊书法,必须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文才学养结合起来,我说了,他是通人,他的背景广阔。
1949年以后,他与友朋交往,依旧保持手札往复的习惯。其中的典型例证,就是与毛泽东的手札往复。遗憾的是,他与毛泽东的手札真迹,作为历史文献,自然封存了,我们无法看到。不过,从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手札中,可以反观章士钊手札的分量。毛泽东回复章士钊的手札一丝不苟,那通写于1965年7月18日的手札,书法超迈,理据充分,语词信息丰富,可见毛泽东的心理波澜和文化趣味。与毛泽东的手札,我们看到的是文字,语言凝练、古雅,情感真挚、纯朴,礼数周全、细致,那份士子情怀,学人风度,从手札文字中明确感知。只是手札墨迹无从见到,我相信,那通手札的书法,一定谨严、含蓄。
好在与其他友朋的手札是容易见到的,比如写给潘伯鹰、高二适等人的手札。这部分墨迹,是我们研究章士钊书法的基础。章士钊与潘伯鹰关系有一点特殊。潘伯鹰夫人张荷君与章士钊有亲戚关系,是章士钊的“义女”。早年,潘伯鹰从学章士钊,研习逻辑学。潘伯鹰辞章、书法俱佳,深得章士钊信任,被称为“生平第一知己”。1949年,章士钊作为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潘伯鹰以私人秘书的身份随行。
“连得数书札”,是章士钊晚年写给潘伯鹰的手札——
伯鹰足下:连得数书都未即覆,素性固懒,时亦有迫促之事,无暇作书,想伯鹰能谅之也。近忽有赴港之议,俟周公在人大作报告之后即可成行。昨晚因得一诗如次:《南行柬伯鹰》南行无计过江湄,故旧如君竟久违。耻借残年谢蒐讨,也缘清恙省书诒。早知岁月迁流极,安事文章绮丽为。试乞西窗待归客,秋风一路倘逶迟。滞港之期约为半年,秋风起时欲绕道上海一图良唔,暂亦姑妄言之而已。尊恙来者,言人人殊,然大旨全快可得,喜慰殆不可言。闻荷君侍候心劳,微形憔悴,此之安神闺房,有仲长公,理所不敢忘君,果何福以致之耶。他日当有专篇为荷君先生致谢,暂不一一。手颂痊祉。士钊谨状。三月廿三夜。
只写月日,不署年份,这是手札的惯例。不过,从陈述中,我们可以推论手札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73年。前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将章士钊的著作《柳文指要》赠送。中美关系缓和,章士钊计划去香港与台湾当局代表讨论两岸统一问题。1973年夏,章士钊启程访港,遗憾的是,年事已高的章士钊已经经不起折腾,酷热的香港让他难以接受,到港后不久突然辞世。
与潘伯鹰的手札,是章士钊生前最后几通手札之一。
清雅萧疏的行草书,宽博、疏朗的字距,真情的陈述,沉郁的诗作,体现了章士钊旧式学问的深挚,手腕的灵动,思维的敏捷。“伯鹰足下”四字,圆润、饱满,所录诗作,一气呵成;“滞港之期”的“滞”,是草书,神采飞扬。“他日当有专篇为荷君先生致谢”,言及潘伯鹰夫人荷君,平阙一格,以示尊敬。
随手札呈诗,或赠答,或求教,是中国文人的雅习。陈寅恪、叶恭绰、马一浮、谢无量、俞平伯、周作人、叶圣陶等人的手札,经常附有诗作,或写在手札正文,或另纸抄录。章士钊与潘伯鹰的手札,随处可见诗稿。在章士钊看来,潘伯鹰是“生平第一知己”,也当是诗的知音。
诗稿《三得伯鹰书》是一首七律,抄录后随手札寄奉潘伯鹰。
平生不愿故人怜,端为酬恩碍著鞭。
老去才情余黯淡,从亡风味受扳联。
三年中兄关诗债,五斗先生为酒钱。
吟罢与君成一笑,云山无尽意无边。
士钊录稿。
诗稿未著时日。书法的苍劲与古拙,预示着写于晚年。诗,陈述了自己的人生感受,表白了与潘伯鹰的友谊,可见道家情怀。书法沉稳,笔锋犹存,“士钊”署名,器宇轩昂。
诗稿《题沪上周吴故事》,是两首七绝,感叹周炼霞与吴湖帆的才情和浪漫故事。
惯耳周师入晋阳,奈何中道下吴阊。
料知一舸西施去,便与夷光较短长。
二窗微妙旨如何,比并樵风倘较多。
若起弢庵更题句,难言断送几年过。
何以作诗,章士钊写了一段跋语:
天佐返京为其周吴近得赁小房子,此定在伯鹰处,闻此消息,似不失为一诗题,因发意写二绝如右,此等诗似不妨持示文通共博一粲。
诗起于周炼霞与吴湖帆的浪漫故事,固诗与书法,也轻松活泼。两首绝句空阔、消散,一个字的涂抹,增添了自由的趣味。诗稿墨迹左侧,言明典故和诗兴起因。在章士钊的诗与书中,仿佛看到当年沪上“体态清丽婉转,如流风回雪”一般美丽的周炼霞与“官三代”的沪上才子吴湖帆的花边新闻。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章士钊,浪漫的一面昭然若揭。
章士钊,最后的士大夫。作为政治活动家,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交往,即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奔走。他又是学者、诗人、书法家,他的治学、吟诵、挥毫,注定是中国文化耀眼的一页。
(张瑞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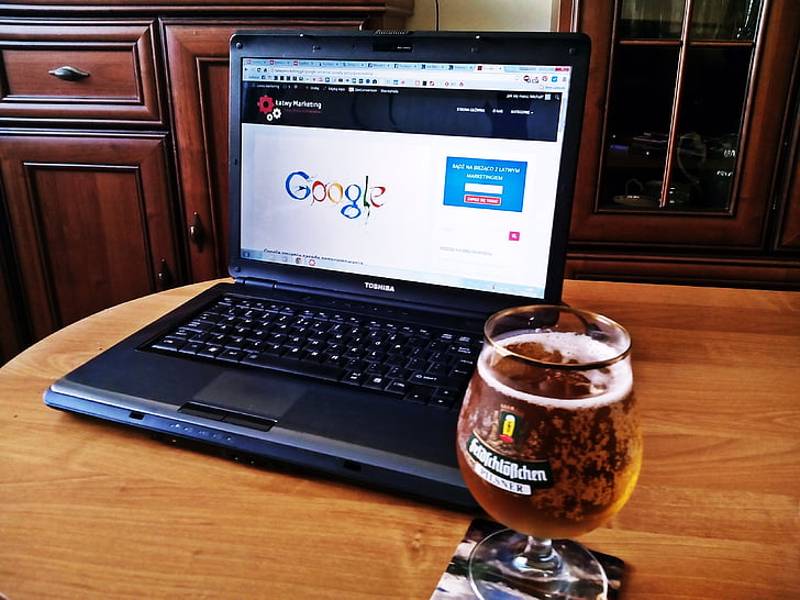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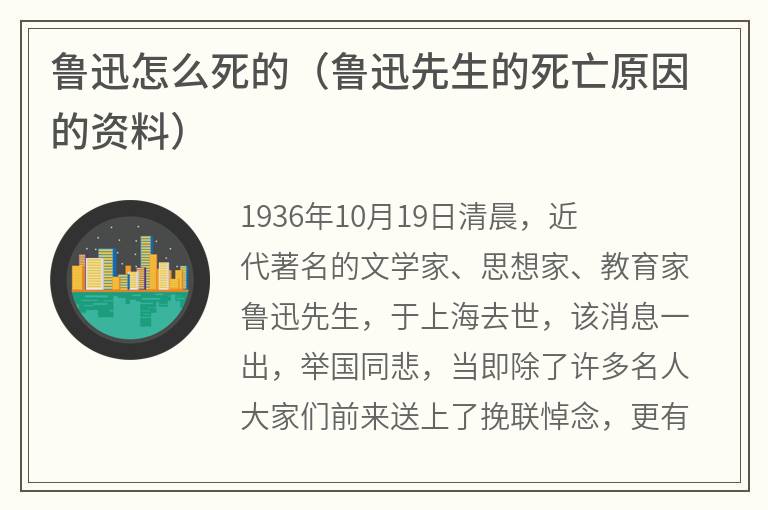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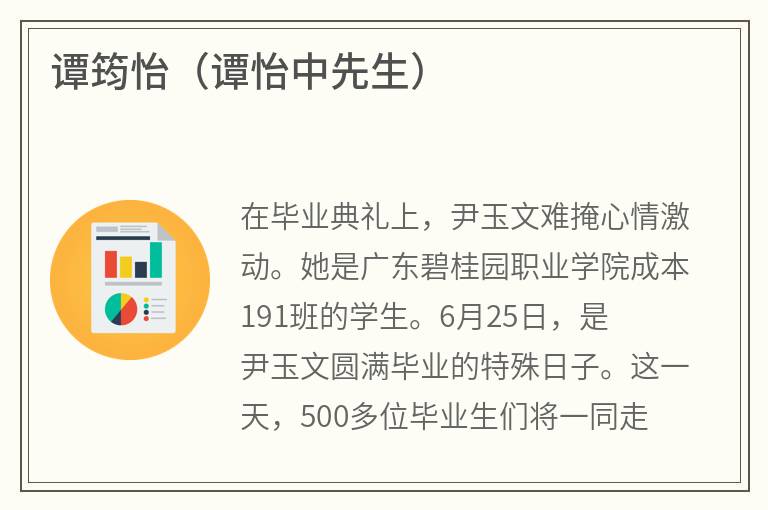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