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文/张明远
《金瓶梅》中存在着大量的赤裸裸的“性描写”,对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甚至是绝然相反的评价。如何看待这些描写,直接关系到对《金瓶梅》的整体评价。本文以明清两朝为例,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相关评价与诠释进行了系统整理。相关引用材料主要来自黄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和朱一玄的《金瓶梅资料汇编》(2),个别地方参照他书作了一定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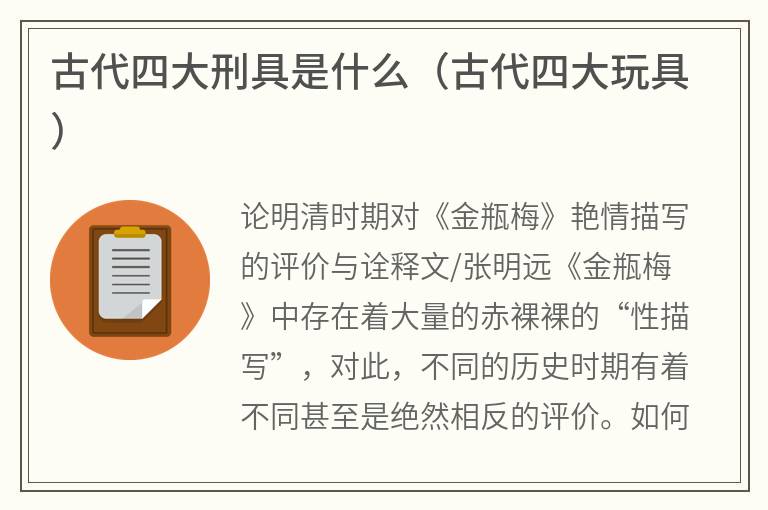
古代四大刑具是什么(古代四大玩具)
一、《金瓶梅》艳情描写存在的版本问题
对于《金瓶梅》,袁宏道曾极力称赞,言“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殇政·十之掌故》)。但是,这句话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如王昙就曾认为,现在的《金瓶梅》只是一个“俗本”,内容与“原本”已经大相径庭。其原本“珍珠密字,楷法秀丽”,“不似流传之俗本铺张床笫等秽语”(《金瓶梅考证》)。蒋敦艮亦称游禾郡时,“见书肆架上,有抄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绘图真本金瓶梅序》)。因而,他们推断其真实的情况便可能是:“《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袁照《袁石公遗事录》)
当然,有人认为王昙的考证本身就是一篇“伪作”,蒋敦艮的“真本”更是一种谎言。对此,我们暂不予讨论,但对于他们所提“原本俗本”的说法,学术界基本还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郑振铎便认为蒋敦艮的“真本”只是“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删一气”(《谈<金瓶梅词话>》)而已。
在文学发展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出现,往往会带来一股“跟风”现象。例如,单单从后续书的命名上来讲,“有《金瓶梅》,遂有《银瓶梅》;有《儿女英雄传》,遂有《英雄儿女》;有《三国志》,遂有《列国志》”(浴血生《小说丛话》),可见其影响的深远。《金瓶梅》更是如此。自诞生伊始,它便充满了一种神秘梦幻的色彩;书未刊刻,已经让当时的那些大文学家们寝食难安了,“遍求全本而不得”,其魅力可见一斑。然而到了清代,《金瓶梅》已同其他“淫词小说”一样成为一种禁书。公然刊刻已是不许,于是改头换面,“原本”“真本”之复出,亦是常理。自然,这种所谓“原本”的幌子,无疑给了《金瓶梅》一种很好的开脱和安慰。同时,社会环境急遽变化的清代已经和明代完全不同。在清代空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下,清人自然难以理解大名鼎鼎的袁中郎之流,为何会不顾身份极力赞叹一部充满了“琐语淫词”的“诲淫”之作。无论是故意、善意还是无意的掩饰,这个“原本”之说可能都是子虚乌有。在没有确切证据发现之前,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假设”更为合适。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最初的词话本系统,还是后来的绣像本系统、张评本系统,都是存在大量艳情描写的,并不存在一个干干净净、没有艳情描写的所谓“原本”《金瓶梅》存在。当然,后世各种各样删减而成的“洁本”则自另当别论。
二、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金瓶梅》的诞生,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从充满刀光剑影的传说,到民间的争相传阅,到朝廷的明令禁止,乃至成为“诲淫”之代表。因而,对其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下面我们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择其精要者,简单梳理一下明清两朝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不同评价和诠释。
(一)明代(约万历年间—1644)
按照吴晗先生的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一五八二——一六〇二)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成书之后,最初是在文人间以抄本的方式流传,后来苏州或杭州(即所谓“吴中”等地)便有了刻本,其后才有了丁巳本的《金瓶梅词话》。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还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统治阶级亦渐趋腐朽,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进一步削弱。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个体个性的突出张扬与人欲的直接显露。这应该也算是元代“尚俗”风气之影响与表现。因而,明代文人政客对《金瓶梅》艳情描写之态度,也相对宽容一些。他们的评价、诠释,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欣欣子以为“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但《金瓶梅》所表现的却是“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从而断定“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金瓶梅词话序》)。廿公亦认为《金瓶梅》“盖有所刺也”,并批评那些“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金瓶梅跋》)。谢肇淛认为《金瓶梅》里的“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以及“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等等,都是“穷极境象”,写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还特别点明:“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金瓶梅跋》)《金瓶梅》和“君子无取焉”的《玉娇李》是完全不同的。
在明代,对《金瓶梅》评价最高也最特别的,当数袁宏道。在《殇政》中,他曾将《金瓶梅》和《水浒传》并举,称之为传奇“逸典”,并认为《金瓶梅》“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有些人曾对“逸典”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袁宏道当时看到的《金瓶梅》并非我们今天所见者,应该有一干净“原本”存在。这个问题上文已有阐释,此不赘述。但对于“云霞满纸”,又该如何来理解呢?徐朔方先生认为“‘云霞满纸’只是形容文章言情状物之妙”(3)。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理解是妥当的,但从整部《金瓶梅》来看,这样理解或许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从《金瓶梅》本身的特性入手,把握其“香艳唯美”的特质。因而,“云霞满纸”亦应同时蕴涵了《金瓶梅》繁复多样的艳情描写,恍恍漫漫,灿若云霞。至于下句“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则似乎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魏子云先生干脆认为《金瓶梅》和《七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从而断定袁宏道书信之伪或与我们所见版本之异。对此,袁世硕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恰恰显示了《金瓶梅》在“始邪末正”、“劝百讽一,势不自反”等写作特点上对枚生《七发》的超越(4)。这是非常正确的。显然,《金瓶梅》在艳情描写上“盖为世戒”,也具有一种“劝百讽一”的效果,而且还大大超越了枚生的《七发》,这也算是对《金瓶梅》的一种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明天启、崇祯年间,还首次出现了一本采取眉批、夹批等方式对《金瓶梅》进行专门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其批点者不详,但纵观全书,点评者对《金瓶梅》还是颇为欣赏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那种“令人魂消”(第二回夹批)的喜爱。对于其中的艳情描写,作者甚而尖锐地认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第一百回眉批)在评点者眼里,那些“媚极”、“骚极”(第四回评语)的文字,“分明秽语,阅来但见其风骚,不见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第二十八回眉批)。这触及到了艳情描写深层的一些东西,并将其归结到原书作者的手法、寄托上,还是颇有见地的。这种评点方法,也成为清代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滥觞。
第二种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金瓶梅》是大毒草,必将流毒社会,必须尽速“铲之除之”。如董其昌虽认为《金瓶梅》“极佳”,但应“决当焚之”(转引自袁中道《游居柿录》);李日华亦认为其“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味水轩日记》)。沈德符更是认为:“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亦大声疾呼:“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综观此种观点,还是因为《金瓶梅》中存有大量的艳情描写,有“诲淫”之嫌,因而招致强烈反对。
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金瓶梅》是“秽书”,对里面大量的艳情描写提出了一定批评,但同时又肯定其全书的价值。如弄珠客既称《金瓶梅》是“秽书”,又认为作者创造这部书的真正目的“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并解释“袁石公亟称之”的原因是“自寄其牢骚耳”,而不是“导淫宣欲”(《金瓶梅序》)。
持此种态度最典型的莫若袁中道,他在《游居柿录》中写道:“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认为对《金瓶梅》可以听之任之,任其自然发展即可。这种评价倒是颇有一种大家风范。
(二)清代(1644—1911)
清代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并在历史上首次把《金瓶梅》等作为禁书加以禁毁。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清代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诠释评价,主要表现为:
一是坚决反对《金瓶梅》的艳情描写,认为该书是“诲淫”之作。在清王朝将《金瓶梅》等书列入禁书之后,这一观点显然占了大多数。如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编》云《金瓶梅》等书“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郑光祖认为“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轨,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胥难挽也”(《一斑录杂述》);林昌彝更是放言:“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砚耒圭绪录)。他如闲斋老人云:“至《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儒林外史序》)李海观云:“若夫《金瓶梅》一书,诲淫之书也。”(《歧路灯自序》)昭梿云:“《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啸亭续录》)即便以写人写妖耿介叛逆著称的蒲松龄,也将《金瓶梅》称为“淫史”(《聊斋志异》卷八《夏雪》)。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否定者认为世传《金瓶梅》为一“俗本”,故“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袁照《袁石公遗事录》),此皆因其没有读到“原本”、“真本”的缘故。前面提到的王昙、蒋敦艮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实际上是以“原本”、“真本”的存在,否定所谓“俗本”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
另外,有些批评者甚而不惜以“报应论”、“迷信论”等牵强附会,痛陈《金瓶梅》的淫色之毒。例如申涵光云:“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荆园小语》)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淫书版”更是记载了苏城杨氏因为刊刻售卖《金瓶梅》“而为病魔所困,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尚未育子”的奇事。待得友人提醒,才明白是“天故阴祸”。劈版焚毁之后,“自此家无病累,妻即生男”,数年间便“家业骤起”;而另一扬州版书贾某不听规劝,“竟死舟次”。
二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诠释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写这些“艳情”是有“寄托”的,但这种写法却遭到大多数人的“误读”和“误解”。如郝培元云:“后生小子不解《金瓶》之用意,直诲淫具耳。”(《梅叟闲评》)鸳湖紫髯狂客云:“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乃误风流而为淫。”(《豆棚闲话评)爱日老人云:“不善读《金瓶梅》者,戒痴导痴,戒淫导淫。”(《续金瓶梅序》)平子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小说丛话》)王钟麒云:“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吴沃尧云:“《金瓶梅》、《肉蒲团》,此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者之难其人矣。”(《说小说·杂说》)
关于小说的创作动因,诠释者认为,“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平子《小说丛话》);而对于其中的艳情描写,“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从而形成了误读和误解。而实际上,“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鸳湖紫髯狂客《豆棚闲话评》)。对这一点,刘廷玑的概括可谓精辟:“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5)(P84)故非善读者,不能发现其奥妙。这实际上可归于一种主旨阐释,也为《金瓶梅》艳情描写的客观存在找到了一个可让世俗接受的理由。
清代还出现了两大著名的评点本,分别是张竹坡的评点和文龙的评点。张竹坡赞同冯梦龙“四大奇书”的观点,并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为之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评论。对于其中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他还单独写了一篇《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重点驳斥了时人对《金瓶梅》的错误看法与偏见。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从根本上否定了《金瓶梅》是“淫书”的观点。他痛斥道:“《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欲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6)(P46)这一开创性观点,成为后世研究《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至于文龙对《金瓶梅》的批评,过去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待到刘辉将其辑录整理后,才慢慢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金瓶梅》艳情描写的问题,文龙的看法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何以谓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丑态,以至家败人亡,后事直有不可问;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第七十五回评)在第一百回的评语中,他进一步总结道:“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此外,他还详解了其中的原因:“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观此书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第十三回评)这几问环环相扣,发人深省。其实淫与不淫,在文龙看来,多在于读者自己的定力如何,而不在小说本身。
三是对《金瓶梅》的艳情描写仍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其中不乏那些持正面意见者,如上面提到的文龙,在对待《金瓶梅》艳情描写的问题上,较竹坡则更为细致和严谨。比如,虽然他认为《金瓶梅》不是淫书,但是有些细节还是应该注意的,例如“年少之人,欲火正盛”,那么就“不可令其见之”(第二十七回评)。至于有些成年人,也是要区分情况,“看亦可,不看亦可”(第二十七回评)。又如曼殊认为:“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小说丛话》)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其他方面的价值与贡献。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清专制统治下文人那种特有的诠释心态。
三、对《金瓶梅》艳情描写之诠释的时代背景及其他
《金瓶梅》的艳情描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诠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学文本的诠释,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差异化的诠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影响诠释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每个人都有他生活的局限,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时代条件的限制。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诠释问题,同样如此。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皇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逐渐走向腐化与堕落。有的皇帝隐居深宫,一二十年都不见朝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怪象。加之当时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使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政治思想上的控制。而清王朝则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统治之下,被统治者斥为“诲淫”之作的《金瓶梅》会受到何种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不对那些小心谨慎的诠释者产生影响。
其次,统治阶级不同的文化政策,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方面,朱元璋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左右群臣和劳动人民的控制;采取压制通俗文学的措施,并在明初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统治者个人享乐的需要,他们有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打破这种禁令。比如朱元璋本人就喜欢评话,也鼓励那些藩王子孙们寄情于歌舞享乐。上层统治者带头喜好俗文学,也就客观上破坏了当时的文化政策,为俗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毕竟,明朝是元朝之延续,元代文学所弘扬的那种“尚俗”的主旋律,还是有深刻的大众基础和历史影响力的。到明中叶以后,统治者渐趋腐败,对社会的思想控制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因之,当时的文人,即便谈论闺中之事,“实亦时尚”(7)(P162)。
清朝建立后,虽然在制度设置等方面依明旧制,并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文化控制社会,但仍实行专制和高压的文化政策,独尊程朱理学,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其残酷性、频繁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实行书禁政策,将大批不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书籍加以禁止焚毁,防止危及王朝统治。康熙五十三年上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尚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而朝臣也拟定了具体的施行办法:“凡书坊一切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着将板片书籍,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8)(P752)这样,《金瓶梅》在清代便成了“小说淫词”,在历史上首次受到官方的严厉禁止。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
再次,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对诠释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首先要解决物质方面的需要,然后才会有精神层面的追求。文学的发展与认识也是如此。当社会发展到富庶开放的程度,社会就相对开明得多。比如明朝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迅速繁荣起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也进一步扩大。这时候,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便在社会上兴起,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趋向世俗化。清朝虽然实行书禁政策,并大力推行高压的文化措施,但到了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诠释趋向自觉。这时候,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阐释便逐渐多了起来。《金瓶梅》及其艳情描写在清末民初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与理解,也是时势使然。
第四,不同身份的诠释者有着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诠释者,不同的诠释心态,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诠释。对于《金瓶梅》,有好之者,有恶之者,有凭心而论者,有不得已而曲解者——此皆由不同的诠释者及其不同的诠释心态所致。这些诠释,有的显示了文人之真性情,虽身处高位,亦不加掩饰,如袁宏道等人,其率真直达宛若明末之小品文,随情任性,唯心所适;有的则曲意解之,牵强附会,演绎出一段段传奇恩怨来。由于受自身、受时势所限,故其诠释亦多种多样,但其中亦有一基本规律:高层禁之,民间好之;社会宽松时誉之,社会严苛时诋之。毕竟,在其位谋其政,这其中还有一个统治阶级把握和引导“时代主旋律”的问题。到了近现代,《金瓶梅》则基本上已完全脱去了“诲淫”的帽子,比如鲁迅、郑振铎等人,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
最后,社会思想状况是影响诠释的一大因素。社会思想状况是影响文学诠释的一大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敏感题材诸如艳情等的诠释,尤其具有影响力。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王学左派兴起。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核心思想便是“致良知”。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主观唯心的,但它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回到人的“内心”,变为人内心一种自觉的“良知”,这就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思想的解放。因而,明朝末年社会思想状态就非常活跃。清初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推行书禁,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社会则变得异常沉闷。然而到了清末,当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之时,社会重又变得活跃起来,对《金瓶梅》等书的评价也逐渐转向了积极、正面。
参考文献:
(1)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徐朔方.答台湾魏子云先生——兼评他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1).
(4)袁世硕.袁宏道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释[J].明清小说研究,2008,(2).
(5)刘廷玑.在园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张竹坡批评《金瓶梅》[M].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