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名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德尔斐神庙,第一条神谕:认识你自己
整部哲学史的主题是,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前者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后者是现代的、尼采式的。
但人们并不能很好地、真正地认识自己!因为,你的认识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用精神分析学的话来说,(个人的)意识总是被(集体的、社会的、文化的)无意识所包围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拉康改写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思”。
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和需要,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找那些决定我们精神状况的社会条件,从而去改变它们对人的自由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你自己”——热爱自己的命运。哪怕自己是一个博士生清洁工,也不觉得委屈。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某种逼迫所致。

▲《完美的日子》剧照。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即职业不应该成为让人觉得“脸上无光”的东西,可以看一部戛纳封帝作品《完美的日子》。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位洗刷厕所的清洁工,他放弃了本来优渥的生活。马克思也说过,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他可以白天干多种活,晚上从事批判。意思是,自由人不必出租自己的身体,劳动应该恢复其创造性和自由面目。)
这种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的转变,是马克思最为鲜明地提出来的。他反对哲学的理论化,将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从“解释世界”变成“改变世界”。但这个改变决不是静态的、固定的。尤其是不能停留在制度化的、纸面上的“法律文件”那里。因此,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终结状态,而是永不停歇的生命运动。
尼采在既肯定生命,又主张“整体”方面,跟马克思是一致的。因此,存在着一个尼采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遥相呼应。这两个人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阅读过彼此的著作。而时代精神往往具有某些类似性。尼采也强烈批判资本主义。
如今,资本主义让一切人都受苦,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我们正从一个规训社会,走向控制社会。权力、资本、技术、数字,等等,让人类社会从彼此奴役走向自我奴役。社会主义之所以再度兴起,正是人们出于抗争悲惨命运的需要。那些“唯我独醒”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看到这里肯定会发出淫荡的笑声:什么社会主义啊,难道社会主义不一样害人么?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尼采是如何拥抱社会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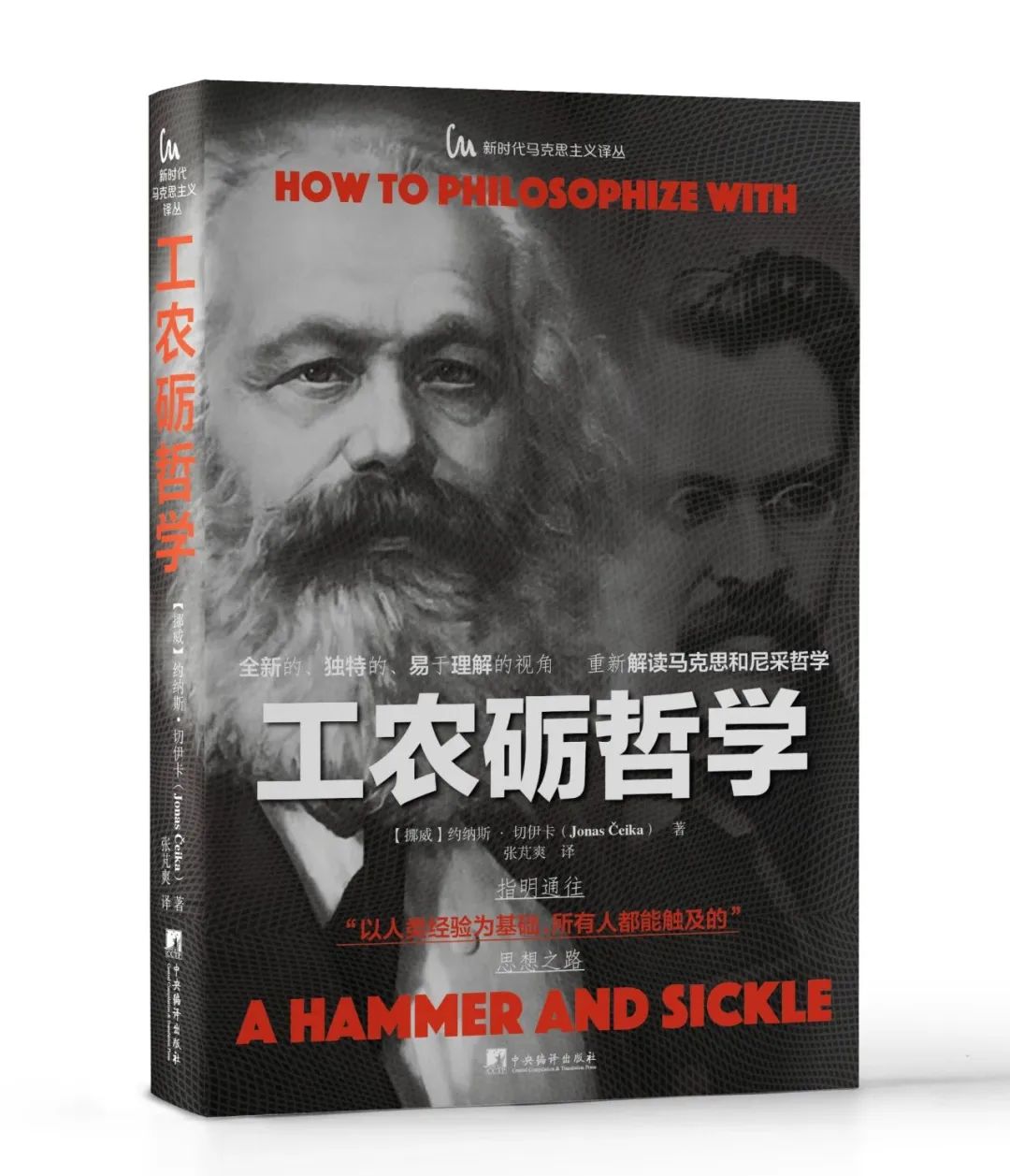
《工农砺哲学》是我今年目前读过的最佳书籍。这本书的副标题是“How to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 and sickle”(怎样用锤子和镰刀从事哲学)。不要想多了,其寓意再也简单不过:哲学应该还原为普通人(“工农砺哲学”的“工农”)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学术分工之下的、躺在纸张上的高头讲章。
作者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因此这本书的每一页每一行每一字都令人感动。所以,这里没办法将它全部介绍给读者。我只对该书的两个总括性的部分,“引言”和“结尾的前言”,进行提炼。从中,我们就得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
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1843年9月,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怀疑是针对理论的,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因此,别人的“看法”“说法”,包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是应该怀疑的。这跟笛卡尔的“我思(怀疑)故我在”是一致的。但马克思还有另外更进一层意思:理论是后于现实的,各种理论之所以应该怀疑,是因为理论往往容易歪曲现实。
我的哲学,如果我有权称之为折磨我到我本性根源的东西,那么它不再是可传播的,至少在印刷品中没有。
——1885年尼采致弗朗茨·奥弗贝克
理论为什么容易歪曲现实?尼采,在维特根斯坦发动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变”之前,就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尼采说自己的哲学“至少在印刷品中”是找不到的!这跟马克思的哲学主张,完全一致。马克思多次强调,哲学应该是实践的,社会生活才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人类精神活动、政治、法律等等)的根源。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知识分子、以往的哲学家,都容易将自己装扮成巫师、祭司,并且因此而获得了“知识即权力”的巨大私利。社会矛盾之所以没办法得以和解,就是因为特权阶层并不认为被奴役者是“我”的一部分。“工农”作为生产者,只能依靠自己来“砺”(打碎)骗人的理论哲学,而挣脱锁链,获得自由。
但,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工农”,所有人都容易被“真理”所迷惑,从而停留在“认识你自己”的自我想象阶段,而不能或不敢走向“成为你自己”的生活实践。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有迷惑性的!中国有“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西方则有对“真理”的敲打,他们认为除了神之外,人是不可能拥有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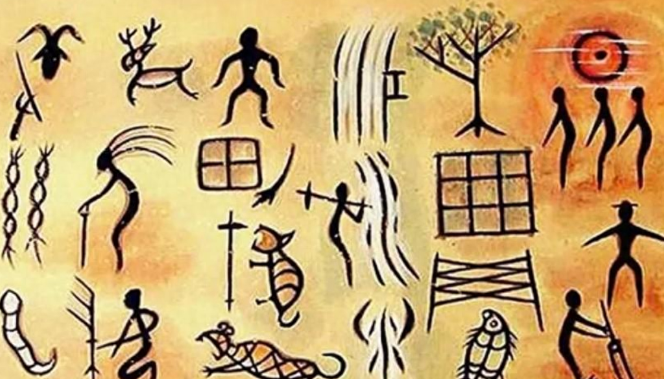
因此,什么是真理?真理即一群运动着的隐喻转喻和拟人化,简单来说,即一组以诗意的和修辞的方式被提高、转化和修饰了的人类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在长久的使用之后被一个民族视为固定的、规范性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人们已经忘了其为幻觉的幻觉,是被用坏了的、失去感性力量的隐喻。
——尼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尼采之卓越,在于他最早明确地发现了语言的秘密。因此,他影响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辈大哲。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革命,其实应该归功于尼采和马克思。“语言学转向”的实质,就是揭示语言对存在既“去蔽”也“遮蔽”的真相,让人们关注整个存在,让人类走向团结,让思想构建的“真理”笼子遭受锤击。
尼采认为,语言不是对外部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存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尼采用德语的Wolf(狼)反映人们是如何创造这个词语的。Wolf最初表现的是人和狼的生活联系,但用着用着,人们就失去了当时的场景,Wolf最后成了一个不再生动的声音或书写。因此,语言本来是为社会合作服务的,但最后变成了概念,故尼采说“真理”是“是被用坏了的、失去感性力量的隐喻”。
这里引申一下。一个人是否聪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否“有悟性”,实际上是指这个人对语言隐喻性的体验能力。“聪明人”往往是“话中有话”,因为他知道一句话往往不是表面上的那种意思。拉康说过,所有话语都是“半说”,这就深入到了人的无意识层面。而正是这个无意识在决定着每个人的存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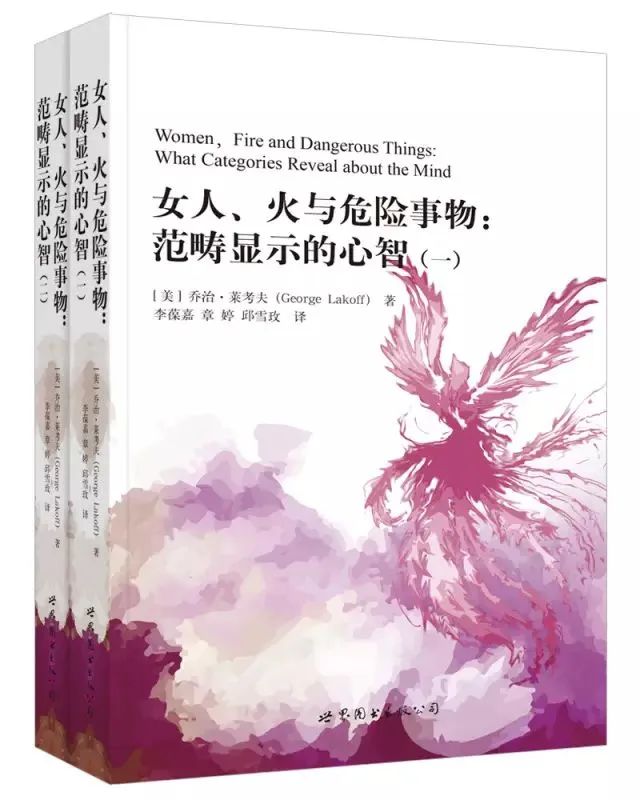
关于语言的隐喻性质,乔治·莱考夫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肉身哲学》《女人、火与危险事物》都是可读的参考书籍。另外,谢林在近年的重新发现,也是因为他的哲学具有强大的隐喻性,人们可以从中读出宇宙大爆炸、精神分析学等后现代品质。
尼采的语言观,必然通往社会革命。《工农砺哲学》的作者约纳斯·切伊卡写道:
这种说法的意义何在?它将语言本身置于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哲学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各种语言学的交流被说成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但是,如果语言交流本身从根本上包括以隐喻方式表达的社会关系,那么直接参与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就可以成为解决哲学问题的一种方式,只是没有语言的中介。
因此,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当时他在博士论文中主张哲学必须成为世俗的,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如果哲学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那么就有可能去掉被称为语言的中间人,通过处理社会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
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即,主体(真实的、生活的、生产的人)与它的客体(人类在生产中利用的自然及其资源)的疏远,被康德认为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到了马克思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主-客二分”,“这种异化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因此这是个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将通过让生产者直接控制他们的生产资料来消除异化,从而消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严格分离。”到了尼采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用“闪电”进行哲学思考的案例——作为哲学方法的革命。最抽象的哲学,不过植根于最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和事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以外的手段,来解决传统的“主-客二分”这个哲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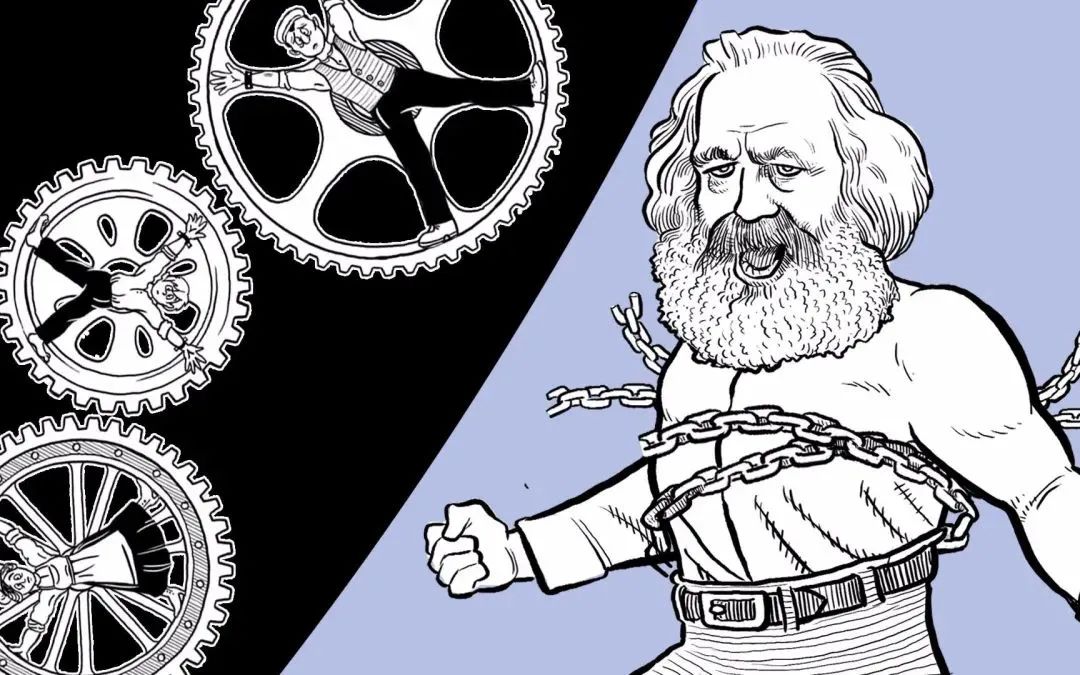
约纳斯·切伊卡:“我们将给马克思一把锤子
来砸开所有压在他身上的历史瓦砾。”
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容易被严重误读的人。约纳斯·切伊卡说:“可怜的马克思——甚至比尼采还要可怜——被迫承受许多可怕的肢解和变异。通过理论上的扭曲和实践中的误用,他改头换面,从一位想要完全超越现代性范畴的思想家转变为一位只想改造某个特定现代性领域的思想家:即社会民主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甚至民族主义者。”
但实际上,马克思和尼采一样,都是为所有人说话的人,都不是想用自己的学说来谋求改造世界的人。真正危险的人物,是那些拿自己的学说当作“救世良方”的“大人物”,他们必然攀附特权阶层。例如,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有这样的危险。(这是我上一篇文章《》没有深入的话题,本文可以作为补充。)
尼采强调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而写”。意思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接受奴役,这是人之为人的第一原理。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没有其他目的,除了: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尼采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对奴役和被奴役的强烈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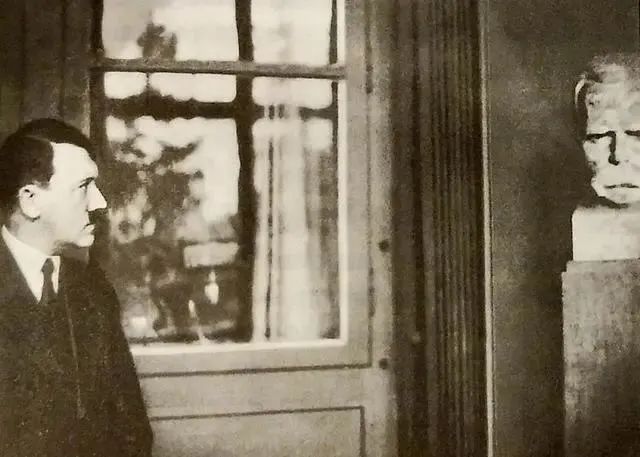
希特勒凝视着尼采的雕塑
尼采不想自己被树立为人们的偶像,或被塑造为思想的雕像。约纳斯·切伊卡写道:“一个思想家变成一座纪念碑,就等于他们的死亡”。
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由于其实践性、生活性,因此必然是革命性的。他们追求的,不是“合法”,因为,“合法化的文件”都是静态的、机构化的、权力化的。他们的“破坏”和“激进”并不是变成残酷,而是生命自身的不断超越。
但,人们往往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奴役,因为,“对于奴性的人来说,外来事物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它的内在密度缺乏透明度,以及从它的角度理解事物的难度。”不仅“认识你自己”是困难的,“成为你自己”则难上加难。但,总有人不想这样活着。马克思和尼采,一起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变革生活的可能性。《工农砺哲学》一书的最后这句话,无疑是激动人心的:
社会主义和生命肯定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或从天上摘下来、然后强加给世界的理想。相反,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可能性,由已经存在的条件使之成为可能,甚至是必要。走向社会主义和肯定生命的趋势已经存在,就像花朵绽放的趋势已经存在于它的种子中一样,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为扩大这些趋势而奋斗。同时,这种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因为逆潮流而动者总是威胁要在种子成长起来之前将其压垮。我们所需要的是点燃肯定的倾向,推动并释放它们蔓延开来,直到实现其最快乐的潜力。
(第一次求赏:那些因为本文有所顿悟的人,读到这里,可以打赏一元钱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