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共6709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父子:男人的世界
说到家庭关系,首先就要看一下家庭当中的父子关系。为什么从父子关系开始呢?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关系的主轴就是父子关系,而不是西方的夫妻关系。
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权性质有关,一个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让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断了香火”,即家庭和家族无法延续,而一个只有孤儿寡母,没有父亲的家庭,也会让人觉得这家门户“无所依傍”,很难发展得好。这些传统的观点都印证了父子关系是家庭最重要的关系。

那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父子关系有哪些特点呢?
这种关系首先体现在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掌控权”上。例如按照儒家伦理规训,儿子必须要孝顺侍奉父母,父母亡故以后,服丧是儿子应尽的义务。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把男子娶妻称为“娶媳妇”,而不是“娶妻子”?因为“娶媳妇”是以父母的名义而娶亲的,“娶妻子”是以儿子的名义娶亲的,如此看来,我们惯用的叫法其实也暗含了父子关系的重要性。
所以,父子关系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传统社会对儿媳妇的要求上。例如在云南的喜洲,如果妻子与公婆发生争执,丈夫必须不问缘由地与父母站在一边;同样,儿媳妇的第一责任是孝敬公婆,其次才是服侍丈夫。
丈夫如果死了双亲,那必须表现得悲痛欲绝,但如果没有了妻子,即使再痛苦伤心,也要时刻谨记儿子对父母应尽的“孝道”。
“父慈子孝”是传统社会对美好的父子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概括,但绝大多数父子关系中,父亲的严厉与儿子对父亲的惧怕是最典型的,这种典型莫过于贾宝玉与其父贾政的关系,儿子见了老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在家庭中,父亲的威严以及权威,不容置疑地要求儿子顺从于他的意志。
需要注意的是,父子关系中其实也强调了儿子对家庭的重要性。
这体现在民间普遍存在的求子活动上。云南地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火把节”。在节日的晚上,云南各地的村子里,居民们用稻草和竹子扎成大火把,将这些火把设置在村子各处。火把的顶端是一个用纸做成的斗,这个斗是一种称粮食的工具。
等到活动开始的时候,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就会聚集在火把的周围,一个成年男子通过梯子爬到高处,把火把点燃。等到火把烧到顶端,上面的大斗将要落下来的时候,众人一拥而上,开始抢这个斗。
为什么要抢这个斗呢?据说,谁能够在空中接住这个斗,谁家就能在来年抱上儿孙。来抢斗的很多是新婚夫妇,甚至一些有钱人家花钱雇人来抢斗。不难想象,抢斗的过程很有可能引起斗殴。这样的节日盛况,反映的便是对“儿子”的需求。
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父子关系——过继。
过继一般是指收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男孩。在传统社会中,上了年纪而又没有儿子的父亲是非常苦恼的,甚至连隔壁邻居也会对他产生同情。在云南的喜洲镇,家中无子的父亲越是势力大、越是富有,就越容易成为别人嫉妒和同情的对象。于是,他会从父系家族中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作为养子,也就是让其过继给自己做儿子。
很多人会认为养子不如亲生儿子那样亲,养子对养父也不会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很多时候,养子不仅得不到父子情感上的满足,甚至可能做不到共同生活,负责对养父母基本的照料。
当然也不会全都如此。史学家萧公权幼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奔波,于是便将其过继给伯父。他在回忆录中分别提到过他与养父、生父的情感。
养父对他非常严苛,管教非常严。萧公权八九岁的时候,还很淘气,经常嬉闹跑跳,养父便严词谴责他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但是养父知道他读书用心,也会称赞他,不惜重金请名师教他读书。
在巨变的时代,养父也多为他的未来考虑。他曾经替萧公权捐官,打算等到萧公权20岁送其进京就职。但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萧公权向他表示想考取新式学堂,他经过考虑,还是亲自送萧公权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萧公权与亲生父亲的关系也很独特,虽然对父亲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但他12岁父亲病逝时嘱咐:“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以后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这临终的嘱咐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过继”而产生的父子关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但也不可否认,一个无人照拂的孩子在过继之后,可能会受到两个父亲的正面影响和爱护。
父子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父权”式微在近现代之后越来越明显。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东北农村进行研究时,一位74岁的老人说,1949年以后,农村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这第一个变化,虽然只是象征性的说法,但却指出了父子关系的改变。
在农村家庭当中,由父辈来掌控家庭财产、资源、决定权的情况逐渐变少了,即使是由老一辈当家做主的家庭中,也有一半父母承认,他们管不了儿子、儿媳妇了。
父子关系的改变可以从婆媳关系中得到印证。在传统社会中,儿子是与父母站在一边的,这样才能体现他的“孝顺”,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父母开始抱怨儿子不向着他们,结了婚的儿子通常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妻子。
他的研究反映了费孝通所观察的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为配轴”的传统中国家庭形态的式微,夫妻关系逐渐取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
父子关系的变化还可以从家庭居住空间的改变中获得启示。
在东北,20世纪70年代以前,靠近锅台的炕头是最好的地方,都是给家里男性长辈留出来的;但随着80年代后期新居的改造或扩建,很多长辈被“迁移”出新居,只得住在破旧的老房子或者即使留在新房子里,他们的居住空间也不再是最好的位置,年轻的夫妇占据最好的东屋。
可见近代社会以来,父子关系从传统的父亲掌握权威、对儿子继承香火的看中,转变为儿子成为家庭的主导者,夫妻关系超越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这反映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改变。

夫妻:社会的最小组织单元
前文提到,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是主轴,夫妻关系是配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夫妻关系的特征,以及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可以先从语言的角度发现夫妻关系的特征。在中文中,“妇”从“伏”中引申出服从、忍受、甘当配角的意思。所以,妻子就是服从和协助丈夫的。
“妻”是从法律上对妻子的概念称呼,既然是妻,就不是妾,那么她就在社会上享有和丈夫相同的地位和声誉。“妻”也就是“齐”,代表着平等。这种法律上的身份,其实也意味着女子在结婚之后是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的,她的身份来源于她的丈夫,必然就归属于她的丈夫。
在传统中国社会,对妻子的别称还有“室人”和“内人”把妻子称为“室人”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男子结婚时得到的与妻子共处的房屋,第二是指他的妻子与这个居室有特殊的关系。男子代表全家,妻子只与卧室有关联。
将妻子称为“内人”,这个“内”同样是指内闱里的那个人。这是一种贬低人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个称谓使妻子变成“内”,成为一个私人的世界,而这个私人的世界是由男子支配的。这个称谓还强调了男女关系中的内外之别,非常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夫妻关系中非常明显的特征。这里的男、女、内、外有相互补充、共处之意,也就是通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应该终日留在内闱之中,不要擅自进入男子的领域。但相反的是,男子很少被告知不要介入妻子的事,这也显示了夫妻关系中的不对等。
两性的严格区分即使是在夫妻关系中也不得松懈。上层家庭的妻子如果对丈夫的活动感兴趣,只能躲在屏风后面听丈夫与客人谈话,绝对不允许加入其中。
恪守规则的妻子往往备受赞誉,甚至大书特书。宋朝时的一位妻子,陪着当官的丈夫和儿子住过许多地方,但无论是西湖还是“南阳百花洲,金陵小金山”,她从未想过去看一看,这样的行为便受到了赞赏。
在中国旧式的家庭中,绝大多数婚姻都是由父母安排的,两个年轻人在举行婚礼前互相不认识,所以新婚夫妇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调适才能慢慢适应。年轻的丈夫不能过多地提起妻子,也不能在家庭聚会中赞扬妻子。
同样,年轻妻子也要避免表现出对丈夫的爱。贤惠的妻子白天与婆婆或小姑子一起干活,晚上必须等到所有家庭成员都休息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间与丈夫待在一起。妻子在提到丈夫的时候,通常不用他的名字或者“我的丈夫”,而是用代词“他”;如果丈夫外出回家,妻子也不能当面向他问好,而是根据婆婆的指示,为丈夫准备热水和茶饭。
在中国传统社会,夫妻关系还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例如近亲联姻。中国外婚制原则虽然禁止同姓堂兄妹结婚,但并不禁止与姑姑、舅舅和姨母这类亲戚的子女结婚。即使在现代,这类婚姻也还存在。
《红楼梦》中也多次出现近亲联姻,例如王熙凤嫁到贾家之前,王夫人是她的姑姑,在她嫁入贾家之后,王夫人既是她的姑姑,也是她的婶娘,二人既有婆家的亲属关系,也有娘家的亲属关系。
更近的血缘关系联姻体现在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上,两人的母亲是亲姊妹,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之后,薛宝钗和王夫人便是媳妇和婆婆的关系,算是亲上加亲了。假如贾宝玉与林黛玉成亲,贾宝玉的父亲与林黛玉的母亲也是亲兄妹,这也是近亲联姻的体现。
那近亲之间的联姻是谁提出来的呢?
在《红楼梦》的两则例子中,毫无疑问是王夫人的主意,王夫人让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夫家的侄子,又让自己妹妹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为什么她会这样选择呢?
通常女人喜欢近亲之间的通婚,是因为女人会由于进入陌生家门而焦虑,无论是妯娌、儿媳、侄媳,女性之间的亲属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来自娘家或者与自己家庭有关的人家的女子总是比陌生女子要好相处的。同样,以新娘母亲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女儿即将嫁过去的人家有自己熟悉的女性亲属,便会对女儿日后的处境更放心一些。
“上门女婿”也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夫妻关系。当一个男人成为上门女婿时,夫妻关系也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模式了。
“上门女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入赘。大部分家庭招上门女婿,是因为家中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又不愿意过继养子。这种婚姻对于男人而言是丢面子的事,然而许多男人“不得不”去做上门女婿,是由于家境贫寒。
随夫的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逐渐适应转变的过程,所以“上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也是一个要逐渐转变适应的过程。在入赘这样的婚姻关系中,“上门女婿”的地位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媳妇”地位相同。夫妻关系似乎不是家庭主要的“矛盾”所在,丈夫没有了夫权,完全受制于岳母。通常情况下,岳母会嫌弃女婿是“没有本事的,吃闲饭的”,二人相互猜忌、滋生不满,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
“举案齐眉”是中国传统夫妻关系的理想模式,虽然这个成语表示的是夫妻之间相互的敬重,但把托盘举到与眉毛齐高的却是妻子,享用托盘中饭菜的是丈夫,这样的理想关系也暗含着夫妻之间的不对等。
那应该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呢?
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有一部分专门记录了他与妻子芸娘的“闺房之乐”。沈复打破内外有别的男女关系,让芸娘女扮男装与他一起逛庙会,夫妻之间情感融洽。
但在一夫多妻制的传统社会,即使是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史中最可爱的女人”的芸娘,也无法避免与其他女人分享一个丈夫的命运。作为妻子,大度的美德让她专门留心为丈夫选择合适的侍妾。这些矛盾和复杂因素,或许能阐释传统中国家庭夫妻关系的一些特征。
从夫妻关系中“妻从于夫”的特征,以及近亲联姻和“上门女婿”两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可见传统中国家庭中夫妻关系的构成形式是比较复杂的。

兄弟:人格与行为
所谓“兄弟如手足”,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兄弟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兄弟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但并不从属于父子关系。人们认为“兄弟本是同根生”,所以理想的兄弟关系是互相帮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长兄为父”,长兄需要负担幼弟的抚育之责。
那兄弟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征呢?在儿童时期,兄弟是玩伴,地位差不多是平等的。虽然他们会打架,但并不会影响相互的情感。
在慢慢学习儒家礼仪之后,兄弟关系便脱离了最“天真、自然”的状态,有了一定的约束。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表达了兄弟之间的谦让和融洽。“兄友弟恭”,就是说哥哥要对弟弟友爱,而弟弟则要尊敬哥哥。
总的来说,兄弟在结婚之前,大部分时间的相处还是融洽的。对于他们来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在父亲的指挥和带领下,虽然他们偶尔有冲突和竞争,但还是保持着合作、互助的良性关系。
兄弟关系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他们各自结婚之后。
当一个原生家庭分裂成多个新的小家庭之后,矛盾也会随之而来,如妯娌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兄弟关系。妯娌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下一代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促使兄弟关系走向恶化。如果父母不能充当公平的仲裁者或者调解者,家庭很可能会破裂。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耳熟能详的周氏兄弟,周树人(即鲁迅)与周作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两人在青年时期,在文学方面相互影响和鼓励,“弃医从文”的鲁迅也非常鼓励弟弟周作人从事文学事业,到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两兄弟又一起翻译日文或西方文艺作品,同吃同住同学的两兄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1917年,兄弟二人到北平,当时正流行传染病猩红热,周作人突然发起高烧。这急坏了鲁迅,他四处借钱、延医买药,后来找到一位德国医师,才发现周作人不过是出疹子,而不是被传染猩红热,他才放松下来。
1919年,鲁迅在北平西三条胡同购买了房屋,把母亲连同两个弟弟及其家眷接来同住。当时,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子女,他很喜欢侄儿们,视如己出。
兄弟二人的不合正是在这同住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此事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有很大关系。在兄弟二人不合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周作人的妻子告诉丈夫,鲁迅对其有“非礼”的举动,而周作人听信了妻子的话,于是兄弟之间的不合便越来越严重。
此后,鲁迅搬出了这个大家庭。两人共同的朋友许寿裳说,自此之后,两人不合,一改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以至于鲁迅想取回原来家中的藏书都被周作人拒绝。
兄弟虽然出于一对父母,但实则也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家产的争夺上,兄弟分家对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传统中国的农村,流传着许多劝谏兄弟不要相争的诗:“九世同居张公艺,子孙世代家不分;同胞手足须和妻,相帮相处能起来;不要三心共两意,莫听妇人背后言……打虎必须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
但这些劝谏诗的流传也从侧面反映出,兄弟相争的现象很多。例如大多数人熟知的历史史实,三国时期的曹植所做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足见手足相残的历史之悠久。
另一个著名的兄弟相争的案例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明争暗斗,在唐高宗李渊的偏袒之下,太子占上风,李世民搏命一击,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以及支持太子的四弟齐王李元吉。
大家很熟悉的是清朝时期的“九龙夺嫡”大戏,为了至上的皇权帝位,兄弟死的死,囚禁的囚禁,即使是最终坐上龙椅的雍正也在后世的不断揣测下,无法为自己正名。而今天如此多的清宫剧选择该事件以及人物,也正是因为有各种“戏说”和“想象”的空间。
除了与生死相关的权力争夺,普通人家的兄弟之间的竞争也无处不在。在传统中国的农村地区,财产按照均分的原则,分给每一个儿子。一般情况下,在最小的儿子结婚之后,或者在父亲去世之后,才有分家的可能。
父母为每个儿子准备同等份的家产,从现金、土地到房屋,很多时候父母本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会对他们寄予养老希望的儿子格外“优厚”一些,这样做其他儿子知道之后会觉得不公平,不仅伤害了父子之情,也伤害了兄弟之情。
当然,“手足情深”也是可以延续一生的。
不是所有的兄弟关系都像上面所列举的那样,夏济安和夏志清两兄弟便是最好的例子。在1947年到1965年间,兄弟二人通信600多封。在已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动荡背景之下,夏志清在耶鲁读书,直到博士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大学当老师,夏济安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再到香港、台北,命运的颠簸在信中一览无余。两兄弟虽然分别漂流在外,与父母分离几十年,但是靠着单薄的信纸,相互鼓励、相互支撑。
在往来的通信中,他们谈文学、谈理想、谈政局,也非常“接地气”地聊电影、歌剧、明星,夏志清恋爱结婚生子,夏济安一次又一次向弟弟诉说对婚姻的恐惧。很难想象,在半个世纪之前,没有现代先进的通信设备,在半个月一次的航空信件中,兄弟之间没有丝毫的距离感。
虽然夏济安是哥哥,但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水平远低于美国,夏志清理解哥哥的清贫,于是从读博士开始,每个月给家里面汇款100美元,那是他奖学金的三分之一,而且几十年从未中断过。他们彼此从未清晰地划分对父母的养老责任,是兄弟之间的体恤和相互帮助,才使得一个家庭在动荡的年代依旧顽强地“存活”下来。
总之,“手足相残”和“手足情深”是兄弟关系的不同面向,也展现了传统中国家庭中兄弟关系的复杂性。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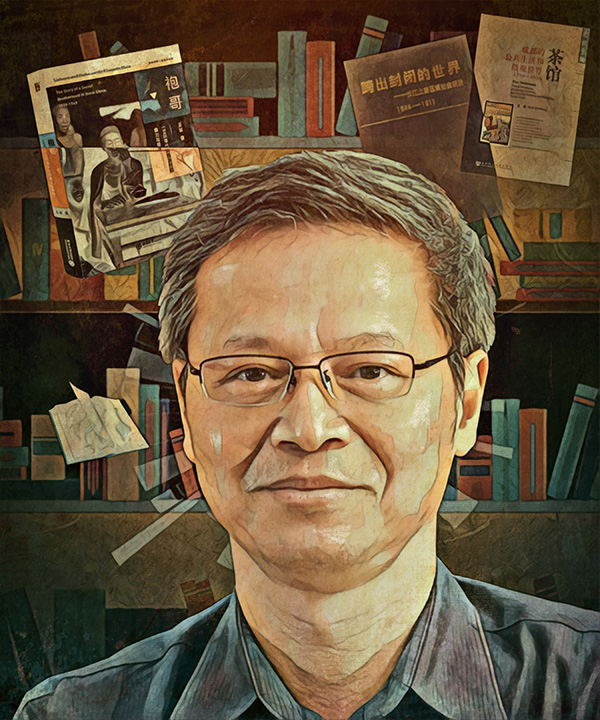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