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东西
一谈起“封建”这个词来,“吃人的东西”,估计许多人脑海里就会蹦出这五个字来。
很多人会把封建和周树人联系起来。在中国,封建这个词是在近现代的时候才流行开来的。那时候的鲁迅,其笔锋利无比,怒斥军阀列强,痛批旧思想旧文化,把赤裸裸的血腥现实排列成一串串文字,让人不寒而栗。
“吃人的人”,这样露骨的言辞,最早出现在《狂人日记》一文中。

有意思的是,里面不止刻画了那些“吃人的人”,还有一条狗,赵家的狗,穿插在全文。“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故事由此开始。“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在这种弥漫着“吃人”的压抑着的社会氛围里,“我”的精神高度集中,有些草木皆兵的意味了。“‘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从基因上揭示狗改不了吃肉的本质,“我”惶惶不安,预感他们就要下手了,害怕又虚弱。
这就是文中几次对“赵家的狗”的描述了,实则上,狗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着主人家的各种状态的。写狗的同时,实际上也是描写那些“吃人的东西”,称他们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暗示这些被旧思想旧道德支配着的人:胆怯弱小、无情冷漠、狡黠利己。
在文中,“我”期望能唤醒这些“吃人的东西”,但在整个旧礼教的大环境内,“我”孤立无援,只是无言无力地挣扎着,甚至有时还与他们同流合污,不得不说,这无比令人叹息扼腕。
所以,许多人认为这篇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鲁迅先生也成为打倒封建主义的卫士。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黑锅,鲁迅先生可背不起来。
鲁迅:我从未说过封建它什么坏话,或许有吧,但决然没有叫过封建这两个字。
在那个学术论战的年代里,封建是一个高频词汇。但鲁迅先生经常克制自己,不去淌这浑水。事实上,鲁迅先生从未使用过封建这一词汇,他反对的是旧伦理旧道德旧礼制,这些也就是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封建主义”的泛论。
鲁迅先生虽认为这么定义封建不大妥当,但对于这些从来不去辩驳什么,也不表态,他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说的太多,既无道理又自找不痛快,就留下“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字眼供后人解读。这才是我们熟知的鲁迅,有理,在对手心窝子上倒插钢刀;无理,人间虽半步也难行走。所以,毛泽东同志这么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狂人日记》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文中多次出现了与历史有关的字眼,“四千年”、“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等等,与那“狼是狗的本家”一样:吃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四千年的浩浩汤汤,到底还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不仅是“我”,也不仅仅是作者,都有此疑惑: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都知道的结果,也都在努力避免,可最终还是一样的结局。真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吗?还是“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是人类不会汲取教训”才真正是真理?如果还不能找到答案,只怕是牛顿力学镇压下的天帝就要出来狠狠地嘲笑我们了。
封建的前世今生
封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了。古今中外,都不能与它分离。如今,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学术思潮,封建本义和泛封建主义论(为简便,后文统称为泛论)。
本义
封建本义,顾名思义,是封建的本来释意。
本义,指殷周分封制度,是区分社会历史形态的一种政治制度,类似于政体。最初,封和建是分开使用的。封建合用的最早记录是在《诗经》中,有“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为记。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简单来说,封就是给予领地食邑和爵位名号;建也有给予土地的意思,起搭配作用。封和建组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封邦建国”,领主拥有领土的所有权和治理权,这与西欧中世纪的采邑领主制有些类似。西周当时还有一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有大宗小宗之分,大宗继承土地和爵号,小宗则继续分封。这样的层层分封,在加上西周内部的等级制,由分封确立等级,又由等级巩固分封,西周成为一个等级观念渗透整个社会的以宗法制为宗旨的宗法制封建国家。
夏商周都是封建国家,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夏商是氏族封建制,而周是宗法封建制。总的说来,封建本义是“封邦建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主要还是以政治制度层面呈现的。
泛论
泛论的开始,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近代以来,“feudalism”这个洋词传入中国。当时的学者把封建作为它的中译,这还是很准确的。“feudalism”一词是用来描述西欧中世纪制度的,含义为封土封城、采邑领主制。这些与封建本义是十分契合的。
世界近代以来,随着各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不断被发掘和融合,世界学者发现在各国发展的历史中,基本上有着一个类似的运动轨迹。他们把这些国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的一致称为普世性,这是历史分期的开始。

社会历史分期是导致泛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社会历史分期中,泛论曾经有两次被提出,一次是在五四运动,一次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
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曾经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而就是这么戏剧性的一幕才导致了现在许多的历史性遗留问题。
在历史分期后,泛论开始成为代表着那些落后和腐朽思想的代名词,“反封建”这才能成为新文化中的旗帜。
本义和泛论的论战:社会历史形态之争
前文说了,泛论曾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候,主要是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封建本是我国古史概念,现在却是由留学生从海外重新学得,再传入中国,再重新解释,这样就产生了些混乱,当然具体是如何产生并且程度深浅这些都不易考究了。总之,封建就成为了“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所对立的腐朽的、落后的制度和思想的代名词。
其中,有一个值得推敲的新名词“前近代”,这就要从那戏剧性的一幕说起。我国的封建制是在夏商周时代,结束于秦帝国时期,即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全国推行郡县制(秦帝国建立前便有了郡县制)。从此,像夏商周这样名至实归的封建制就不再有了。
再来看看国外的封建制度。西欧: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终于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日本:发源于8到12世纪平安时代的律令制,在12到19世纪武家政权时代成为主流体制,止于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这样看来,西欧和日本封建制的开始距离中国封建制结束,西欧隔了有将近七个世纪;日本更是长达千年之久。
根据马克思的五种历史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前近代”说犹如无水之萍,站不住脚。“前近代”的说法,是因为中国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缘由(只有资本主义萌芽),用以代名秦至民国这一时期。而实际上,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前近代”就是封建社会。而在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反封建斗争中,封建势力是无比强大、腐朽和血腥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样“前近代”一词也继承了各国对封建时代的记忆,再由于明清以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盲目闭关锁国等政策的高压下,往日的帝国变得落后、腐朽、腐败,这些落后的思想和制度成为泛论的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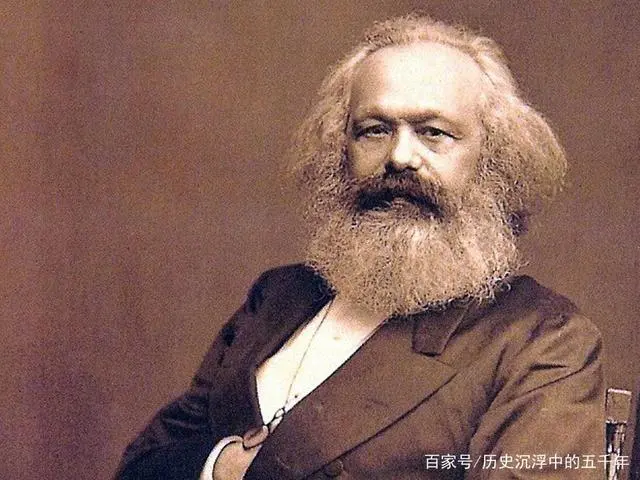
中国以外的国家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前近代”时期定义为封建,代表着落后与腐朽,与近代文明相对立。中国某些学者便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把秦至民国以来冠以封建之名。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并未完全接受这种泛论,陈独秀先生也逐渐发现这种说法存在有漏洞,后来也少有谈论封建一说。虽然在第一次泛论之争中,泛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其“封建××”格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次泛论之争起源于共产国际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定义。1912年,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中国近代是封建主义,又说是半封建国家。后来,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思想,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随着星火燎原之势,这些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者接受,泛论成为定势,自此沿用不辍。
1927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开始。中共二大指出中国当时是“半封建的独立国家”;同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一文中,把“反帝”和“反封建”确立为中国革命的任务。然而,陈独秀等人判断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反对近代封建说,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双方的争论,使论争从党内延及党外,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展开。
接下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导引出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如何理解"封建",以及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认定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重要议题之一。实际上,就是如何统一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分期的问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中,提出了不少的新颖观点,但没有一种学说能够使大家心服口服,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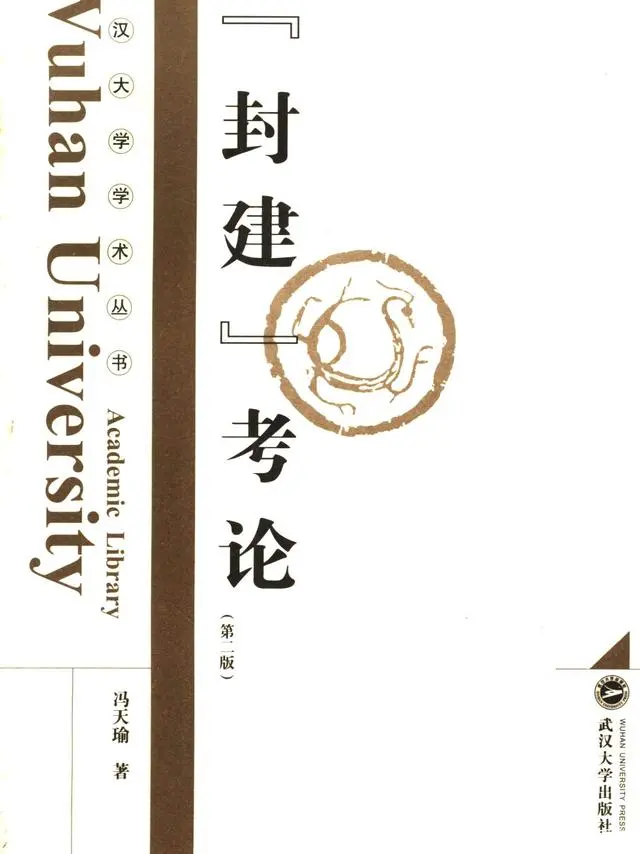
总之,夏商周封建说是有理有据的,但封建本义却一直被人淡忘。而自秦至民国的社会形态,世界上也有许多种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君主专制”、“霸朝”等各种说法(关于社会历史形态分期就不过细谈论了,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以及相关的资料)。
再谈封建
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帝王、封建皇权、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糟粕、封建迷信、封建脑筋、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
说起封建,或许许多人没有感受。以上这些“封建××”式短语就是我们最为深刻的记忆了,封建一词俨然成为了日常口语,尤其是年轻人在与老一辈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些短语前缀的封建一词去掉,“地主、帝王、官僚、迷信、包办婚姻...”,再把这些全以贬义标签贴入,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意思无二。
封建本义是“封邦建国”,封建制之后是郡县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取代了宗法分封的封建主义,官僚政治制度取代了氏族血缘制度。鸦片战争后,留学生从日本带回封建新义。作为古词的封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义,泛论首次出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近代仍为封建社会,半封建观从党内到党外被广泛接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泛论被普遍使用于教育活动等日常生活中,但纠正这一错误的斗争从未停止,有识之士皆在努力。
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不一样的,各国的实际也是有差别的。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西欧的历史演变路线,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致的。他认为自秦到民国这段历史,是东方特有的专制制度。
当然,在这里不是批驳那些导致泛论产生的人和时代,而是要从根源处解决问题。泛论能够产生并流行开来,是有它的理由的,有它能够产生的时代实际的,这是大势。泄洪也是一般的道理,总是堵着,那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所以需要一道适逢其会的口子,反而能挨过去。但洪水过了,不能作壁上观,该疏浚河道的疏浚河道,该开辟新河道的就去开辟新河道,反正,总不能什么都不去干吧。

正名,总该是要的吧。《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用本义,则有新义在那,要紧跟世界学术潮流,只有思想封建的人才这样用封建,反对的人会这么说;要是用泛论,又有古义在那,崇洋媚外、这样总是不妥,其反对者又这么说;要不这样吧,第三人弱弱地说,出去,岂有此理,本义和泛论罕见同声。
把别人家的,当作自己家的,这或许是正名不下去的缘由了。把西方那一套不加思索地安装在中国声上,那哪行,也不可能行。事实上,任何像马克思那样客观,不带有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利益的学者,都不大赞同泛论这样的学说。
这样看来,一些学术论战,也不是很纯粹,还是有立场的,也可以接受,但绝不能容忍迟迟不去解决。那些所谓的历史悲剧,其实都是人民的悲剧。但凡上过点学的,都知道,是人民缔造了历史,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朝代更替,人民颠沛流离;盛世繁荣,也没多捡得些好处。
解决这些的本来还是在于学问二字。
那些精英们,那些学者们,但凡做过些许研究的,都会了解些。其实,大众舆论,一直是由少数人掌控的,他们隐瞒欺骗引导,不知道将人民当作什么。
学问,学的是古往今来,学的是上下四方;问的是针砭时弊,问的是民间疾苦。借用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的墓志铭,做学问也是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近代以来,民智未开,腐朽、落后,实则是国人学问太浅,思想僵化。一国之民,如一屋之柱梁,今柱梁尽朽,大厦安好?这是朽到骨子里了,从内而外,自下而上,非有一剂猛药不得始终。泛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猛药,然则时过境迁,时代的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这剂猛药该还原了。
人民都会做学问了,将会对他们依赖得少些,也将会是一次由人民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对于知识等垄断的洗牌。或许只有人民才能最终解决这些历史性问题,而不是只存在于“历史是由人民缔造”中的“历史”字眼而已。
邵阳县志:我是一本不一样的乡土志
致敬英雄:白衣作客不见卿,常使人民泪满襟
礼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