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婴儿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提高。老年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养老相关的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对社会结构有很多影响,包括对家庭、健康和社会服务、长期照料、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政治历程、休闲服务、住房等的影响(N.R.霍曼、H.A.基亚克,1988),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
1、家庭结构变化
城乡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来看,三代家庭户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且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比例倾向于不断提高(杜鹏,1999)。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三代家庭户有所增加,而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则下降较多(曾毅、王正联,2004)。对比2000年及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代际结构的简单化。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10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1.78亿人,全国有1.2亿个家庭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家庭户的30.6%,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家庭人口构成的新格局。特别是,在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中,32.6%的家庭只有一个老年人和一对老年夫妇(张丽萍,2012)。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化给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模式带来挑战。
2、居住方式变化
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对代际关系、照料方式都会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中国城市老年人愿意让已婚的子女单独住,只有当老年人不能自理时,他们才住到一起(Davis-Friedmann,1991)。从居住方式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住房条件的改善,与以往传统大家庭居住形式不同,目前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已经呈现多样化特征,老年人口与子女不同住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不断缩小。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比例在城市有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张丽萍,2012)。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变动是以子女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尽管农村社会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劳动力外流使传统观念逐渐淡薄,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与子女不同住,从而使老人独居比例增高(王萍、李树茁,2007)。
3、家庭关系变化
养老抚幼作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是承担养老责任的场所,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是一种“反哺模式”(费孝通,1983),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日益提高,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导致越来越多的“四二一”家庭出现,给家庭养老带来极大的挑战。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父母威权的衰落,具体表现在父母控制子女的能力大大降低,但在孝道伦理仍旧获得道德上的认可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中,正是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在家庭生活中的合作与协调,使得家庭养老制度得以维持(陈皆明,1998)。通过抚养期的亲代抚养、独立期亲子间的双向即时交换、赡养期的子代赡养,独立期亲代与子代的代际交换所构筑的代际关系,取代了抚养期亲代所投入的经济资源,成为当前影响子代赡养行为的关键因素;同时,经济资源对赡养行为的约束作用与日俱增,而社会规范资源对赡养行为的影响力正日渐减小,法律资源对子代赡养行为的约束作用则微乎其微(余梅玲,2015)。
二、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
1、照料负担加重
老人健康状况与养老负担密切相关,从宏观上来看,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总量为576.49万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2.60%,预计2050年中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将超过1450万人,是2015年的2.5倍以上(王广州,2019)。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家庭养老责任由子女分担或共担,但随着生育水平下降,亲生子女人数减少,老人照料资源也随之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从照料时间看,顾大男等人(2007)研究发现,65岁以上(但非纯高龄)的老人临终前平均需要他人完全照料的天数为82天;对山东老年人口的调查也发现,农村老人在去世前平均临终卧床时间超过半年,80岁以上老人年人均卧床时间超过一个半月(王广州、张丽萍,2012),由此可见,随着家庭亲子结构的变化和男女人均预期寿命的差距,照料资源不足是家庭养老必须面临的严峻考验。周云等(2014)指出,代际的年龄差距小,两代人同时进入老年的可能性增大,则会出现银发人照顾银发人的现象。吴帆(2016)认为,政府应该大力开发50~64岁人口乃至65~69岁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他们不仅是家庭中照料老年人的主力,也可以成为老年人社会照料供给的重要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老年人既是养老照料的主要对象,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也是养老照料的主要提供者。鼓励他们为老年人的社会正式照料提供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
从家庭照料者来看,健在的老伴在照顾配偶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王来华、约瑟夫·施耐德,2000),有无配偶不仅影响到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料分担(庄绪荣、张丽萍,2016)。除配偶外,子女在生活照料上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当代中国家庭,女儿开始和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责任,甚至比儿子更加孝敬父母(Xie & Zhu,2009;唐灿等,2009)。从城乡家庭养老的照料方式来看,“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已超过儿子(许琪,2015)。
2、经济压力大
经济收入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依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市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比例最高的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乡村老年人以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收入主要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子女给的生活费等为主,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高龄老人没有离退休金,只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及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能领到的养老保险金(赵欢、韩俊莉,2012),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劳动收入比例降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比例提高。在80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有37.2%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给,而在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67.6%依靠其他家庭成员供给(张丽萍,2012)。在中国特殊的传统与现代、发达与不发达、城市与乡村等社会经济差距巨大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迁移模式使得大多数老年人口留守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资源分配、家庭养老的模式和能力发生变化,同时老年人缺少有效的财富积累(李萌、陆蒙华、张力,2019);随着经济增长和扶贫减贫措施的不断完善,老年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老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李实,2019)。特别是从医疗支出来看,有研究发现,个人医疗费用的高峰集中于死亡前一段时间(李大正、杨静利、王德睦,2011),对于老年供养者而言,高龄父母没有退休金或者只有很少退休金,加上高龄父母需要巨大的医药费支出,导致供养者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陈亮,2015)。
3、家庭养老责任边界模糊
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体系下,养老的责任由家庭承担,但随着国家介入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责任边界问题也随之出现。将老人纳入养老保障范围后,国家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目前已经为老人提供了基本支持,减轻了家庭负担,家庭就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照料和赡养责任;子女则认为既然国家对老人有了基本的制度安排,那么家庭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就可减轻,这成为部分农村家庭不赡养老人的借口(钟曼丽、杨宝强,2019)。国家在“老有所养”的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超越国家能力替代家庭养老则是十分危险的(陈军亚,2018)。所以,在家庭养老中,家国责任边界的划分是十分必要的。
三、家庭养老的社会支持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养老模式却受到了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剧烈冲击,家庭养老资源不足以及家庭照料负担加重,而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和社会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仍显不足(袁小波,2017),所以,对家庭养老需要从不同方面加以支持。
1、完善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社区环境
随着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下降,应在居住环境上为养老提供便利条件,老年人居住的社区与普通社区也要有所区别,李斌(2010)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老人居住的社区针对老人的服务和设施相当欠缺,尤其针对残疾老人的设施更是奇缺;同时,老年人在居住上获得包括单位在内的机构的帮助很少,他们大多处于无助状态;如果老年人居住在设施齐全、各类服务容易获得的社区中,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就会增强。需要构建老年居住社区,打造老年居住模式,并在普通社区的基础上增加社区养老的一系列设施和服务(王明川,2007)。
2、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随着生活自理水平的下降,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多。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来看,居家养老或家庭照料仍然是中国老年人所期待的最佳的养老方式,但随着家庭规模缩小,现有的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使得家庭承担老年人照料的功能逐渐减弱。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照料观念的影响,大多数老年人不能接受社会养老或机构照料(王晶、张立龙,2015),需要必要的居家养老服务,部分城市在照护服务网络上,已经形成以社区助老服务社、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等为服务实体,以上门照护、日间照护、助餐服务为主要形式,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模式(房莉杰,2014)。
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对上门看病、陪同看病、上门护理和康复治疗等与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相关的养老服务需求的比例越高(王琼,2016)。从国际相关研究来看,王晶等(2015)分析美国的PACE项目、日本的介护保险、瑞典的居家老龄服务,发现这些服务项目全面考察老年人的需求,是以社区为主要依托,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一体化的养老、医疗、护理等服务,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老年护理师、老年营养师等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是有序运作老龄服务项目、有效满足老年人需求、提升老龄服务质量的关键。
新技术在养老中的应用也随之被提出,史云桐指出,通过网络化居家养老,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既有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建立起一张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并整合全社会为老服务资源的养老网络,使老年人在家中就能尽享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便利,通过统一的为老服务平台,使老年人“巢”空而心不空(史云桐,2012)。
3、支持家庭照料者
随着老人健康水平的下降,家庭照料负担逐渐加重,在相当长时间内养老责任主要是由家庭承担,以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亲属等提供非正式照料为主要的照料方式(陈蓉、胡琪,2015)。被照料老人绝大部分是高龄老人,失能、失智的比例高,照料负担重,照料时间长,对家庭照顾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陈蓉,2017),所以,需要为家庭照料者提供支持,在家庭内部提供的支持包括主妇服务、送饭服务、暂托服务;在家庭外部提供的支持包括成人日间照顾、交通服务、家庭外暂托服务、辅导和支持小组(陈树强,2002),以及照料技能培训、心理支持、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陈蓉,2017)。
4、机构养老
家庭养老所需的社会支持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选择机构养老也逐渐成为部分老年人的愿望。城市老人由于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原因选择入住养老机构(风笑天等,2014)。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广义的老年人群体,但实际服务对象的主体是靠自己或家人在家庭中难以获得照料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吴玉韶等,2015),但当前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也制约着其发展,各类养老机构倾向于对健康、相对年轻的老人提供服务,而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服务提供不足(王延中、龙玉其,2018)。同时养老机构资源严重不足,养老机构设备设施大多比较简陋,服务档次总体来看还比较低,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素质总体也较低(李岳,2018)。从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国际养老机构发展趋势来看,“就地养老”是大势所趋,未来养老机构小型化、专业化、社区化、连锁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机构养老服务将与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吴玉韶等,2015)。
总而言之,家庭养老问题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加剧,中国家庭养老问题研究主要围绕谁来养、怎么养、在哪养、什么时候养进行。国家老龄战略“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设计,无论是“9064”还是“9073”的养老格局,都是定位居家养老,以实现家庭养老功能,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在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框架下的养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涉及钱从哪里来、照料的人从哪里来等突出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针对需要养老照料的刚需群体,对养老资源进行不同的配置,解决全社会养老能力和养老资源问题。借助人工智能科技辅助手段突破以往的养老和社会支持的思路和框架,提高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彻底解决千百年来困扰中国家庭的养老负担问题,是今后不断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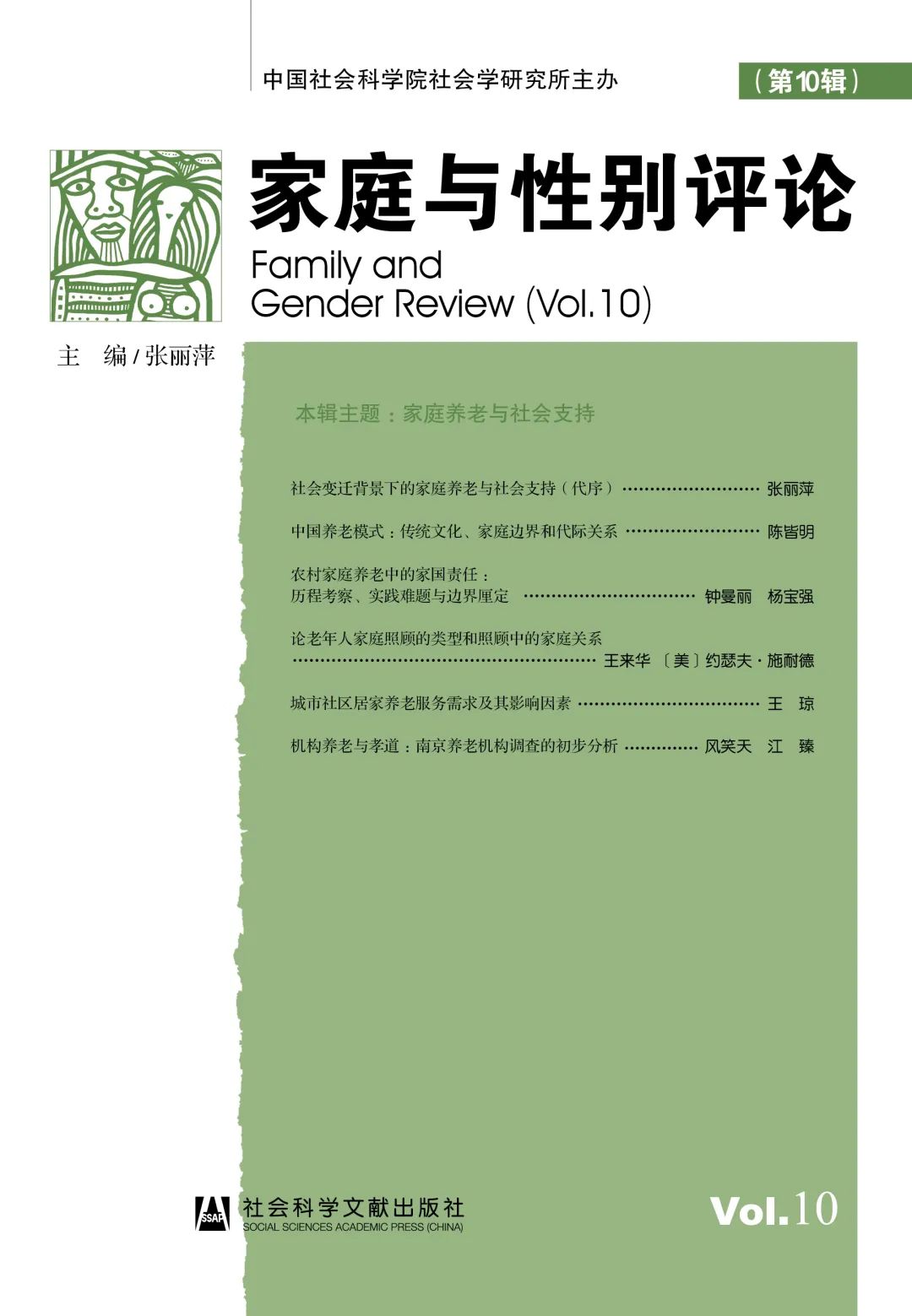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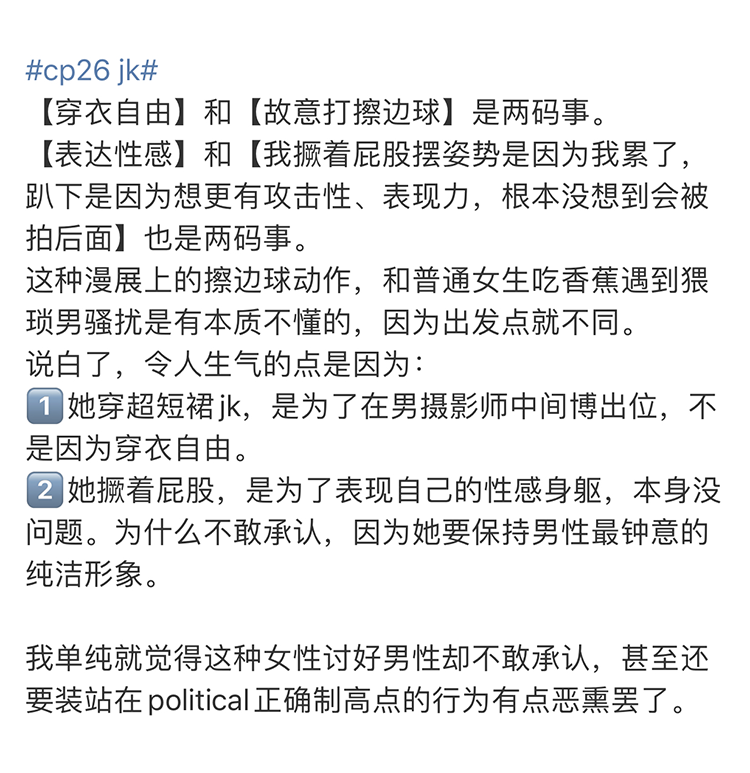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