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少时读书,还有个传说。据说,李白家住在阴平古道旁,商旅不绝,人声喧杂,父亲为了让他静心读书,将他送往离家十多里的小国山上。人山以后,李白不仅白天读书,夜晚也要点灯苦学。每到夜晚,人们都能望见山上的灯光。因此,当地人又将小国山称作“点灯山”。
无论故事真假,李白的刻苦是真实的,他在国山修业读书也是真实的。江油市有小匡山和大匡山。小国山位于四川江油让水乡境内距江油城区
二十华里,在让水乡读书台村,青莲镇至国山的古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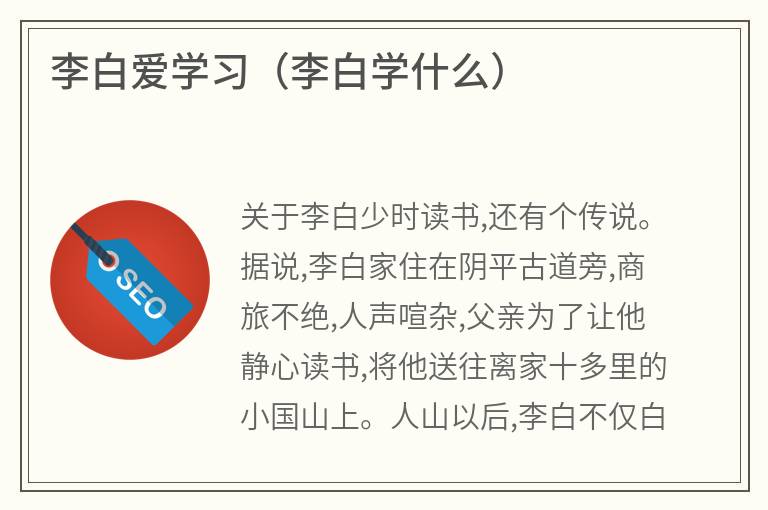
李白爱学习(李白学什么)
大匡山位于江油市大康镇西北,其山势如筐,谐音匡山,距市区二十公里。山势险峻,林壑深邃,风景秀丽,背倚龙门山余脉诸峰,下临清澈明净的让水河,西有天然溶洞佛爷洞景区相邻。
大匡山于唐代就有寺庙。《江油县志》载:“国山寺,唐贞观中,僧法云开堂于此,僖宗幸蜀,敕赐中和寺,寺右有李白祠。”宋乾道六年(1170)匡山碑文记载:“本寺原是古迹,唐李白读书所在。”杜甫入蜀到江油曾吟诗云:“国山读书处,白头好归来”。
李白天生聪颖,李客心里欢喜,对他悉心培养。十岁时,李白开始阅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典籍,初步了解华夏历史文化,广泛汲取百家的思想养料。他喜欢将自己放逐在书籍中,流连忘返。自然地,他喜欢上了写诗。
对他来说,诗是现实之外的别有洞天。有了诗,便有了看不尽的水净山明。
与诗结缘,终生不悔。可以说,诗给了他重桫宫阙,而他让诗一醉干馆诗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若是没有李白的名学,必是莫大的缺失。诗之是细雨斜风,是千里月明,却也不能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他还很小,但想象力已非常丰富。就像那首《夜宿山寺》所写:
危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我始终相信,诗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山高水远,月白风清,愿意与之深情对望,心底亦能刹那花开,这大概便是所谓诗性。而有的人,纵然皓首穷经,也未必能为一朵花开而欢喜,那或许便是与诗无缘的。
这首诗,看似词句浅显,却也颇显才思。多年以后,他仍对此诗念念不忘。在游览舒州峰顶寺时,作为登高观感,将这首诗题写在了墙壁之上,只是为了应景,将首句改为了“夜宿峰顶寺”。宋人周紫芝《太仓梯米集》与《竹坡诗话》、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赵德麟《侯鲭录》都记载了此事。
学习写诗的同时,少时的李白也学习写作辞赋,对司马相如、江淹颇为欣赏。他在《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中写道:“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此赋写楚国之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子虚向乌有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铀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不服,便以齐国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其主要意义是通过这种夸张吉势的描写,表现了大汉王朝的强大声势和雄伟气魄。此赋极铺张扬厉之能事,词藻丰富,描写工丽,散韵相间,标志着汉赋的完全成熟。
那时候,李白时常阅读并且模仿的,是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文选》。萧统死后谥号“昭明”,因此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诗文总集。其内容包括赋、诗、骚、文、表、上书、奏记、史论、碑文、墓志、等数十种类别。《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等书。
江淹的赋也备受李白青睐,在《李太白文集》中,存有《拟恨赋》一篇,虽有模仿江淹《恨赋》的痕迹,却也是他年少时的用心之作。
司马相如说: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年少的李白,尚不知个中滋味。爱情的甜,离别的苦,他都还不清楚。相见的欢喜,相离的悲伤,似乎都只是别人的。他有的,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节。
外面的世界,仿佛与他无关。大唐王朝经历了唐中宗、唐睿宗两代皇帝后,迎来了李隆基,即唐玄宗。李白十三岁的时候,他所处的大唐已属于开元年间。他在日渐成长,大唐王朝亦在日渐强盛。
遗憾的是,华美的开元盛世,留给李白的却是漫长的叹息。他因才情而走入皇宫,却也只是个舞文弄墨的御用文人,未能实现安民济世的理想。即使人们为他的傲世不群添上了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样的典故,他的政治生涯终究是晦暗甚至是苍白的。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只能赋予山河诗酒。
此时,十几岁的李白还在诗海中畅游,遇见文字中的美丽与哀愁。
于他,那都是美的。就好像,世界也在平仄对仗之中,满是诗赋韵味。
但其实,世事的平仄,属于聚散离合;
人间的对仗,属于悲欢苦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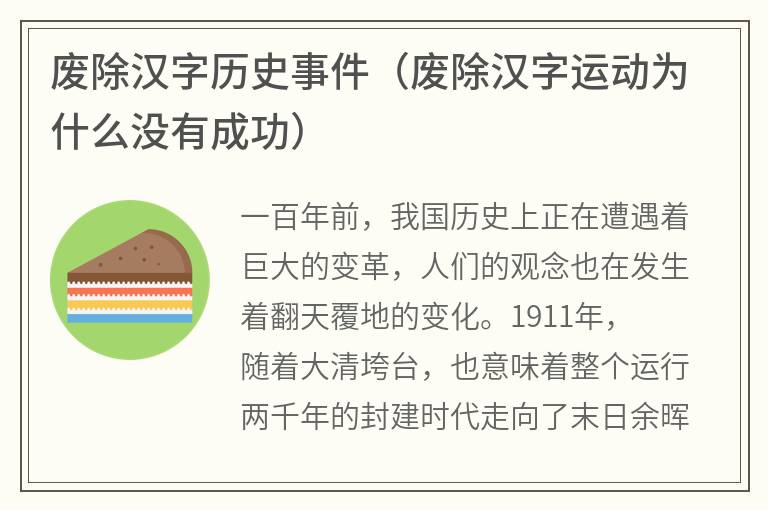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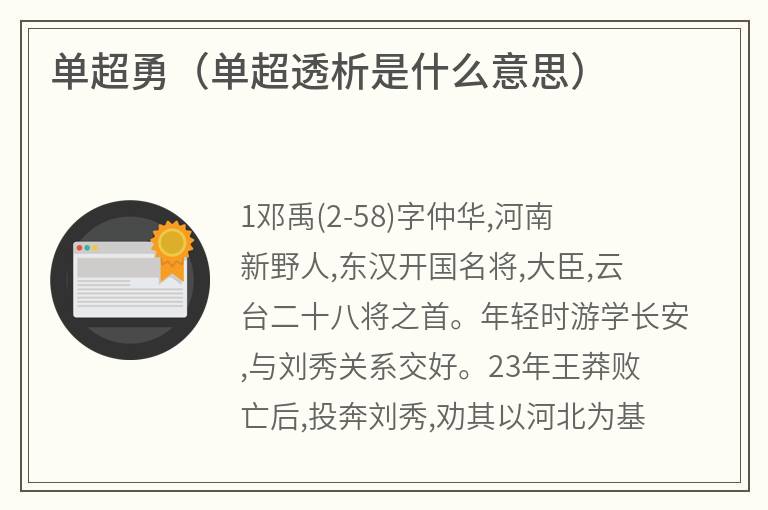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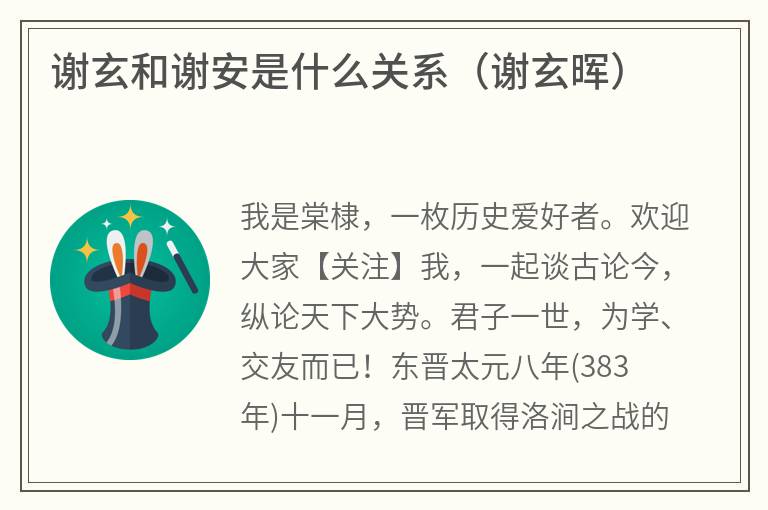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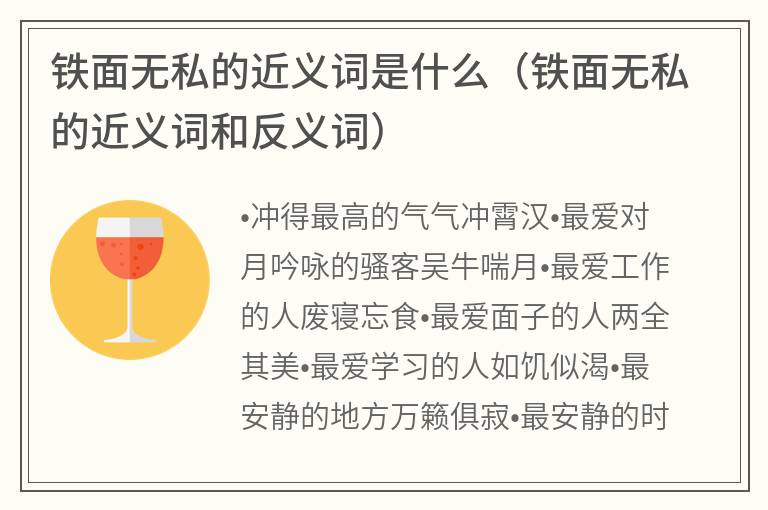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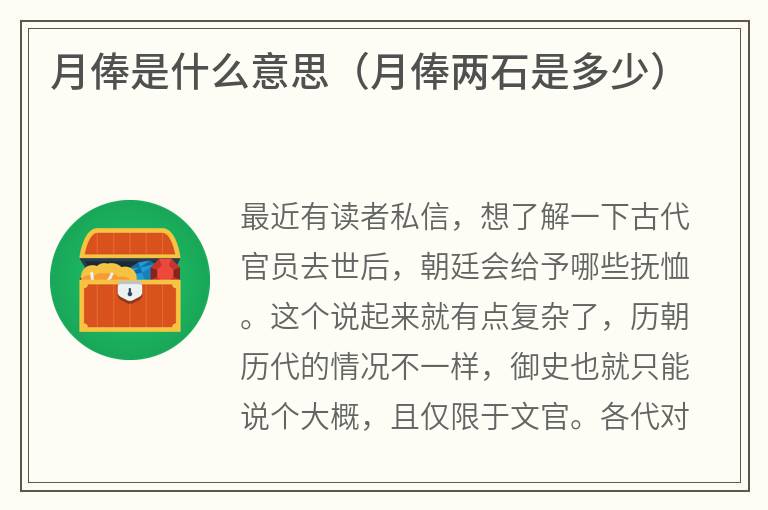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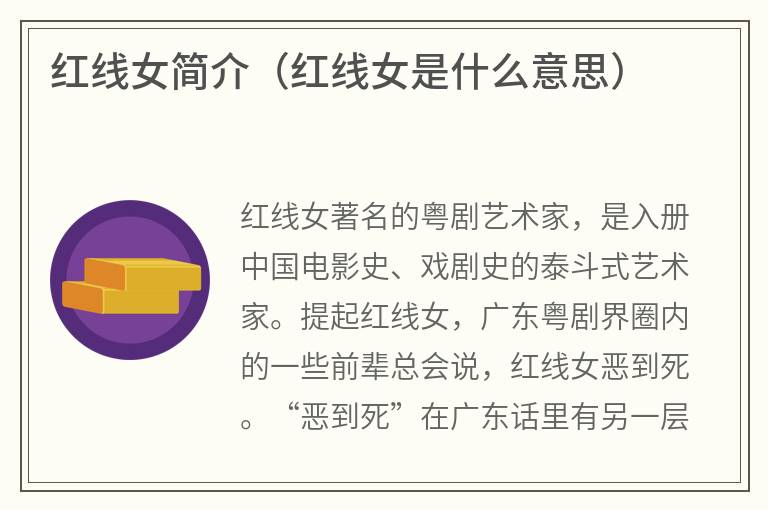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