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展科学与文学被遮蔽的思想空间 | 社会科学报
洞见
现实是科幻文学想象未来的基底,科幻文学就如同在思想实验室里展开的一场实验,向由现实条件和问题构成的溶液里添加各种试剂,化学变化的结果便是现实经验与未来想象共同生成的未来故事。因此,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在时空转换中的变形,我们可以从未来形象中逆推出隐匿其中的现实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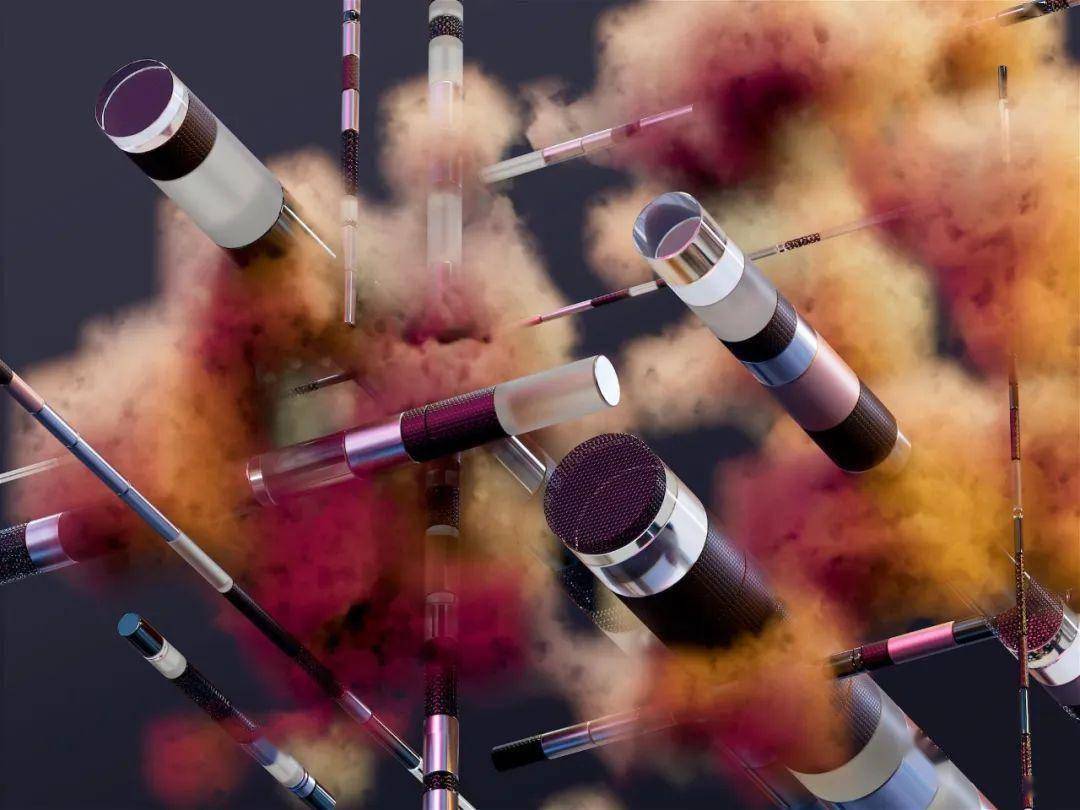
原文 :《延展科学与文学被遮蔽的思想空间》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茜
图片 |网络
《三体》三部曲以史诗般的笔法描写了地球文明初入太空的故事,结构恢宏,内容丰富,其中一个关键线索就是作为宇宙社会学基础的“黑暗丛林法则”。从叶文洁最初发现三体世界,到罗辑、程心的不同选择,地球与三体恩怨交织,再到地球、三体乃至整个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命运沉浮,黑暗丛林法则可以说是推动全部情节展开的核心,人类对黑暗丛林法则的态度也成了令读者争论不休的焦点。
两代执剑人罗辑和程心究竟孰是孰非?罗辑作为领悟“黑暗丛林法则”的第一人与忠实践行者,为人类赢得了威慑纪元的和平,但身处和平生活中的民众为何会抛弃罗辑选择程心?第二代执剑人程心代表人类文化基因中的“善”,她纯洁美好的形象是人类自我认知的理想投射,但也成了将地球文明推向灭亡的直接力量。既然如此,小说为什么又将程心设计为太阳系毁灭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并将延续地球文明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程心身上?最后,程心、智子与她们携带的小小生态球在宇宙中的未来命运并不明朗,作品为地球文明能否以及如何适应如黑暗丛林般的宇宙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局。
客观真理与自由意志之间存在裂痕
其实迄今为止,人类在外太空探索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地外文明的痕迹,黑暗丛林法则也只是文学虚构,所以《三体》的思想价值显然不在于为人类如何实际地应对未来有可能遭遇的地外文明提供行为指南,宇宙伦理学的设计也许另有深意。现实是科幻文学想象未来的基底,科幻文学就如同在思想实验室里展开的一场实验,向由现实条件和问题构成的溶液里添加各种试剂,化学变化的结果便是现实经验与未来想象共同生成的未来故事。
既然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在时空转换中的变形,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未来形象中逆推出隐匿其中的现实意识。围绕“黑暗丛林法则”的分歧,映射着如何理解认知客观世界与自由心灵意志这两者在推动人类行为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康德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看成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两大支柱,纯粹理性意味着认知符合客观物质规律;实践理性意味着人可以不受制于客观物质规律,做出自主行动选择的自由意志,人类的伦理行为主要由实践理性推动。康德又认为,由于宇宙具有终极和目的性,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遵循客观规律与心灵的自由意志,最终能在人类行动中达成协调统一,对真的追求最终也必然是对善的追求。必然与自由、自然与人文、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人类的至高道德境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小说中的叶文洁之所以想让三体人进入地球,便是因为相信有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必然也会拥有昌盛的文化与高级的道德水准,这是非常康德式的想法。
康德的理论里隐含着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对具有终极合目的性的宇宙的信任,一是对人类心灵能够领悟这种合目的性的信任。基于此,他构筑了一幅充满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的宇宙和人类生命图景,相信人类文明将在不断深入的自然认知与不断提升的道德水准的和谐关系中持续前进。而这种诞生于地球文明内部的人本主义哲学思考却在《三体》的宇宙文明视域中遭遇了挑战,挑战同样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颗行星,人类文化信念因此也仅限于在孕育它的地球生态圈范围内有效;第二,从人类有限的文明视野出发,宇宙是否具有终极合目的性不得而知,但可以获得一个毋庸置疑、合乎逻辑的最低基本法,就是各文明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持自身的延续。这样一来,《三体》就打破了康德所设想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得以协调一致的基础,依循客观真理与遵循自由意志两者之间也许存在永远不能弥合的裂痕。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认定为善的行为未必是合规律的,而当我们尊奉自然规律行事时又未必符合人类道德伦理的善,这个矛盾或许最终难以协调。
“黑暗丛林法则”是罗辑根据叶文洁提供的数学模型推演出来的宇宙社会学法则,虽然听起来残酷却符合事实;程心代表人类文明基因中高尚的道德冲动,结果却是将地球文明推向毁灭。《三体》悲剧的根本原因可以概括为代表自由意志的“心”战胜了代表纯粹理性的“逻辑”,如果说内在的“心”与外在的“逻辑”作为影响人类行动选择的两个主要因素本应构成一架天平,那么正是这台天平的失衡导致了地球文明的陨落。

纯粹理性也应为实践理性立限
我们无法确认上述对《三体》未来想象的现实注释是否符合作者的本意。但是,“诚心”之于“逻辑”的膨胀和包覆在中外文明史上都不乏先例。在中国,有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说,宋代理学将“格物致知”联系于“正心诚意”,阳明心学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在欧洲,19世纪末以来以批判科学理性滥觞为主导方向的人文话语也表现出“心”的日渐膨胀,胡塞尔现象学从人的意识活动结构中解释世界的显现方式,海德格尔将世界笼罩于人的存在中,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则将真实归结于物质现象背后的深层话语结构,人文话语不断表现出以主体的意义建构吞噬客观世界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大大提升了现代人的批判意识,一方面也因客观实在地基的不断消融导致了个体化、碎片化、虚无化的后现代生活世界。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思辨实在论、新物质主义之类试图重新树立人类外部物世界的先在性与超越性的逆向努力。
在小说里,人类一开始出于对三体的陌生恐惧而支持罗辑,三体作为有待认知的绝对他者,充当着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制衡力量。但是随着接触不断增加,人类逐渐将三体纳入到可理解认同的范围之内,在一厢情愿的文化想象中不断将其同化,把善良和平的人类心灵逻辑也施加在三体身上。这种在对三体和宇宙并不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意味着“诚心”超越了“逻辑”,正如“程心”这个名字与“诚心”谐音,虽然是善良意愿,但终究也是人类自己的意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人们却常常忘记“已所欲”也许亦应当“勿施于人”,施与不施完全取决于对自我之外他异性客观存在的清醒意识。在伦理的领域里,纯粹理性也应为实践理性立限。
那么作品对罗辑这位始终恪守职责的执剑人又是何种态度呢?罗辑的存在寓示伦理行动应当受到客观理性认识的必要限定。作品一方面肯定罗辑,另一方面却没有完全否定程心。即使程心不止一次做出错误判断,她的善良美好依然充满人格魅力,作为心灵自由表征的“善”始终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宝贵部分。客观认知外部世界是保障文明在自然中存活延续的基本条件,心灵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却使文明充满意义感。
正视人类文明的有限性
小说中的三体世界虽然科技发达,但其文明完全是围绕着“如何在三个太阳的恶劣生存环境中谋生”这个问题发展出来的,为了避免使文明变得脆弱,它们禁止一切艺术、哲学与情感活动。人类在有能力用智子锁死地球科学进步的三体人看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虫子,但没有情感和深层意义体系的三体在拥有自由心灵和丰满意义世界的人类看来同样也是虫子。在三体与地球共同流浪的岁月里,小说安排双方开始有了一些真正的交流,智子不再只是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一个地球女性,它也开始尝试接纳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当地球毁灭,程心、智子及她们携带的小生态球为人类和三体人在未来岁月中能否携手共创文明留下了一点点期待。
然而,小说叙事却一再反转,程心宁肯冒着飞船失重的危险将生态球带离地球,生态球既代表着文明延续的希望,又意味着潜在的危险,它是脆弱的,只能在封闭的球体内部保持着岌岌可危的平衡。三体人尝试理解人类的情感,那么地球人类又从三体世界和作为黑暗丛林的宇宙中学到了什么?小生态球能否向着与地球迥异的宇宙敞开,通过从外部空间汲取新的生存动力而变得强大,抑或只能在自我封闭中维持令人伤感的美丽?《三体》并非乐观的结局背后埋藏着叙事者对人类文明依旧陷入自我封闭的隐忧。
客观认知外部世界的规律与心灵的自由追求作为推动人类行为活动与文明进展的两个关键动力,未必能达到一致,反而是在其彼此矛盾断裂的张力中可能发展出一种既能自由追求又善于自我克制的文明。超越自我的外部世界与纯粹理性作为限制心灵过分膨胀的力量,可以使意义建构免于因事实地基的缺失而陷入主观主义或虚无主义。
由于人类在地球文明中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很难对以自我为中心精心建构的文明系统进行自觉反思,但当《三体》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超越地球的浩瀚宇宙中,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人类文明的有限性和蕴含着无限未知的地外空间时,“逻辑”就更容易为“诚心”设限。这样,《三体》便以科幻文学特有的诗学手法,“以自然科学思维和认知视野,将考察人类文明生活的价值坐标放大到一个惊人的尺度上,同时又以文学的方式,将其与人的生活密切地联系链接起来,从而互相撬动、延展了科学与文学各自被文明的惰性与生活的尘埃遮蔽的思想空间,造成了科学与诗性的聚变效应。”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