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是通识核心课程“社会研究:经典与方法”课上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李从予,现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19级本科生。本文在2020北大通识核心课优秀作业评比中,获得“系列二:现代社会及其问题”部分的二等奖。
作者基于对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的阅读,并结合自己的田野调研经历与对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历程的理解,就乡土社会现代的症结以及适合乡土社会结构与特点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展开写作。作者从费老写作时关注的问题发出,从土地制度中的“田面权”、“田底权”以及农民理解土地的观念入手,就乡村工业发展的可能与模式加以讨论。她指出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是技术改进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关系再组织的问题,并且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乡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Vol.1206
优秀作业
迈向现代化经济的
乡土本位社会
李从予 | 元培学院
一
基于乡土本位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20 世纪,于现代中国而言的最核心抉择即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面对着西方工业化文明的冲击与挑战,寻求一条适应于中国传统根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这种道路选择并非是单纯效仿西方工业革命进程所作的经济改革,更是一场基于乡土本位观念,与中国数千年制度文化传统相碰撞与融合的社会转型。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开篇即点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是“传统的复旧”。几千年的中国农村传统已经在乡土社会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平衡,一味地颠破传统以寻求现代化与工业化,即会面临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的种种失衡问题,但平衡也并非意味着可以自足,在面对强大外部冲击与内部长期顽疾时,社会必然也需要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因此明晰“乡土”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中发挥的作用是使之稳定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而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学者有别于西方学者,扎根于本土进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各个地域村落中的亲属关系、生产生活组织、财产继承形式、婚丧祭祀仪式都紧密关系着当地在经济生活中的合作与发展形式,乡土社会成员的选择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因此社会转型之路也必须由此开始。
在选择道路前还需明确的是,我们为何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特别中国农村,之所以要进行现代化社会转型并非是“为了工业着想”,追随西方工业革命步伐,而其核心目的是为解决中国“最基本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即“广大农民生活的痛苦”——饥饿问题,“为了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提高生产力使中国大部分人口吃饱穿暖是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而仅仅在大城市发展工业并不能真正解决扎根于乡土的数亿农民的最基本问题。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农村,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同样来自农村,只有帮助农村实现能于其乡土本位相融合的现代化转型,找到乡土社会现代化的症结所在和适合乡土社会的现代化经济模式,才能实现这场现代化变革的核心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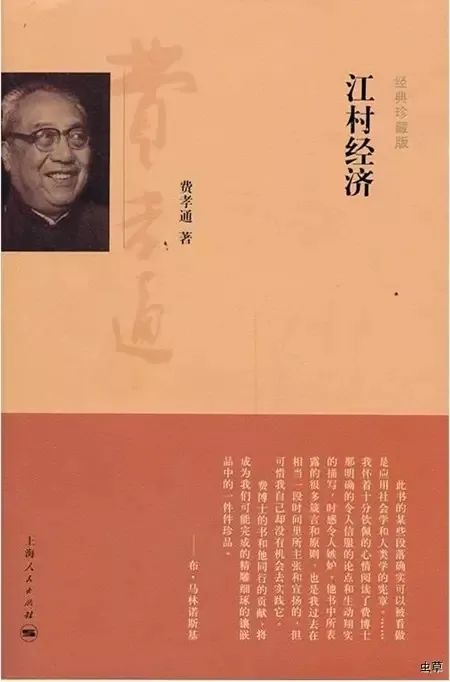
图为《江村经济》书影
二
土地制度: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传统根源
由于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现代化经济发展进程也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农业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丧失?乡土社会成员又为何如此依附于土地?农民进城是否就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这些都是有待通过土地制度及其背后乡土社会成员对土地的联系所要回答的问题。
乡土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即是土地。对于乡土社会成员而言,首先,尽管土地的收成会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动,但人们总能在土地上寄予丰收的希望,它是乡土生活中的核心生产资料与经济来源。哪怕人们外出打工或是从事其他行业遇到冲击,也总能回归土地,以其取之不尽的性质获得经济保障。其次,土地是父承子继中最稳定持有的财产,哪怕钱财散尽,土地依旧可以作为固有的资产传递给后代。此外,土地更是开枝散叶的家庭宗族所赖以依附的精神根系。乡土社会成员及其祖辈生于斯、长于斯,祖宅、祭祀,一切社会亲缘关系与宗族观念都依附于土地,土地的延续甚至是一种孝道的体现。由于土地具有这样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多重意义,因此土地制度并非是割裂的产权问题或经济制度,其转型与改造也并非是单纯针对于土地本身的。土地制度关切的是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文化模式等组成的有机整体,也即是乡土社会现代工业化的肯綮问题,更是今天仍在影响着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对于经济社会而言,土地权的归属则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在江村,土地所有权在农村家庭中持续稳定地继承传递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永佃制的支持。大多农民作为土地的实际耕种者并非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他们拥有着土地的“田面权”,而“田底权”往往掌握在不居住在农村中的地主手中。由于“田面权”所有者对当地乡土的融入性及对土地的熟悉性,地主会通过宽容交租等方式尽可能让持有“田面权”的农民持续耕种这片土地,拥有“田面权”的实际耕种者也会因如上所述的土地非经济价值而不会轻易出售土地,这保障了土地不会被随意交割。因为失去土地权对农民也意味着经济来源保障与精神归宿的消失,因此当农民进城伴随着土地权丧失的发生,大量失去土地且无法获得稳定城市工作的农民便会聚集形成城市中的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对于拥有“田底权”的不在地主而言,他们也会因土地所有权所建立的与乡村的联系,而避免大规模破坏或改造农村。因而土地制度既维持了地主和佃户所构成的城乡间金融系统关系的平衡,也“保护了贫农不致因乡村工业需要而迅速失去土地权” 。
今天的土地问题困境与数十年前费老笔下的江村土地制度有相通之处。去年夏天,笔者在湖南益阳进行田野调查时,一位农业企业负责人即表示,当地农业机械化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他认为这一是因为南方本身耕地面积不及东北,“每人只能分到七八分地”;二是当地农民仍旧受到小农经济的思维限制,将土地视为各家最重要的财产,将田埂视为不可触碰的、划分财产的重要依据,不愿交出的土地与田埂的束缚使得大规模的机械化设备无法应用于农田。这位企业负责人将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希望寄希望于通过政府出台政策破除这种小农经济的束缚。他指出了乡土社会成员重视土地的现象,但这根植于乡土社会中对土地多层次的依赖,固然不能直接归因于农民的传统思想,也非是单纯政策因素所能化解的困境。
第一点提及的耕地面积限制是中国广大地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条件本身的约束造成地块的分散,另一方面也存在分家造成的影响。土地作为家庭传承的重要财产,在每一次分家时都要依据家中男性子嗣情况进行合理公平的划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将面积本就有限的田地切割成更为细碎且分散的地块。
而从第二点所有权来看,今天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很大程度上即类似过去的永佃制。农民拥有对土地类似“田面权”的承包经营权,但很少愿意通过政府给予的补偿将土地承包权进行转让,因为农民实际上将土地承包权赋予了财产权的属性,田埂更是这种权利所属的标志。在江村,田埂决定了土地灌溉的水资源流向,也继而决定了传统农业的收益,因此田埂的保留象征着土地权的持有。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户需要保留土地权以在进城失败后仍得以返乡,而有能力进城的农户也会将土地留给仍在村中的亲戚邻里,以保留在无法在城市中立足时的安全感。土地是乡土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最基础的保障,这才是农民不愿将土地转让给外部进入的规模经营企业的核心驱动因素。
故而在乡土本位社会中,农业现代化并非是单纯的机械化普及问题,任何技术的应用背后所需要的是匹配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们不能仅看到土地私有化与自由交易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更要意识到现代化经济的核心作用是要提高这些最广大乡土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而资本介入、土地兼并只会更大程度上造成农民面临失地失业的双重危机,形成更大规模的贫困群体。
要解决农民基本的饥饿问题,就需要在保证农村社会结构稳定的同时,为农民找到合适的收入途径。土地是农民的基本收入保障,却也难以在维持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水平。试图以规模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从客观自然条件与社会关系及制度依附上都并非易事,因而除在提高农业亩产、灌溉、育苗等技术外,乡土社会仍需从现代化工业发展中寻求新的出路。

图为在江村调研的费孝通先生
三
“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的合作与连接
从民国时期起,中国农村地区就开始出现了大量专业化的手工业区域,这些手工业具有现代经济的特征,比如远程贸易、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区域,在一些地区甚至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但彼时最发达的农村工业仍以家庭工业作坊的形式存在,却并未形成工厂,而是维持着“家庭+包买商”的生产和市场制度。对此,学术界的一种解释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和纺织业的低利润率构成的“过密化”。由江村可见,以缫丝业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经营者主要为农村女性,她们无法参与到农事劳动之中,一旦缫丝业亦为工厂机械化取代,就意味着大量妇女成为剩余劳动力,她们或恢复家庭工业,或进入城市成为工薪阶层,而后者造成的婚姻母子关系疏远则会进一步破坏农村家庭。另一种解释是包买制这种制度形式相对于工厂制度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优越性。但这两种解释仍旧无法完全阐释在面对工业进步的技术改进和家庭生产的质量控制问题下,为何当时的家庭生产仍未被工厂所取代。但可以明确的是,由传统手工业走向工业不单纯 “是一个技术改进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
而在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衰退与技术进步的冲击背景下,可以看到农村通过工业以提高生产力并稳定收入的需求是迫切的。以江村的蚕丝业为例,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发展,缫丝流程逐渐被机器规范化、标准化,机器生产出的大量高质量生丝使得传统手工生丝价格被大幅打压。稳定农民蚕丝业收入的需求迫使农村引入有赖于集体合作工厂的蒸汽引擎以提高农村生丝的核心竞争力。
而为何工业一定要在农村落地,而不能依靠城市工业使农民进城务工以提高收入呢?首先,需要重回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议题:解决最广大农民的饥饿问题。现代化经济与工业化发展需要通过保护农民基础生活,而非破坏农村生活的形式来发展工业,满足资本家的需求。当时中国超过 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城市中组织工厂或许可以快速推动工业发展,但城市本位的工业化将使得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离开土地的依附,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完全资本化工厂化的运作更会使得低价高质的产品将传统农村直接淘汰,造成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破坏与对城市劳动力的冲击,更牺牲了最初想要保护的农民利益。“离土不离乡”,上述土地制度的论述已经说明了土地对于乡土社会成员的重要性。他们可以离开土地农业,却无法长久离开乡土土地,因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性正扎根于土地。
面对现实中收入下降、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甚至质押土地以偿还高利贷的恶性循环,需要发展乡村工业将技术改革的利益归还给生产者,使“他们(农民)生计既有了保障,也不必借钱了,这非但安定了工业,也安定了乡村里的土地问题。” 中国的传统经济中本就含有以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的工业,人性与家庭是乡土社会中传统工业的核心,它并非是乡村工业的绝对劣势,而恰恰可以作为维系乡村工业的纽带,在机器生产中保留乡土社会的非机器化的制度文化特性。
而何以发展乡村工业?“合作”与“士绅文化”即是乡村工业的特殊关键所在。
家庭是乡土社会中的核心经济单位,在乡土社会的所有制下并不存在个人所有权,“个人所有权总是包括在家的所有权名义之下。” 乡村工业需要将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整合成为现代工业。在江村,这种形式通过合作工厂的形式得以完成。从蚕丝业的生产来看,在孵化蚕茧过程中,农民通过在共用房间中集体喂养以控制温度湿度进行合作;在幼蚕时期过后,仍旧依靠各家各户的更大空间以家庭为单位孵化蚕茧,而在缫丝时又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贡献的原材料,以集体工厂为单位进行机器缫丝制造,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生丝并分得红利。在不同生产阶段中家庭与合作工厂发挥着各自优势,使原材料生产与加工在农村一体化完成,亦不影响农村原有的农业土地经济。
由家庭手工业过渡到合作式的乡村工业经济,有别于国家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或强制推行的合作经济,更不同于都市工业经济,其保留了农村家庭的基本生活形式,同时将工业经济建立在本就因乡土关系连结的农村共同体之上,以乡土关系促进合作经济的发展,将机器生产以伦理关系维系的合作形式融入乡土社会结构之中,免于被资本剥削,而真正为自身谋得利益。
然而农民并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从资本、技术到制度的全部改革。在乡土社会成员自身的合作之外,外部力量的引入同样至关重要。士绅文化在其中即起到了重要作用。士绅多为乡土中的地方精英,他们拥有农村社会以外的知识与资源,同时怀有建设地方乡土的崇高愿景。他们或许并不拥有在行政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却能在地方发展中获得有效信任并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外部变革力量与乡土传统中的连接桥梁。
在江村,发挥士绅作用江村农民建立起合作工厂的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从国外学成蚕种改良及科学养蚕技术的她将蚕茧科学生产的方法,通过蚕业学校与当地领导人的连接带入江村,同时也从组织上创新地依乡土特性,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进行乡村工业变革。
外部的政府信贷系统、资金与政策支持固然也对乡村工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士绅文化的连接作用较之则更能在最本质层面从技术制度与文化上将变革生于实处,在教育尚不普及的农村中将现代化工业与国际化标准落地乡土,使乡土工业经济以强有力的竞争力焕发出独属于乡土的内生活力。

图为开弦弓村(江村)生丝产销合作社
四
合作与连接的变式:乡土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展望
江村的合作工厂改革并非是完全成功的。一方面,受到市场环境价格波动与农民对自己在工厂中所获得的主人身份认知不足的影响,他们并未获得充足的、其所唯一重视的经济利益。而另一方面,乡村经济的机械化与工业化发展仍旧导致了劳动力剩余,使得农村人口自发地向城市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合作与连接的形式尝试与乡村工业 的发展路径就是失败的。
事实上,承接乡村工业的发展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也是一种合作与连接形式的变式。在苏南,家庭大多紧密依附于土地,“血缘和地缘关系相结合,将家庭、集体和地方行政体制并合一处” ,依靠农业区域发挥原有社会结构的作用;而与之相对的温州模式则通过商品和人口流动形成的庞大的宗族网络,形成可以彼此互相依附互助的家族企业。两种模式都依托并利用乡土社会的关系特征,将现代化企业与家庭和乡土紧密融合,在其建立的网络之上进行合作发展。
而从连接形式上,在士绅之外,上山下乡的青年力量也在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这场政府发动的大规模人力资本流动运动使得教育与技能被广泛普及至农村之中,知识青年的连接作用促使农村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大幅增加,进一步促进 80 至 90 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入世”后中国“世界工厂”的建成。
今天中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也同样是依靠着乡村经济一村一业的模式,在基层乡土之中达到某一产业的领先制造水平,并由此激活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经济,这是今天乡土社会的合作与连接仍在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农村人口外流已成为不可逆趋势,乡土社会与土地的联系在逐渐弱化,其症结仍在于尚没有充足的经济发展机会适应于乡土土壤,而这也是中国的乡土本位社会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1] 潘建雷. 2015. 合作社:乡村工业的可能模式——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实质主题[J]. 社会学评论,3(06): 64-73.
[2] 周飞舟.2013. 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J]. 社会,33(03): 39-50.
[3]渠敬东. 2013.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J]. 社会,33(02): 1-32.
[4] 彭南生,金东. 2010. 论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J].史学月刊(11): 80-85.
[5] 吴知. 1936. 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6] 周飞舟. 2006. 制度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Chen, Yi and Fan, Ziying and Gu, Xiaomin and Zhou, LiAn, 2018.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云舟 编辑 / 柏榕 校对
通识联播
精彩依旧继续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