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篇文章讨论下民族性的问题,因本人比较惫懒,能坐着就绝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趁着外面高温,周末无事,就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
先说说我为什么突然想写这个话题。
因为10年前,那时候还很青涩的我偶然间读到《丑陋的中国人》,读得还津津有味,觉得太有道理了。此后10年流转,今年疫情期间发生了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就想着再重温一遍本书,没成想书还是原来的书,我已不是10年前的我,看了前面一部分就将我恶心到不行。我实在无法想象,当初自己是怎样读完的,居然还那么起劲。
所以心里一直憋着一些话,不吐不快。
言归正传。
既然是“民族性”,自然有优秀的一面,也有病症的一面。
前者是一个民族赖以传续的内核动力,后者则是该民族起伏波动的直接动因,也被叫做“劣根性”。
自民国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个主要分支。
大体来看百年:从民国时鲁迅先生开始,到后来台湾的柏杨,再到改革开放后各种公知大V。
而批判的本质:也从鲁迅先生的建设式批判,到后来者的苛责计较,以及为批判而批判,直至屁股长歪了。
一
“民族劣根性”的讨论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人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找出问题,进而对其进行矫正。
如文学作品就有文学批评。作家与文艺批评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一旦这其中掺杂进个人的主观因素,或者某些外部因素,那将对整个体系造成破坏性的冲击。
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
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演进,必然有其生力,也有病态。生力是国家历史推进的根本动力,病态则是演进过程中遭受的阶段性的顿挫波动。
生力自古长存,病态随时忽起。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生力是从古至今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病态则是这个过程中偶尔从外边感染的事变。
比方说,我们从小到大,人都会感冒或得病。小时候会,长大了依然会。我们活着的生命就是生力,而感冒得病就是阶段性的感染。人从小到老不知道要得多少次病,这次好了,过段时间还会得病。
文化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讨论的“民族劣根性”其实是在一个阶段感染的病症,并不是我们民族从古至今就存在的。
当然也就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得病,就否定了我们整个人的存在,就要去寻死,那不是脑子有病嘛。

二
民国时期之所以要大批“劣根性”,是因为满清三百年积累下的病症在一个时期内全面爆发。
满清因为是少数部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持其统治,政治上采取高压态势,思想上禁绝了从宋明以来700年的民间自由讲学,知识分子只得埋首于故纸堆中,去训诂、考据来躲避现实。
其次再用八股文限制人的思想,笼络归顺的汉人。凡是当了官的汉人,都在思想上成了满清的奴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捞钱成了他们的唯一追求。传统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代表下层百姓沟通上层的社会中坚彻底变了质。这个国家想不病都难!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影像中,清末民国初,老百姓都一脸木讷、愚昧,这就是三百年积累下的病态。
所以鲁迅先生才要大声疾呼,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他爱之深,所以责之切。
比方说:女人裹脚。
这是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流行,而在清代盛行到极致的对女性的摧残。在此之前,我们文化中没有;在新中国建国后,我们文化中也没有了。
由此可见,所谓的劣根性就是一个阶段内被感染的病症。时代过去了,该病自然也就治好了。
新中国的建立,就是我们民族内部自身孕育出的一股新力。这股新力舒发进而革除了旧时的弊病,方才能建立新阶段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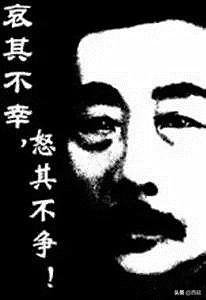
三
下面就来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老实说,这一次的阅读体验很不好,非常不好,简直把我给恶心坏了。如果柏杨现在还活着,如果思想发生大的转变(高年龄的人思想很难转弯),他必定会成为一名公知。
这并非是对老前辈的不尊敬,而是从他的思想推导出来的。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压根儿就不是一部专业的学术著作,只能算是一部情绪的积聚发泄体罢了。书中的观点没有一个是经过严谨逻辑分析出来的,而只是一种感性的对现象的直观认识罢了。
1、比方说序言中描述了一个“酱缸国”医生与病人的对话:
病人结婚前去医院拿体检报告,医生告诉他得了三期肺病,咳嗽、发烧、吐血等,病人于是就杠上了。说你刚才也咳嗽了,说你喝过洋墨水就看不起人,还说看他快结婚了专门打击他拆散他们。
这哪是个病人,简直就是个杠精嘛。下面摘录一段,让大家感受下:
病人: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这会是一个病人对医生说的话?到底病长在谁的身上?
我反正看不出这人得病了,这也不是现实中病人的说话方式,反而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杠精。即便是真正的杠精,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三期,早就吓得瘫地上了。
而现实中的实际反应是,不相信自己得病,要么开骂,要么直接挥拳头。哪用得着在这儿干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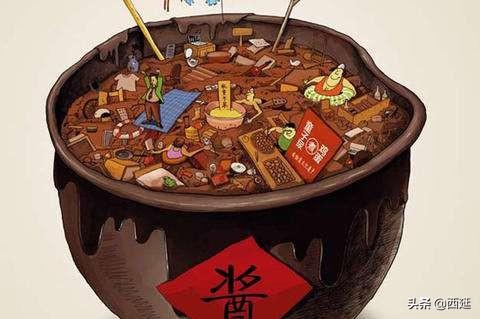
酱缸
2、再说柏杨说中国人脏、乱、差,说话声音大
什么时候说话声音大也成了民族的劣根性了?这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式与特性罢了,属于坏习惯。
至于脏乱差,老百姓那么穷,生活无着,你让人如何讲究?连肚子都照顾不过来,还管这些。
这就是典型的脱离了现实而胡乱批评。
他还说,去马来西亚博物馆参观,见有说英语的、马来语的、却没有说华语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马来人心胸不宽广,以及马来的华人没力量没地位。
看看他的推导逻辑,简直没有逻辑可言嘛。
这明明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跟道德上的心胸有半毛钱关系吗?
还有就是当地华人为推行华语教育所做出的牺牲,你在那里就不知道去调研下吗?随口就下结论,学问真的不是这样做的。

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
3、再来看一段吧: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们幸福。在人们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
眼熟吧?是不是跟之前的某著名作家的言论何其相似?
“我不关心国家的强大,我只在乎小民的尊严。”
啧啧,你们说说,柏杨如果还活着会不会成为公知?
这样的认识何其可笑!真当世界是你家,想怎样便怎样?不强大,连说话喘气都是错,哪来的幸福可言?这世上从没有国家贫弱,而人民却幸福的!
好了,关于这本书我就不再赘述了,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作者的立论点错了,书中的结论自然说不上正确。

最后,我想郑重强调一点: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优劣所在,对于“民族劣根性”,我们要反省要矫正,但千万别走火入魔,别走到自我阉割。
其实真正对民族有害的糟粕,在民国时就差不多刮完了。新中国在土改、妇女解放运动后,残余的已经对整个民族无关宏旨了。
所以,我们要谨记一个原则:只要不是大到影响国家发展,影响下一代的传承,那些所谓的缺点都无伤大雅。
看看西方殖民历史的残酷剥削,种族矛盾的尖锐,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安定,也没见几个西方人反省批判。当然他们不反省,受伤害的是他们自己。
但我们也切不可自己苛责过甚,甚而自戕!
如今应当聚焦的,反而是金融资本时代,资本对人的异化!
以上。
补充一点:
我看到书评区很多朋友的回答很激进,我很理解。虽然也有扣帽子的,但都是这么年轻过来的,也没什么可生气的。
只是有一点,很多朋友将“劣根性”与“坏习惯”搞混淆了,这里简单说一下:
前面说了劣根性是一个阶段性,外部侵入的病症。满清260多年的病症,在民国和新中国土改、妇女解放运动后,基本被肃清了。
新中国也是一个新的环境,但人对环境依赖产生的劣根性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侵入过程,我们现在时间还太短,民国时出生的一代人都还没过呢。
但更重要的还是跟外部压力有关。满清文字狱的极度压迫,所以问题才那么严重。纵观古代大家看看汉末、唐末、宋末、明末都不像清末那么严重吧?这就是环境的差别。
至于声音说、随地吐痰、广场舞打扰人等,这些都是坏习惯罢了。是国家富裕,人民意识提高的一个过程。民国时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那时人连活着都用尽全力,哪还管得上这些?
坏习惯需要的是文化道德教化,更要时间。至少现在出国没有前几年那么多坏习惯了吧?这就是素质的提高。别总拿日本跟我们类比,人家发达几十年了。就像前几年西方指责我们雾霾,难道他们曾经没有吗?所以这种指责毫无道理。
仅供参考,不同意的可以讨论,但别动辄扣帽子或人生攻击。我更希望大家能冷静思考,对自己提高认识很有好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