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过去两期咱们分别讲了,克里雅、桑株、克里阳、喀拉喀什河道和新藏线故道。这几条古道北段的对应点,分别是于田县、和田市、皮山县和叶城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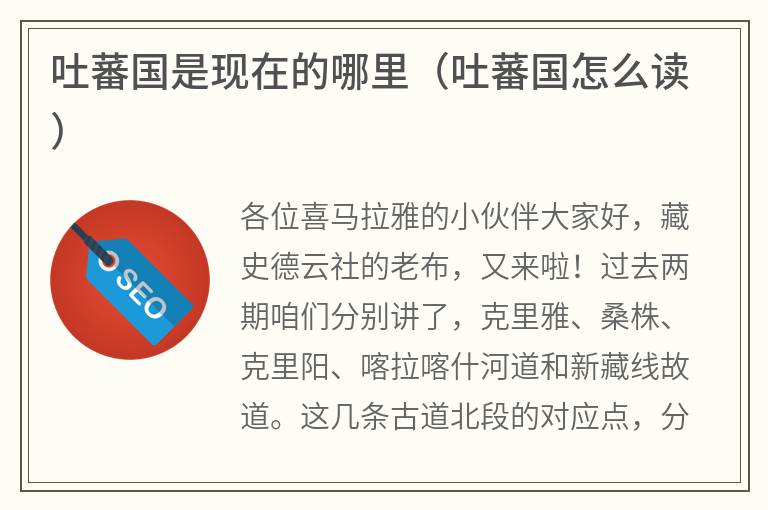
吐蕃国是现在的哪里(吐蕃国怎么读)
在唐朝的时候,除了叶城以外,其他几个地方都在于阗国的范围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于阗和吐蕃的关系之深。
今天,在就来好好唠唠,于阗和吐蕃,这两个貌似隔山跨河,相距辽远之地,到底有多少渊源。
西藏和新疆的联系古已有之,早到了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地步。之前在讲女国的时候,老布曾经提过,生活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族群,有一条从藏北羌塘贩运食盐,到低海拔地区换粮食的古代商道。这条商道被称为“盐粮古道”。
一般来说,盐粮古道的路线是从北向南,穿越喜马拉雅的沟谷,到印度进行物资交换。阿里粮食不够吃,印度不产盐,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南疆绿洲也是农耕区,也不产盐,为啥一定要拉着藏北的食盐,往南走换粮食,往北走不行吗?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人,往南走换粮食,靠近昆仑山的人,往北走换粮食。这样的话,盐粮古道就不是一条单向往返的道路,而是以西藏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商路了。
于是,在从南疆到西藏的路上,流通过来的就不止是粮食了,还有丝绸、茶叶,以及佛教思想。
关于阿里古入江寺墓地发现的丝绸和茶叶,咱们讲过好几回了,就不再赘述了,这次咱们主要讲佛教思想。
于阗国的佛教鼎盛很早就出现了,在不晚于公元3世纪的时候,于阗就已经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了,并且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玄奘路过于阗时,对于阗国大加赞赏,称“(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佛教。”
要知道,当时于阗国的军队也才四千人,僧徒都五千多了,可见佛教势力之彪悍。
在藏文文献《柱间史》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两个“李域”的沙弥,供奉文殊菩萨十二年,怎么也修不成正果。于是,文殊菩萨就对他俩说:“你哥俩这脑袋啊,实在是没法弄。得了,你俩也别跟这儿楞练了,去观音化身所在的吐蕃之地,他名叫松赞干布,你俩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于是这两位沙弥,就跨山跃河的跋涉到了吐蕃,当他们走到拉萨以北的堆龙山口时,看见这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打听,当地人就说了,“这些都是赞普处死的罪犯”。
这俩人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哪能杀人呢?这松赞干布哪是什么大悲观世音化身呐,这不嗜血成性的暴君嘛!”
但是因为有文殊菩萨的指示,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等他们走到旦巴滩的时候,又看见遍地都是割了头的、剜了眼的、砍了手的、剁了脚的,烙了皮的、斩了腰的,反正就是各种惨不忍睹。
这俩沙弥都快疯了,转身就往回逃,一遍跑一边咒骂吐蕃赞普是个暴君。
这事儿松赞干布也知道了,他对大臣说:“你去当巴滩,把两个光头,穿黄袈裟的人,给我带回来。”
这俩沙弥见到松赞干布就质问了,“乔帮主乃是大慈大悲的怙主,可你却滥杀无辜,导致涂炭生灵。你对得起帮主吗?!”
松赞干布瞅了他俩一眼,说道:“我对臣民向来秋毫无损,然而,对那些用仁慈不能调伏之人,就只有用严刑加以惩治,以维护十善之法。”
结果这哥俩脑袋还挺硬,咋说也绕不过弯儿来。
松赞干布一看,这哥俩也就这层次了,就让他俩去睡觉,心里想着回家。等他俩一觉醒来,已经躺在千里之外的自家门口了。[2]
这故事挺有教育意义的,老话说“没有霹雳手段,显不出菩萨心肠”,修佛不是爱心泛滥,不是一味地做滥好人,菩萨还有忿怒相呢!
最近就出了个供战犯的事儿,可见有些人对世间的基本逻辑,都搞不清楚了,就这水平再修个一万年也白扯。
另外,在这个故事里还出现了地理名词,就是“李域”。
“李域”这个词,广泛见于各种版本的藏文文献之中,关于这个词所指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林林总总的有九种之多。
比较有影响力的三种,分别是“于阗说”、“新疆说”、“泥婆罗说”,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是“于阗说”。
至于各种说法的细节,咱们就不讲了,都是考证,太细碎了。我们只要知道,于阗是个国家,不是一个城市,有时候藏文文献写的“李域”,会特指某个城市,所以有时候能在文献里看到“李域”和于阗是并列关系。
比如说在敦煌文献《于阗教法史》里有一段话,“李域于阗中部的海心之处,在于阗城内,集市上方,供奉扎瓦夏佛像的下面,海心至今尚存。”
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李域”指的什么地方,而是“李域”的这个“李”(li),到底是什么意思。
《藏汉大辞典》里,对“李”的解释是“钟铜”或“响铜”,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可以用来铸造各种乐器。比如说“李玛尔”就是“紫响铜”。
王尧先生认为南疆一带产铜,藏语的“li”又是青铜合金,所以“李域”的意思就是“产铜之地”。
但是藏族学者东嘎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他在《东噶藏学大辞典》里面解释“李域”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属于阿里地区的地名。
我们之前讲了西藏和新疆的交通线,大家应该清楚,从地理单元上说,南疆和阿里紧挨着,只不过中间隔了一条昆仑山,让大家感觉上很遥远。
那么“李域”的名字会不会是从阿里传过去的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象雄的时候,曾经提过象雄王室的名字,末代象雄王的名字叫李弥夏。
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象雄王怎么会姓李?
如果东噶先生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以地为姓,或者因姓为地,在中原早期也很常见,这也算是一个解释了。
而且在一本藏文手抄的《于阗文书》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于阗国王有好多的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被称为‘李域王李’。其名也被冠于地名,故称之为‘李域’。”[3]
不过我们要清楚,这个“李”和李世民的李,没一毛钱的关系。唐朝时的于阗国王姓尉迟,根本不姓李。
这位疑似跟“李域”有关的于阗国王,被学者认为标定为于阗国首任国王萨尼。他所在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1年左右,这时候陇右李氏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但我们知道,象雄据说年代非常久远,至于到底久远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好说,不过上溯到两汉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个年代久远的“李域”之“李”是不是跟象雄有点关系,只能看以后的研究成果了。
其实,松赞干布是不是真的见过于阗沙弥,这个真不能确定。
比较公认的吐蕃和于阗僧人发生关系,出现在金城公主在西藏期间。当时在位的赞普是赤德祖赞(尺带珠丹),也就是公元八世纪的上半叶。
当时,于阗国发生内乱,僧人遭到了驱逐。无处可去的于阗僧人便来到了吐蕃。正好金城公主在西藏期间,吐蕃佛教有了一个小高潮。金城公主便请求赞普收留于阗僧人,于是尺带珠丹建寺安置,僧人们得到了三年的供养。[4]当然这些僧人最终还是被撵走了,这部分内容等讲到尺带珠丹的时候,咱们再细说。
这个记载广泛见于各种藏文史料,在于阗发现的藏语写本里也有记载,所以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内容。
不过最新发现的证据,可以证明两地之间的佛教传递,远比尺带珠丹的时代早,也比松赞干布的时代早得多。
在龟兹石窟里面发现的题记上写着,哲车王给吐蕃聂赤赞普送去了佛经,结果被聂赤赞普给烧了。[5]
聂赤赞普大家还记得吧,这位可是吐蕃的第一位赞普,号称是从天而降的神王之子。在聂赤之后的三十二代,才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时间该有多早了。而且这个时间,也比佛教自己说的,在拉脱脱日聂赞时期,有个装着佛经的宝箱,砸在了雍布拉康房顶上早多了。
送到聂赤赞普面前的佛经被烧了,一方面说明佛教传播的艰辛,另一面也说明,聂赤不认同佛教思想。
这其实也挺好理解,毕竟他是被“十二智本”扛在肩上拥立为王的。您说人家扛着你嗷嗷跑,您跟人家说,“佛教瞅着也不赖哈!”
这多少是差了点意思,按张国立的台词来说,“做人要厚道!”
再说了,以当时本教的势力来说,送您回天庭,其实也未必办不到。
吉如拉康的塑像
除了这些见于史料的记载之外,两地之间的联系,还能从艺术的层面看得出来。
按藏文史料《贤者喜宴》的记载,松赞干布时期修建昌珠寺,就请了于阗僧人雕塑佛像,并且留下雕塑艺术的技法;吐蕃赞普热巴巾时期
建造温江岛本尊寺,还专门从于阗请来了著名的雕塑家。
另外,张亚莎老师在论文里还写到,“目前西藏保存的吐蕃时期塑像不多,但从造像风格来说,拉萨扎拉鲁甫石窟中的石雕造像与山南吉如拉康内的泥塑造像,有较大差异,可以认为样式的渊源不同。
拉萨的石雕造像可能与尼泊尔有些联系,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吐蕃本土造像的风格,而吉如拉康的佛像,则很可能来源于阗雕塑的粉本。”
张亚莎老师所说的吉如拉康,位于在乃东县结巴乡吉如村,是非常罕见的吐蕃时期的寺院建筑。
宿白先生在谈到西藏寺院建筑分期的时候,将吉如拉康排到了第五位,前四个分别是大小昭寺、扎拉鲁甫石窟和桑耶寺,可见吉如拉康的江湖地位。[6]
有喜欢西藏艺术史的朋友,强烈建议去吉如拉康看看。
这座寺院离桑耶寺很近,直线距离只有三十公里,路也不难走。但更多人的还是愿意去桑耶寺,我这么说不是说桑耶寺不好啊。桑耶寺也很好,但毕竟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晚期的,而吉如拉康这座面积很小的寺院里,保存着难得一见的,吐蕃时期的建筑和雕塑式样。
这座小寺院的主体建筑,建成的年代在公元八世纪的上半叶。整个建筑的结构,保存了吐蕃时期的建筑规制,使用的梁柱斗拱硕大古朴,在柱头栌斗上的装饰雕刻,刀法简洁洗练,古风凛凛。
而吉如拉康里的雕塑,保存比较好的释迦牟尼主尊和八随佛弟子,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原造像特点。[7]这也是张亚莎老师认为,这些造像塑造时使用了于阗粉本的原因。
最有意思的是,主尊旁边的男女供养人塑像,被认为分别是尺带珠丹和金城公主。说真的,我是真心希望供养人就是这两位,但是已经有学者提出质疑了,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不过,吉如拉康的创建年代,确实与尺带珠丹和金城公主的时代重合。当时吐蕃佛教有了点冒头的意思,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建设的寺院,借用两位主要施主的相貌做塑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目前西藏保存的寺院里,还有一座在艺术风格上与于阗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康马县南部的艾旺寺。
上世纪的40年代,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在西藏考察时发现,后藏地区有一批寺院的雕塑风格,与常见的印度式样迥异。
他一开始将这种艺术风格用寺院所在地区分类,称为“萨玛达类型”。
但他到达艾旺寺后,寺内巨大而精致的雕塑震撼了图齐,尤其是其中一间佛堂的壁画题记上,写着“李域”。于是他认识到,这一区域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后弘期早期卫藏艺术中,有别于印度艺术的另一条源泉。
随后,他在第二次赴藏考察时,又发现了几处有相似造像风格的寺院,比如泽乃萨寺、达囊寺、萨迦寺、扎塘寺,以及更晚一些的纳塘寺。这让图齐认识到,在西藏11到12世纪的艺术中,存在一种“波罗与中亚”,两种艺术融合的流行风潮。
所以,他在鸿篇巨著《梵天佛地》里将这一类艺术风格,命名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亚。需要注意的是,图齐笔下的“中亚”指的就是于阗。[8]
现在去到艾旺寺,依旧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塑像,但当年图奇亲眼所见,写有“李域”题记的壁画,已经完全损毁,难觅其踪了。
不过,寺里那些残损的塑像真的无比精彩。他们高大的头冠、恬淡的面容、厚重肥腻的衣纹、排列整齐的团花图案,以及佛像脚上的长靴,都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西藏是一处文化交融之地,这种兼容并蓄的杂糅,成就了西藏之美。
艾旺寺塑像_张超音(拍摄)
艾旺寺塑像_李希光(拍摄)
艾旺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座小寺院,每次去西藏我都要去看看,哪怕是绕道也要去瞅一眼。
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队里一位北京的老先生,见到残破的塑像,不仅潸然泪下。当时我就问,他是这么美的塑像,为什么不好好维修一下。我当时说:“再好的维修,也会损失历史的印记。我们要做的是见证历史,而不是去修改它,掩饰它!”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中国的审美是在走下坡路,西藏如此,中原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了维修过的那些文物的心情,只能用暴跳如雷来形容。
我宁愿这些文物,像我们一样慢慢得老去。这就是每次我都要去看看艾旺寺的原因,每次去了看到依旧残破的塑像,我都会暗暗庆幸,“吾已老去,汝尚依旧,幸甚!幸甚!!”
好啦,这期就先讲到这里,下期咱们接着来讲于阗与吐蕃的关系。
参考书目:
[1]、《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_沈琛;
[2]、《柱间史》_阿底峡(著)卢亚军(译);
[3]、《藏文文献中“李域”(1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_丹曲,朱悦梅;
[4]、《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_朱丽双;
[5]、《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_德吉卓玛;
[6]、《藏传佛教寺院考古》_宿白;
[7]、《浅析早期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风格及其特征》_白日·洛桑扎西;
[8]、《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_张亚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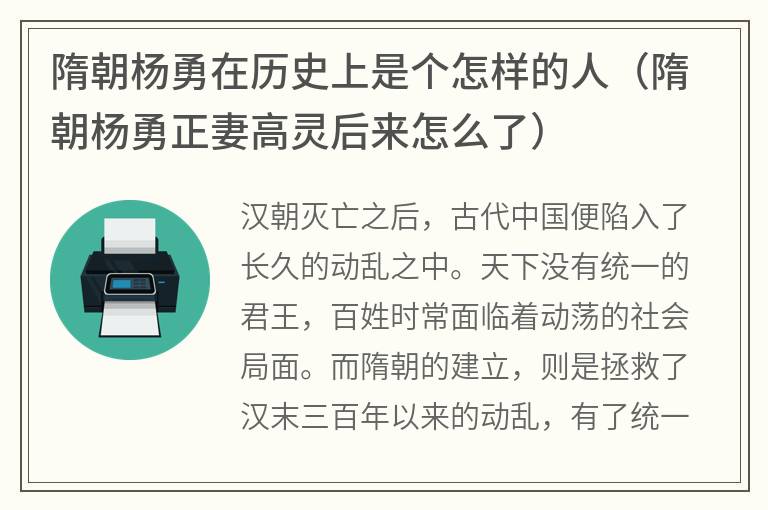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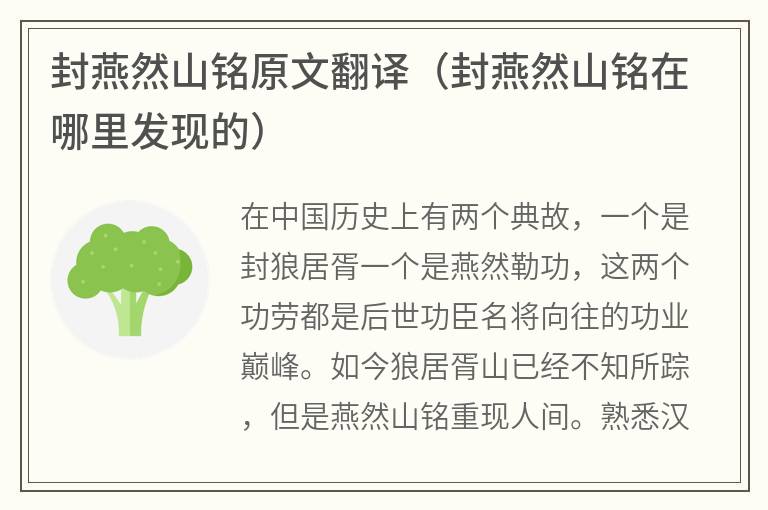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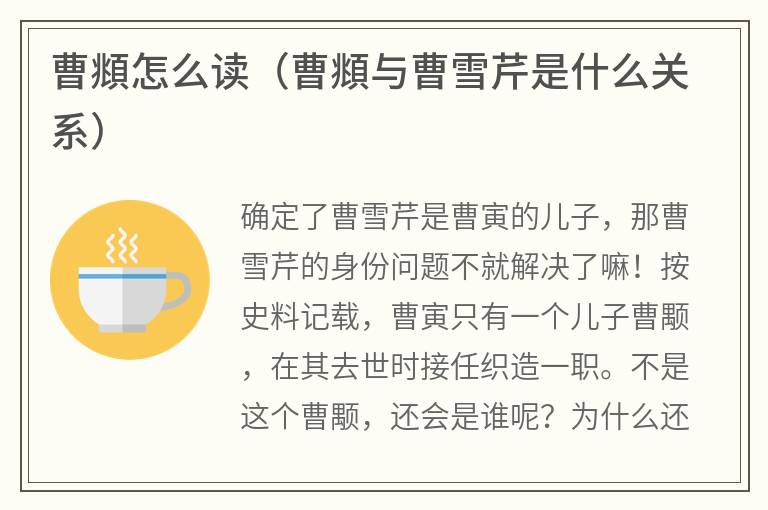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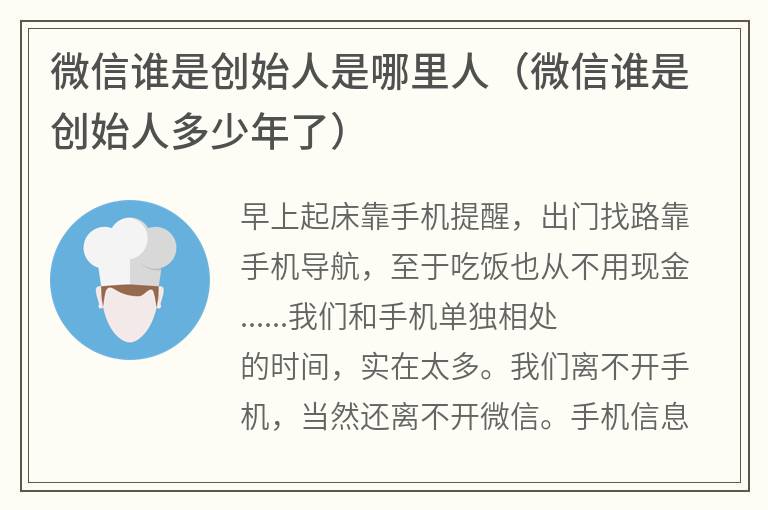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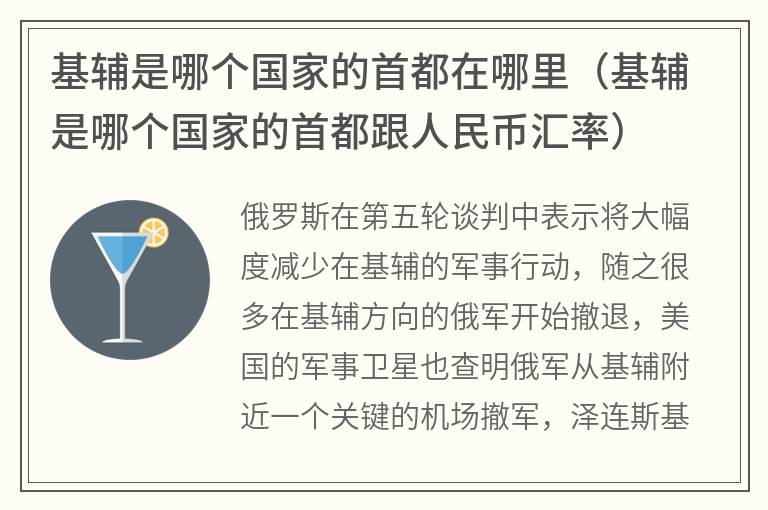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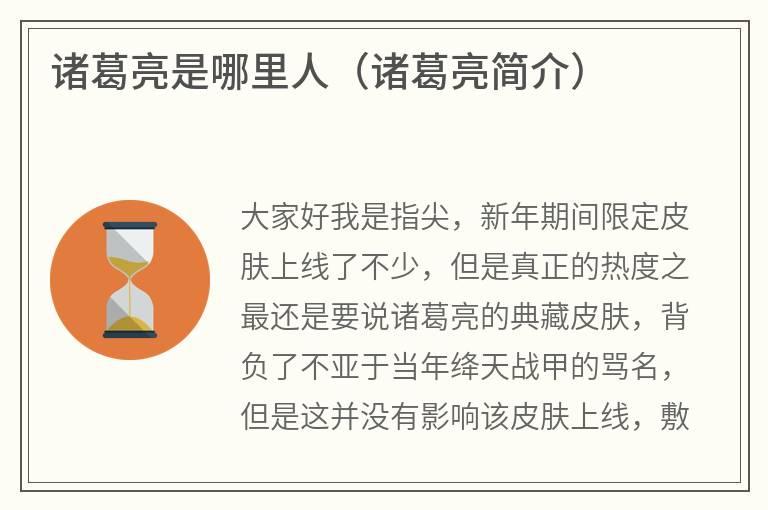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