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三生”(前生、今生、来生)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人就是活一辈子,其差别只不过是寿夭不同而已。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人们的思维便突破了现实人生的囿限,有了“轮回”“三生”的观念和信仰,于是中国人便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类的玄妙问题。
由于性格中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古人对于“三生”的探索,以立足于当下,对今生今世的思考居多。他生难卜,古人对后身的思考和表述很少。前世茫茫,但古人笔下却不乏对“只我前身是阿谁”的回答。尽管言人人殊,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认定杜甫是自己的前身。
杜甫字子美,由于一度在长安城南少陵左近居住过,所以自号少陵野老。杜甫诗才卓尔不群,诗歌成就登峰造极,但吊诡的是唐人不学杜诗,直到北宋年间苏轼、黄庭坚等人登上诗坛,杜诗才为人们所推重,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能把诗歌写得像杜诗,也成为了文人的梦想。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宋代诗人王禹偁就认为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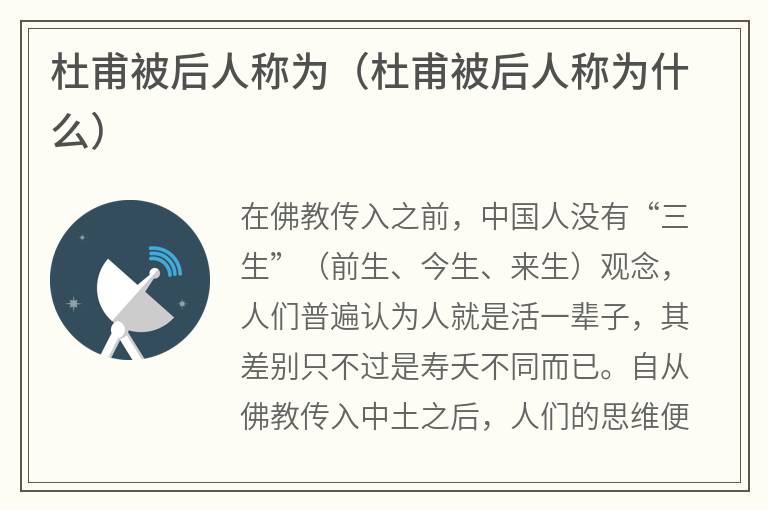
杜甫被后人称为(杜甫被后人称为什么)
王禹偁字元之,据《蔡宽夫诗话》记载:“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谐,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得易。”
王禹偁效法白居易平易诗风,也受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影响,写过一些具有现实性的诗歌,但是他对于自己不期暗合杜甫诗意且惊且喜,并申明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需要指出的是,诗歌本是性情语,而人心攸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言之”,其实是很正常的。杜甫让千古文人竞折腰,清代诗人李调元也曾经说过:“少陵疑是我前身。”这种表述与王禹偁如出一辙,堪称王禹偁的嗣响。
文人除了声称自己前身是杜甫之外,还有认定别人前身是杜甫的情况。苏轼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组诗中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牂欲上惊崷崒。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在苏轼看来,许多人学杜甫只得到皮相,孔毅父却深获其神髓,信手写来都是天然的好诗,所以他认为杜甫就是孔毅父前身。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他在《观崇德君墨竹歌》中说:“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黄庭坚一辈子对杜甫最为推崇,学杜勤下功夫,并有将杜诗“点铁成金”、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心得,元代诗人方回就曾经说过,“山谷诗本老杜骨法”。正因为如此,时人认为杜甫是黄庭坚的前身;而读者不难感受到的是,黄庭坚对被目为杜甫再世颇为自得。
南宋诗人刘应时虽把杜甫视为陆游前身,但立论角度却不同。他在《题放翁剑南集》中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表面上看,刘应时认为陆游和杜甫一样忠君爱国,无终食之间违之,所以把杜甫视为陆游的前身。其实从七言律诗发展流变史上考察,刘应时的说法也有道理。
诗的历史和诗的影响无法截然分开,面对光焰万丈的前辈诗人杜甫及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诗歌史上后来者的陆游,无疑饱受了“影响的焦虑”。杜甫的影响于陆游而言,既是一种负面压力,也是一种正面激励。陆游通过深入生活、广泛师法和点化修正,将自己从“影响的焦虑”中摆脱出来,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自己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七言律诗“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陆游成为了继杜甫、李商隐之后七律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刘应时视杜甫为陆游前身,可谓歪打正着。
有道是“子美集开新世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巨擘,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后人追摹的经典,影响至深至远。诗人把自己的前身纷纷追溯到杜甫身上,这一有意味的现象,既表明了诗人对杜甫的推崇和服膺,也无疑是杜甫的无上光荣。
◎本文原载于《文摘报》(作者朱美禄),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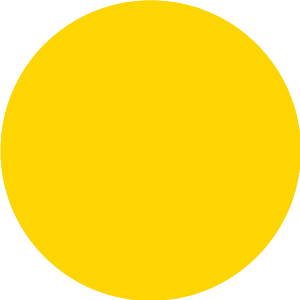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