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儿时刚会说话,父亲就教我三字经。于是我就记住了“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关于古人“席地而坐”的教诲,已深入我的骨髓,滋润着我的血脉。
雁北的席子是铺在炕上的。我常常想,若古人的席子也铺在炕上,则一定“席炕而坐”了。诚如丹青先生所言,当初开国大典时,伟大领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如椽巨手;如果他老人家是站在大前门上,后来那首歌必定是《我爱北京大前门》了。
记得父亲还给我讲过“割席断交”的故事。及至成年,始知此成语源于《世说新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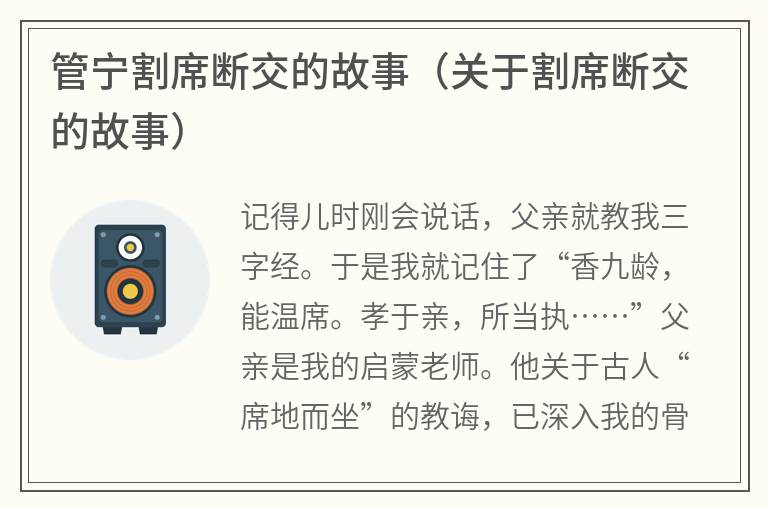
管宁割席断交的故事(关于割席断交的故事)
华歆的修养远远超越了管宁。但更多的人记住了割席的管宁,却忘记了华歆是大隐于市的率真雅士。
昔日雁北有家暖一盘炕之说,足以说明火炕在家中的作用和地位。雁北还流行一句老话:“炕上席,脸上皮”。进了家,墙面雪白,炕围子色彩斑斓,再加上一领展油豁水的炕席,脸上自然就有光彩。家里来了客人,就能喜笑颜开地拍拍炕席往炕上让,因有“让席”一词。反过来,若无炕席或者炕席破烂的人家,那就没有脸面、惹人小看。
不铺席的炕叫“光炕”。直到六十年代,得胜堡家庭条件差的人家还有用草汁蛋清抹炕的,还有些人家用洋灰袋子糊炕。那时形容某人家境贫寒,会说“炕上连领席都没有”;形容年景好的时候会说“今年能置上炕席了。”可见炕席之金贵。
昔日雁北迎娶新人,要置新席子。按雁北婚俗,不光新房里要铺新席,迎亲时男方还必须给女方家买一领新席带上。因为媳妇小时候给岳母家尿烂了一领席,送席子是新郎对新娘家的感恩与补偿。雁北有歌谣:“八个馍馍一只鸡,光棍今天要娶妻,千万要拿一领席。”现实中就曾发生过,新郎娶亲忘了拿炕席,岳丈不给开门的先例。
雁北有句俗语:“进门三相,相了锅台相炕”。六十年代,五台洼有父女俩来得胜堡相亲,经媒人相互简单介绍后,男主人热情地把父女俩让到了炕上,女主人忙着递烟泡茶。闺女问了一声“大姨好”,女主人喜得合不拢嘴,忙答应“好!好!都好!”
那闺女不高不矮,两条麻花辫子透着秀气,白净的脸庞显露出几分红润,让人感觉一定是个知礼、持家的好媳妇。时近晌午,女主人准备生火做饭,此时父女俩执意不肯,说家里还有事,等一半天即给他们回话。
次日,媒人传话说,闺女看来很乐意,主要是她爹没相中。说什么没见粮,没见草,炕席旧得变了颜色,还打了好几处补丁。好好的一门亲,就因为一领席给闹黄了。
高粱席一点也不结实,炕头、炕沿的地方最容易损坏;炕里头、盖窝垛底下则好些。炕头的席子最怕炕热烫糊了,一发现炕头太热了,就得赶紧卷席子。为了多用些时候,人们过一阵子就会把炕席调个个儿。孩子多的人家,炕席更费,娃娃整天红打黑闹,又不脱鞋上炕,几个月工夫就烂了。
穷人家席子烂了往往不能及时换,多数用旧布刷上浆糊糊一下。旧席子换下来也舍不得扔,遮盖粮食、草垛,或剪取能用的部分糊成笸箩。
舅舅家孩子多,娃娃们有时在炕上争抢东西,一个不留心,炕席上尖利的篾条就会刺进肉里,让人钻心地疼。这时就要赶着紧用缝衣裳针把篾子挑出来,不然的话被刺的部位就会红肿发炎,甚至化脓。
据妗妗回忆,表弟刚满月的时候,躺在炕席上,身下垫着一块尿布。一天,趁他睡觉的时候,妗妗忙着做饭,正在紧要关口,表弟醒了,见没人理,大哭。等母亲急三火四、洗净手过来的时候,表弟已经哭得昏天黑地,两只小脚在炕席上乱蹬,两只脚后跟都在淌血。这次流血事件之后,妗妗领教了他的脾气,再也不敢怠慢他了,凡事总让他三分。表弟在家里的地位一直比较高,与那次流血事件有很大的关系,也算杀开了一条血路。
最好玩的是,夏天穿得薄,在炕上坐久了,或者睡着了,子上、脸上、胳膊上,都会印上红红的席花。半天下不去,痒痒地不舒服。
儿时得胜堡的娃娃打闹时常喊:“你二姨,花肚皮,半夜起来挠炕席。”说明其二姨睡觉不铺褥子,半夜醒来,一模肚皮,上面都是花纹。感到奇怪,再用手摸一下身下的炕席,才释然。因此这里不应该说“挠”,应该说“摸”才精准。
不懂事的孩子们吃饭,抛洒得到处都是。稀粥、菜汤、馍馍渣掉在炕席上,用笤帚一忽拉,有些就进了席缝里。还有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一不留神便屙尿在炕席上,常常让人无计可施。日子久了,炕席就脏乎乎地惹人见笑。得胜堡人清理炕席,有个高招。就是把萝卜礤成丝撒在炕席上,用手按住萝卜丝在炕上揉搓。你还别说,三下五除二,就能把那层黑乎乎的污垢清理得干干净净。
得胜堡的女人们,常把用报纸或者旧书剪成的鞋样压在炕席下。有时一毛两毛,一块两块的零花钱也被藏掖在炕席下。时间长了,当一些东西找不到时,女人们常会提醒:撩开席子看看哇。经常撩开席子后,不见的东西果然找到了。那时,许多人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将钱呀,各种票据呀,信呀什么的,顺手压在炕席底下。小偷好像已经谙熟了人们的这种习惯,进屋后会首先撩起席子,寻找是否藏有值钱的东西,而那些马大哈们一般不会让小偷失望。
雁北过年讲究除旧布新,腊月二十三祭灶后,新刷的墙贴上两张年画,再加上一领新席,整个屋子就焕然一新。家境困难的人家即便有一领新席,也仅在过年时铺几天,过完年又将旧席换上了。一领新席能过好几个年,直到旧席实在不能用了才换下。
乡间的娃娃,学数学也离不开炕席。有一道智力测验题:“进门就上炕,炕席比炕长一丈,炕席叠回来比炕少一丈,问炕席和炕各多长?”答案:炕席四丈,炕三丈。
得胜堡人称上事筵为“吃席”。一日,一人赴筵归来,邻居老汉问他:“你宅是闹甚圪来?”答曰:“我去堡子湾吃席圪来。”
“吃了多少?”
“人老了,吃不多!”
“吃了有一领?”
“圪泡!我又不是一头驴,能吃一领!”
然后俩人哈哈大笑。
炕席咋就论领?不才至今也闹不机明。
雁北有许多有关炕席的故事:五六十年前,一寡妇带着十七八岁的闺女走亲戚,因路途较远,夜里投宿客栈。那个客栈极为简陋,隔墙是用炕席糊上泥巴做成的。因为年深日久,已有些残破。那天夜半,隔壁一汉子从墙缝里瞅见是母女二人,且闺女紧挨隔墙睡。那汉子顿时色胆包天,扣开一个窟窿,把阳物伸过来想占便宜。闺女梦中感觉子上有异物碰撞,转过身来只见一物一柱擎天傲然翘立,讶然间急速摇动熟睡中的母亲,汉子慌乱中将阳物收回。寡妇惊醒后异常恐慌,寻思了一下就与闺女换位睡眠。须臾,阳物再次探入,寡妇此时已有心理准备,激愤之余一把抓住。汉子一紧张射了寡妇一手,借机将阳物抽回。此时,闺女询问母亲:“刚才那是个甚啦?”寡妇虽然心知肚明,却说:“是个大耗子,差点被我逮住。不过它也活不了了,脑袋都叫我捏塌了,脑浆也攥出来啦!”
民国时,有一位老中医为一名热感风寒的病人诊病,开的方剂里有麻黄六钱。病人连服两剂都没效果,于是麻黄增至十二钱。再次去抓药,病人服后仍未发汗,第三次医生把麻黄加至二十四钱。第一、二次家属抓药都是在堡子湾一家小药店,第三次才换至大同一家大药铺。病人服药后大汗淋漓而亡,人命案惊动了官府。警察从前两次的中药残渣中找到的麻黄,竟然是用炕席铰成小段冒充的,只有最后一次抓的麻黄才是真的。后来,药店和那个老中医都被惩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广东的古董商来雁北收购古董。为了方便收货,他长期租了一间农村老汉的厢房作为晚上歇息的地方。
那年夏天奇热,入伏后这位古董商晚上热得睡不着。晚饭后,房东老汉抱着一张席子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你今儿铺着这张席子睡,就不会觉得热了。
古董商看到席子立刻就愣住了。他反应过来后,激动地对老汉说:“这是张象牙席,属于宝贝呀。”他知道老汉不懂,立即从包里掏出五百块钱对老汉说:“大爷,我住在这儿一个月了,你们对我非常照顾,为了表示感谢,我出五百块买下这张席子吧。”老汉听完后,惊讶地看着古董商寻思:他既然肯出五百块买我这张席子,想必这张席子非常值钱。于是他拒绝了古董商,第二天就拿着席子下了大同。经过文物保护部门鉴定,这张席子是北魏皇宫里的御用象牙席。人们猜测他家祖上曾有人在宫里当差,都城南迁洛阳时,趁荒乱窃取的。
后来老汉主动将象牙席捐献给了国家。政府部门为了表彰他献宝有功,事后给了他十五元钱、还颁发了一张奖状。那张奖状老汉用高粱秸压住,钉在墙上。后来经年累月被烟火熏得漆黑,已不见本色。
那个老汉是个地主分子,后来因痨病无钱医治死了。他死后没钱买棺材,用一领旧席裹住埋了。我曾暗自想,老汉捐赠的那块象牙席,用来换一口楠木棺材也富富有余。唉,真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呀。
不过雁北人对“软埋”见怪不怪。听老年人讲,民国七年,雁北遭罕见鼠疫,死人无算,有不少村庄几近十室九空。由于死人太多,疫后收尸,多数死者无棺可殓,大都用一片破席卷了“入土为安”。小时候看的评剧“卷席筒”,就是这个习俗的诠释。命运落魄到最后就是用席子包裹灵魂,告别肉体的苦难,去极乐世界了。
“卷席筒”的鬼成精,在雁北叫“半截子蹦”,有不少人见过。却说得胜堡有个做豆腐的,人称“豆腐张”。一天,豆腐张起的很早,推车披星戴月地出丰镇卖豆腐。那天,天色太暗,他走得很小心。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个人影,他寻思那个人和自己一样也是去赶早市的,不如结伴而行。于是推着车快步往前走了几步,想追上前面的人。
追到离前面的人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豆腐张突然停住了脚步,再也不敢往前半步,因为他发现前面的人没有脑袋。不,何止没有脑袋,整个身子包裹在一个席筒中,而且走的极不平稳,像是一跳一跳地往前蹦。
豆腐张当时吓得腿软了,立马瘫坐在地上,想喊也发不出声来。
后来,豆腐张回到堡里,和人们说起此事。老人们说,豆腐张所遇见的,叫做“半截子蹦”。早年穷人死后,没钱买棺材,常用炕席一卷就软埋了。豆腐张遇到的可能是个成了精的软埋鬼。
听五舅说,那年他患伤寒,九死一生时,也曾梦到有个人拿着一领炕席来卷他。梦境中他激烈反抗,一脚把那个人踹翻,于是那个人落荒而逃了。奇怪的是,五舅醒来后大汗淋漓,顿觉身轻体快,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五妗妗说,那是“半截子蹦”来找替身,叫五舅给踹跑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炕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炕换成了床、席换成了席梦思。像幕天席地、座无虚席、席卷八荒、夺席谈经、雪天萤席、说经夺席,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词汇也只存在于词典里了,再无实物印证。
后记:
席,藉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说文》。因方幅如巾,故从巾;用来待广大宾客,故从“庶”。席本义指用草或苇子编成的成片的东西,古人用以坐、卧,现通常用来铺床或炕等。清·方苞《狱中杂记》就有席地而卧的记载。
《周礼·春官·序官》:“司几筵下士二人。”郑玄注:“铺陈曰筵,藉之曰席。”贾公彦疏:“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孙诒让正义:“筵长席短,筵铺陈于下,席在上,为人所坐藉。”《礼记·乐记》《史记·乐书》都曾记述古代“铺筵席,陈尊俎”的设筵情况。此后,筵席一词逐渐由宴饮的坐具演变为酒席的专称。
雁北人将“筵席”简称为“席”,因而有“吃席”之说。也就有了文中“吃了有一领?”之噱头。(作者韩丽明)
![焦氏故事丨[30]石寨铺焦氏祭祖发言稿 焦氏故事丨[30]石寨铺焦氏祭祖发言稿](https://miehuo119.cn/uploadfile/thumb/20240729/1722243884772_0.gif)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