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究竟有多恐怖。亲历过这场惨剧的美国人列斯特·丹尼,在战后个人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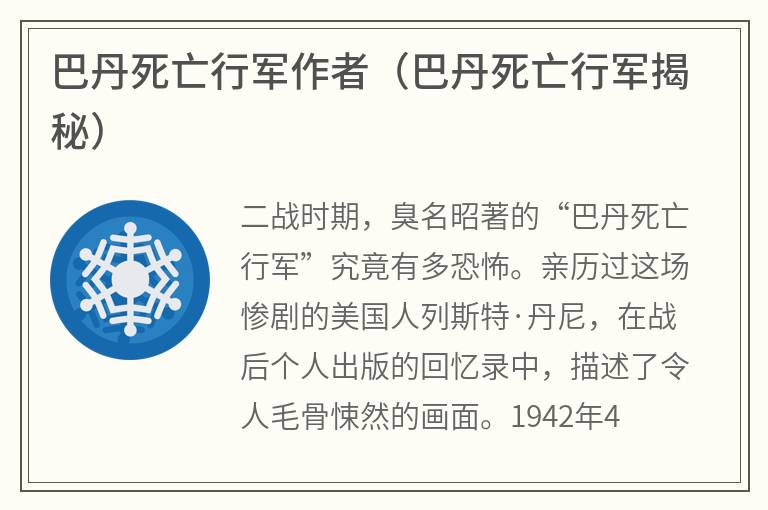
巴丹死亡行军作者(巴丹死亡行军揭秘)
1942年4月9日,白天,士兵们仍顽强地跟日军作战,夜里却受到了投降命令。要求大家将武器集中起来,不准抵抗,等待日军接收。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一阵嘈杂的喊叫声伴随着零散的枪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7、8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闯入我们的帐篷。凶神恶煞似地狂呼乱叫,其中一个日本兵将两根手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吸烟的姿势。显然,他在命令我们将香烟交给他。
很遗憾,所有的香烟全都被我们吸光了,我们用英语向他们解释着。他们却好像受到莫大的侮辱似的,用枪托、用木棍,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
我看到,有个愤怒的士兵拿起了卡宾枪,只要他扣动扳机,那些日本兵立即就会中弹倒地。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克制着怒火和屈辱,将卡宾枪放回原位。
就这样,我们20几人被7、8个矮小的日本兵肆意羞辱,一个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昨天,我们还勇敢地跟这些“黄皮肤的土拨鼠”作战。今天,我们却成了“土拨鼠”们戏弄的木偶。奇怪的是,我们居然连丝毫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显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了。
日本兵乱翻我们的物品,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完全不知文明为何物。
一个日本兵在下士劳尔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一张女人的照片,那是劳尔的女友。这个矮小猥琐的家伙,竟当场对着照片做出下流的动作。劳尔哆嗦着手,央求将照片还给自己,却被枪托重重地砸在脸上,导致他鼻梁骨粉碎,鲜血瞬间浸透了前胸。
我为了保护劳尔,上前理论,脸上也挨了重重一击,颧骨瞬间撕开一个大口子,鼻子、嘴唇也被打破。
有个士兵拿出一块巧克力,请求他们息怒。没想到这些“土拨鼠”恩将仇报,吃了巧克力后,反过来殴打这个士兵。直到将这个士兵打得趴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他们才狂笑着离开我们的帐篷。
我们的私人物品要么被拿走,要么被损坏,武器也都被带走了。我们坐下来,相互安慰着,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人会如何对待我们。
脸上的伤,不及心中的伤重,在无助与苦恼中熬过了一天。那晚,所有的人都睡不着,有人还偷偷地哭鼻子。
4月10日的清晨,又有几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闯入我们的帐篷,用刺刀威胁我们出去,却不准我们携带任何物品。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跄着走出帐篷,谁动作慢了,立即就要挨打。
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白人士兵,而日本兵却寥寥无几。如此之多的白人士兵,居然被如此之少的黄种人吆来喝去,这是多么可笑的笑话。
全体人员到位后,日本兵大声呵斥着,用刺刀朝人的身上乱戳,许多人被戳得满身是血,不住地哀嚎。日本兵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拖出来,用武士刀、用刺刀、用削尖了的竹竿,如玩游戏般,叫他们永远闭嘴。
大约上午10点左右,排好队的我们,被日本兵催促着赶路。
行军的路面,大约20英尺宽,布满了碎石子。我们被分成四人一排,不准交头接耳,将双手放在脑后,服从地朝前迈步,谁要中途停下,立即就会被日本兵拖到路边枪杀。有些受了伤的士兵得不到医治,却仍要艰难地行军,在未来的5天,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全部死在了路上。
我们连续走了五六个小时,脚底痛得受不了。炎热的天气,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散发着汗臭。由于一直没有喝水,喉咙里如同着了火似的,非常难受。
走在我前面的下士汉克,不小心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了过来,用我们听不懂的“鸟语”呵斥他。我朝汉克大声喊道:“快起来,快起来。”
但一切都太迟了,那个日本兵怪叫着,将刺刀插进了汉克的胸口。可怜的汉克,在挨了五六刀后,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鲜血浸透了他的军服,他蹒跚着走进队伍,机械地迈着步子。但他没走多远,就再次倒下了。这一次,日本兵不准他再站起来,朝他的头上开了一枪。
我看到,那个日本兵开完枪后,样子非常满足,好像一个猎人捕杀到猎物似的,神采奕奕,十分满足。
汉克的死,给我们提了醒,想要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远休息”。每走一步,脚底疼得钻心。大小便全部解决在裤子里,石子路上布满了秽物。
这艰难的行军,终于在下午四点后停下了。我们背靠着背,坐在坚硬、潮湿,遍及秽物的石子路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行军的第二天,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日本兵开着缴获的美军卡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根本不在乎会不会撞到我们。
突然,前方传来了惨叫声,同时响起了欢笑声。
原来,车厢里的日本兵玩起了西部牛仔的“套马”游戏。他们将绳套朝队伍里随意乱抛,被套中的士兵继而被卡车拖走,锋利的石块将他们的肌肤割碎,绳子松开时,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喝一滴水了,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相容的…….
到了第三天,我们仍一滴水也没有得到。其实,路边到处是清澈的泉水,但日本兵不准我们喝。有人实在无法忍受,冒险冲出队伍去喝水。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脱水的人越来越多,倒下后,立即就被杀死,没有例外。
下午两点左右,一望无际的队伍在日本兵的命令声中停了下来。万万没想到,日本兵竟好心发作,允许我们喝水。
难道,他们突然同情起了我们这些可怜的白人吗?
当然不是。在路边有个大约50英尺,散发着臭气的水塘,水面上满是飞虫和发绿的泡沫。这是严重污染的水,根本不能喝,但渴急了的士兵还是疯狂地冲过去,贪婪地牛饮那些发臭的脏水。
大约5-6分钟后,一个身材偏胖的日本军官吆喝了一声,几十个日本兵快速跑过来,端起枪朝着水塘边的白人士兵射击。
我们只能看着,却不敢阻止。大家都很清楚,谁敢阻止,也会被枪毙。
侥幸活着的人,目光呆滞地走回队伍当中,他们喝了脏水,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的折磨,直至死亡……
第四天的下午,我们总算进入了巴郎牙城区。好心的菲律宾人朝我们投掷清水和食物。突然,日本兵开了枪,菲律宾人四散而逃,有几个好心人被射杀。
天即将黑下来的时候,我们被赶进一间大仓库。这里原本是储藏粮食的地方,如今所有的粮食都不见了,我们却像麻包一样被塞了进来。由于人太多的缘故,连蹲都蹲不下,只能站立着挤在一起。
好不容易捱到了天亮。当大门被日本兵从外面打开的时候,能走出去的人只剩不到一半。数百人因为缺氧而死,地上满是粪便,许多人在这种肮脏的环境里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在此后的几天内相继死去。
已经四天没有吃一口食物了,嘴巴火烧火燎,根本张不开。终于,日本人允许我们喝水了,但每人只能喝半杯,还全是浑浊的凉水。喝了水,还有一捧米饭,由于没有饭碗,所以只能用手捧着吃。在那一刻,我竟不由自主地感激起了日本人,估计当时多数人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吃完了米饭,则又要开始苦难的行军了。那些还活着,却站不来去的士兵,被丢入仓库了。然后,日本兵朝里丢了几颗手榴弹。紧跟着,大门被牢牢地锁死了!
第五天,无疑是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一天。当虚弱无力的我们走到一片满是坑穴的路段时,日本兵突然疯了似的,用机枪、用步枪、用武士刀、用刺刀、用竹矛,甚至用特制的钉棒,朝着行军队伍疯狂施虐。
这场屠杀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停止。满地全是死尸,以及伤重不起的人。日本人显然早有预谋要进行这场大屠杀,那些坑是他们早就挖好了的。
死掉的,以及尚未死掉的,一股脑地全都被丢入坑中,由我们这些虚弱的手足负责掩埋。
大约有15个还没有彻底断气的士兵,被日本人用绳子拖在卡车后面,直至支离破碎。
此后的路途中,每到一个休息点。日本兵都会随机杀掉一批人,他们杀人的花样层出不穷,甚至不乏维京时期,那些骇人听闻的野蛮手段。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娱乐。但对于我们来说,只一种难以描述的恐惧。
这一幕幕惨状,一桩桩悲剧,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
(列斯特·坦尼,1919年出生,巴丹行军之前,任美国驻菲律宾陆战队上士。在巴丹行军中幸运生还后,被关入集中营,从事严苛的体力劳动。直到1944年,才被盟军解救。战后,将自己的亲历以回忆录的方式出版,取名《Gohomealive》。中译:《活着回家》)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