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嗯。”“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嗯,还有什么?”“不要叫敌人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在课堂上,我问学生们如何理解水生最后说的那一句话。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这是水生要妻子守住贞操,宁死不从。学生说得对吗?我不置可否。我的提问,只是想了解当代学生对这句话的直观感受。
在备课时,我就留意到这个细节。已有几人对此发表了意见,或是或否,各执一词。
逄增玉教授在《重读》一文中,明确点到这一句话,认为其中蕴含着“守节”和“节烈”的含义。这种阅读感受与我们多数读者的感受是一致的。
逄文发表不久后,另一位作家——王士美发表了题为《质疑》的文章,明确反对逄文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挖空心思的奇思异想”,“一种荒唐的歪曲”。
在紧张的备课中,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证双方的观点,只能姑且存之。
寒假期间,我有目的地读了孙犁的不少作品和评论,心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王作家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样的立论(指逄文——引者注),首先是无据的,是虚设的。该文把抗日战士与自己亲人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的誓约与决心,说成是一种只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封建意识的“妇德”和“节烈”的要求,只能说,是一种低水准的推测和判断。
我这篇文章,就围绕着这段话,来谈两个问题:一是《荷花淀》中“节烈”的存在依据;二是如何看待《荷花淀》的“节烈”问题。

01“节烈”观的存在依据
逄文的立论不是没有依据的,其中提到了这两处:
第一处是《荷花淀》写到的。妇女们在探夫的路上,遭遇了敌人并被追赶,此时她们的心理和誓言是:“假如叫敌人追上了,那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她们的视死如归,隐含着“节烈”意识。
第二处是《采蒲台》写到的。白洋淀的青年妇女一边织席劳动一边编歌自唱,她们的唱曲中有这样一节:
我们的年纪虽然小,我们的年纪虽然小,你临走的话儿记得牢,记得牢:不能叫敌人捉到,不能叫敌人捉到!我留下清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如果说第一处尚有讨论的空间,妇女们可能不想成为俘虏被敌人套取情报;那么第二处几乎是水生嫂与水生最后话别的歌谣版,它把为何不能被敌人捉住的原因表述得更明确。
民间歌谣是平民大众传递价值观念的有效方式。这首歌谣中反复强调的“不能叫敌人捉到”,是重中之重,也是当时妇女的共识。众所周知,日军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侵害妇女;而冀中平原的形势就是敌占区与游击区呈犬牙交错之势,日军经常会出城扫荡,妇女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要遭殃。

孙犁在同时期所写的作品中,有多处直接或间接谈到了日军给妇女带去的性的威胁。
在《芦苇》中,“我”遇到了在芦苇丛中躲避日军扫荡的两位妇女,一位三十好几,一位十八九岁,其中年轻的还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当年长的认为面对日军小刀完全不顶事,年少听了只是“凄惨地笑了笑”。凄惨地笑,这是多么悲凉而无奈。
在《游击区生活的一星期》中,一个村民给“我”讲了个节烈鬼的故事:鬼子要侵犯一个挖沟渠的年轻媳妇,那年轻媳妇宁死不从,被逼得跳井自杀。那天晚上,敌人的炮楼就闹了鬼,那些鬼子都不敢在村子周围的炮楼住下去。这个节烈鬼的故事,掺杂着封建礼教与坚决抗日的多重想象。
在《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中,船夫给我讲了红衣少女扔手榴弹炸鬼子的传奇故事,他最后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
不厌其烦地列举上面这些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日军带来的性威胁,是妇女们无法回避的噩梦。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就要避免被敌人和汉奸活捉,甚至要以死相搏,这是当时妇女的共识。(当然,现实中也有人默默忍受活下去的,不对前人的选择作评价)
“节烈”观念的存在,并不妨碍白洋淀的水生们和水生嫂们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相反,“节烈”的存在,让“同仇敌忾”之“仇”更加明确,让宁死不屈更多了一份理由。至于对“节烈”存在的推测,更不涉水准高低。处在战火之中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伟光正”的英雄画像,借着政治正确无限拔高历史,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贻笑大方的“抗日神剧”。

02 对“节烈”观的反思
以前,贞节牌坊是士子文人所鼓吹的;如今,节烈在文人笔下已不受待见(生活中可能又是另一回事)。王文措辞如此激烈,很大程度上是被“节烈”点爆的。
20世纪的中国,关于节烈最有名的文章便是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逄文与王文都有提及。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成果,是对封建社会节烈观发出的一篇檄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断定“节烈”这事是:
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于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对于历史上那些节烈的女子,鲁迅是予以同情的。她们上了历史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
不对妇女提节烈的要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新道德之一,也是剥除男权解放女性的重要一步。
如今,“节烈”在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王文就用“虚伪”、“自私”、“残忍”这些词来形容封建的“节烈”观念,而当有人把“节烈”这样的字眼安在孙犁的《荷花淀》头上,是可忍熟不可忍。(孙犁的《荷花淀》在王文那里似乎已经神化。)

从传统道学家的神圣化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污名化,“节烈”的真实面容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抛开男性的权力文化,我们应该还要思考:节烈这一行为对于受难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难道纯粹是他者赋予的?
在历史上,每逢外族大举入侵之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奸淫掳掠之事,妇女是这一劫难的主要受难者。为了逃避即将遭受的巨大的身心创伤,投井上吊就成为一种消极的解脱之道,就好比陷入包围的士兵为了不被俘虏受刑,也可能选择饮弹自尽,两者的行为动机有一致的地方。撇开“国仇家恨”与“贞洁烈女”的修饰,“节烈”首先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苦难”。(“苦难”不仅是侵略者带来的,也是统治者描绘的。)
正因如此,作为自保行为的“节烈”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无论男女,都有选择逃避不可承受之“苦难”的自由。只是,在被意义编织的社会中,本能的自保的“节烈”往往被遮蔽,有人看见的是“国仇家恨”,有人看见的是“贞洁烈女”,连当事人也自溺其中。
在《荷花淀》这样一个以冀北为故事背景的抗日小说中,水生最后的嘱咐,既可以说是“节烈”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同仇敌忾”的期望,两者可以共存。需要区分的是:“节烈”是当时游击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同仇敌忾”则是抗日小说的政治要求。
无论是水生这一人物,还是创造水生的孙犁,都带有男性中心的世界观。1952年,孙犁收到一封由某师范文艺小组写的信,信中对《荷花淀》提出了三点批评:一是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二是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的牺牲品;三是不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孙犁对信中的所有批评都予以否定,然后以《关于小说的通讯》为题发表出来。很快,孙犁被群起而攻之。(感慨:1950年代的县城学生,都已有了如此强烈的女权意识)

以我来看,当时学生所提出的某些批评,确实存在小题大做,钻牛角尖的情况;但在批评的大方向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孙犁的解释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但也存在强辩的,以势压人的情况。
比如说,在伏击战斗结束后,水生说水生嫂们是“一群落后分子”,这句话虽然带有意气的味道,但却足以反映男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男性往往比女性更进步。包括小说的结尾,女性也是以男性为追赶目标来操练射击的。联系孙犁的其他抗日小说,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好女人跟好男人走,好男人跟党走,政治是爱情的道德。
孙犁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角,但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男性的审美视域中的,是从“香草美人”的传统中绵延下来。前后变化的只是看的对象:从秦楼歌女转向乡野村姑。
不过,这一转变足以引起文化官员的兴趣。1947年,周扬编《解放区短片创作选》时,就收录了孙犁的《荷花淀》。周扬在序言中对这些作品予以赞赏,因为它们“究竟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水生嫂们翻生做主人,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确实算得上历史地新人物。但与此同时,其中也有旧的文化元素渗透,历史上的“花木兰”与“杨门女将”,已经成为女性抗击异族侵略的传奇符号,而这一符号在民间社会是广为流传且被认可的。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革命文艺被要求协助革命工作,文艺的“普及”工作要优先于“提高”工作。普及,就意味着要更大程度地照顾工农兵大众的现有认知,要更好地利用已有的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
在这一“接地气”的过程中,一些传统观念甚至封建遗产也融入到新时代的革命文艺中。封建的“节烈”观就混杂在民族大义中得以复生。
在革命文艺的民间传播过程中,这种似曾相识的封建遗绪,成为农村大众接受新思想新指示的有效通行证。人们在对贞洁烈女的自我感动中,也接受了民族大义的熏陶。
可惜,这一过渡性的产物,终究只是时代的权宜之计。如果不及时地剥离掉其中的封建残渣,封建的那一套东西终究会死灰复燃。发生在1950-1970年代中国的某些事,是一个明证。如李泽厚所说,我们太过提防“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却忽视了“封建主义”的借尸还魂。(大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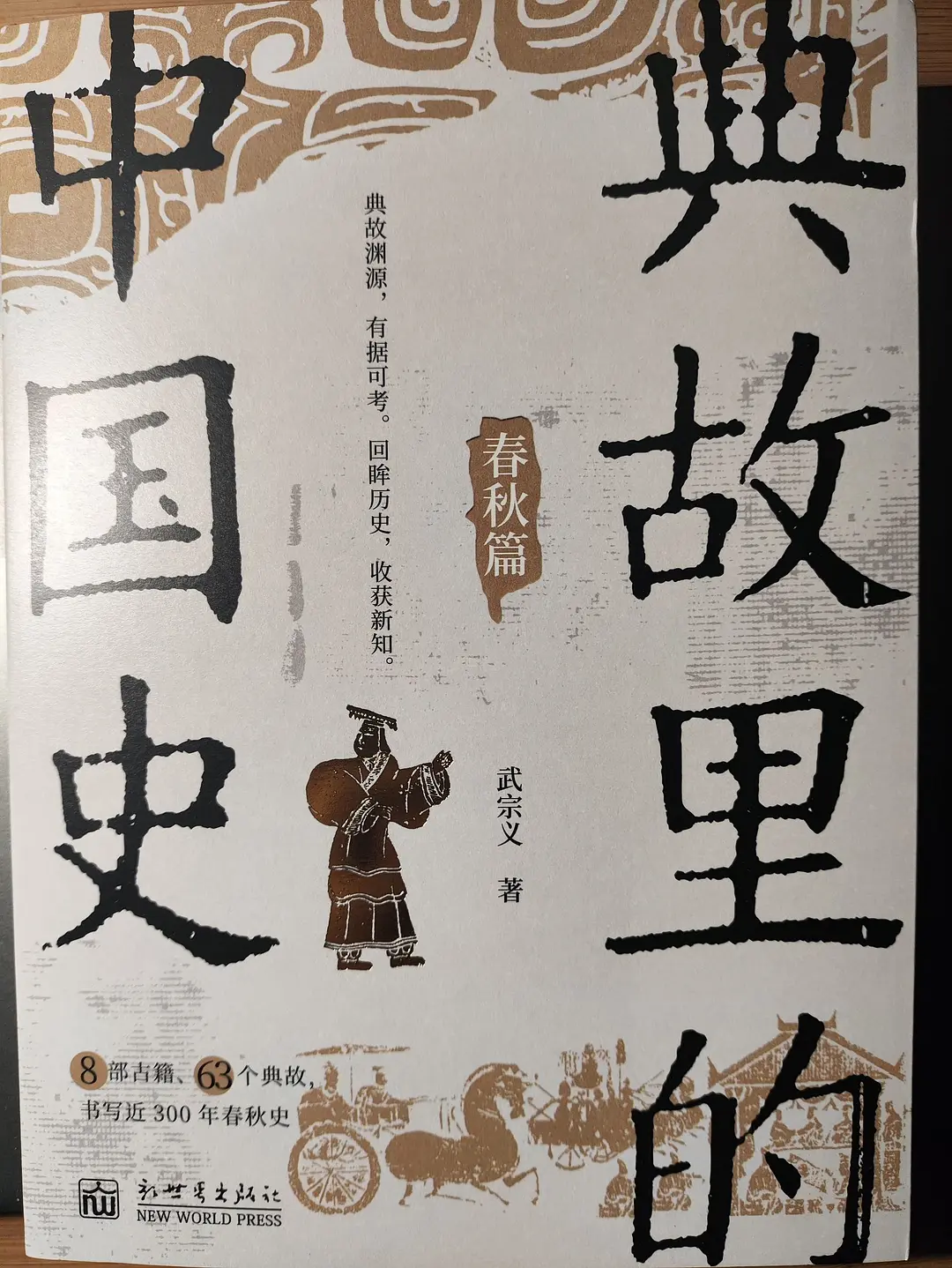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