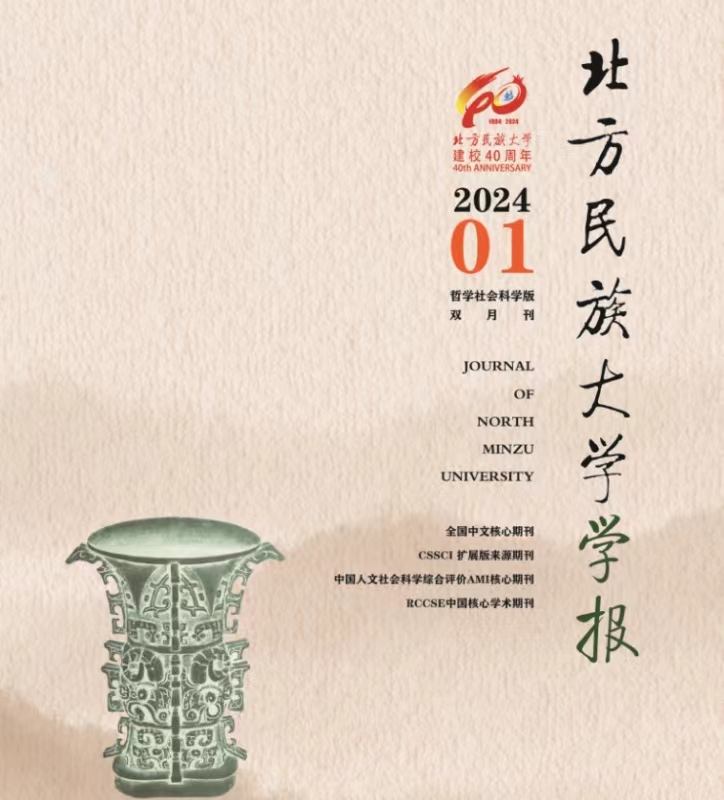
【作者简介】杨亚雄(1984—),男,甘肃礼县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甘肃省民委委托项目“甘肃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2023-YJXM-16);兰州理工大学红柳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
【摘要】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统合”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的发展历程,任何共同体的繁衍生息都会形成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历史记忆。“共同的记忆是共同体共有的、在一个群体或集体中大家共享、共同传承并共同建构的事或物,以及由其所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世界。”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承的国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大量记载我国各民族灿烂历史的史书,如“二十五史”对各民族的态度实际上是认同祖国各民族同种、同宗、同血脉、同姓的表现,反映出历史上各民族相互的认同传统。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书写的历史,各民族在共创中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各民族凝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目前,关于历史记忆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历史记忆概念解析以及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关系等方面,尤其是对后者的研究较为热烈。如有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历史记忆是凝聚族群认同的纽带;也有学者将共同历史记忆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中加以研究,认为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要素。总体而言,将历史记忆视作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基础是当前学界对该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到底共同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前者在后者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目前学界在此方面的关注似有不足。本文拟从共同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入手,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基础上形成的“统合”记忆为视角,探讨共同历史记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一、共同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性的存在,在其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记忆是其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特征之一。“正因为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才能在5 000年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可以说,历史记忆记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足迹,也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因此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证据。
一般来说,族群的历史记忆属于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记忆主体对过去事件的集体感知和反思,并将其投放到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共同体的共同记忆实质上是诸多集体记忆的整合。对此,麻国庆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各民族集体记忆的整合(交集),“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每个民族根据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的区域社会环境,形成了民族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多样化的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中整合出各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的集体记忆,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上位共同体的历史依据。
共同记忆的延续和流动,在很多时候是中华民族实体在自身发展实践和社会有序变动中的无意识过程。当然,在激烈的社会变迁时期,共同记忆会因为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被有意识地激活和唤醒,甚至还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创新和创造。事实上,无论是无意识的流动,还是有意识的复活,共同历史记忆一直处于个体与集体变迁的动态中,并随社会流动而不断传承。因此,共同历史记忆并非静态的存在,它根植于共同体的发展进程,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它不断强化和巩固着共同体的聚合力。总之,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和交融而最终整合而成的所有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时空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因为有各民族共享的历史记忆才得以被广泛理解和普遍认同。
实际上,共同历史记忆中已经包含着对国家的认同意识,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华文化在共同体及其成员间的代际传承,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记忆的激活和重现来实现的。另外,历史记忆并非仅强调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指向自我或他者对历史的认知或态度。因此,中华民族在“三交”基础上形成的“统合”记忆就成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基本依据。
中华民族“统合”记忆的传承使中华各民族凝聚起普遍的共识:统一比分裂更得人心,大国比小国更能抗压,强国比弱国更有力量,富国比穷国更受民众爱戴。因此,无论是哪个民族在中国建立王朝或政权,都在“统合”的历史记忆基础上认识到“大一统”的正确性,都把“大一统”思想视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全面落实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实际行动中;无论中华民族内部曾经有多大的分歧和不同,但在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华民族的“统合”记忆均会被激活和放大,并转化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心灵的原则,是人的本质意志的特殊标志。随着共同历史记忆不断被激活和重复呈现,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这个各民族共有的民族实体之认同也不断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也随之不断增强,最终各民族共创而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联结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是每个中华儿女最为持久的思想共识和情感共鸣,是对自己“中国人”“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定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可。一言以蔽之,共同历史记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对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华民族的“统合”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它既是客观史实,也属于观念范畴。在中华民族诸多历史记忆中,既有能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正向记忆,也有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负面记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质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修复完善,正本清源,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导向,归纳整理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在“三交”基础上形成的“统合”历史记忆就是正向的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之典型。
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一部中华各民族通过不断“三交”而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统合”与“分化”交替呈现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统合”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趋势的不断增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史实的传承以及中华儿女对该历史事实的认知和态度,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统合”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就是在长期“统合”记忆的传承中不断积淀和凝聚力量,最终形成了稳固的民族共同体。
(一)秦朝首次一统天下,“统合”记忆格局基本奠定
公元前221年,秦国攻灭六国,统一天下。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始于秦朝。秦统一六国后,实施了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管辖体制,建立了促进文化交流的统一文字书写体制,修建了有助于各统辖区域之间交通往来的统一官道,制定了促进经贸交流的统一度量衡。秦朝“大一统”的制度设计有力地将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统一起来,形成了统一的生产生活体系。自此,“以古华夏族为核心,在包容了众多少数民族后,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浮出了历史的地平线”。尽管秦朝的存续时间不长,但这些“大一统”的举措,无论给当时和后世的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心里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统合”印记,以至于后来在改朝换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把实现和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作为毕生的追求和努力目标。“虽然从秦代至于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间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秦朝的一统是中华民族“统合”史的重要开端,由此,“统合”思想基本形成,“统合”记忆格局基本奠定。
(二)汉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统合”记忆根深蒂固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封建“大一统”王朝,开放进取和繁荣强盛是它留给后世的主要印象。在民族关系方面,与秦朝相比,汉朝的民族政策更为包容和有力。自汉武帝始,在同匈奴对峙甚至战争角逐之后,汉朝选择了同势力遭到削弱的匈奴罢兵言和,和平共处。这些“统合”的制度安排,使得汉朝得到当时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可。与汉朝相比,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各民族“三交”更加普遍,中央政府对边疆事务的管理更加自信和完善,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统合”质量较之以往更高。有唐一代,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带来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疆土拓展以及“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交融,成为人们对唐朝最持久的“统合”记忆。“唐朝时期的各民族关系基本上已是政治一体、经济关联、文化融会贯通的关系,即多元一体关系,这就是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已基本形成。”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对“统合”的认知,人们对“统合”记忆也因此根深蒂固。
(三)元清两朝的“大一统”实践,“统合”记忆融入各民族血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建立“大一统”王朝所展现的示范效应,以及元朝的“统合”实践均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元时超大的国家版图是这个王朝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历史记忆。清朝作为继元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统合”质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王朝。国家疆域的底定,边境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制度的实施,“康乾盛世”的出现,使得1840年之前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统一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清朝再次强化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印记,“统合”记忆已经完全融入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
由于中国古代各民族频繁的“三交”实践,使得各民族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凝结和聚合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以“统合”为主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要思想认知。当然,这一认知是经过历史的发展和积淀而不断形成的。谷苞先生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这一历史传统源于中华民族对因统一带来和平与盛世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代代相传,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知逻辑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正是在不断呈现“统合”记忆的基础上,“继承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使‘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由古代发展趋势变为现实存在的事实”。因此,传承并落实“统合”历史记忆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的宗旨。
中华民族的“统合”记忆是我们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依据,因为它最持久、资源最丰富,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的作用,挖掘和整理古代中华各民族在“三交”视域下的“统合”记忆资源,把这些共同记忆通过“历史遗存”的物化方式和“文本创作”的描述方式展现出来,让人们真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是“多元一体”,而且还是“多元一统”的客观事实,以此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统合”记忆使得中国人民开始致力于新的统合实践,各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经历,“较好地展现了中国各个民族由‘自在’区隔走向统合一体的巨幅画面”。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合”记忆再次得到了升华,成为当前所有中华儿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共同历史记忆的传承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历史记忆往往呈现出多向度功能,它不仅呈现过往,诠释共同体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更重要的是表达着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价值追求和行动信念,以强化共同体今时奋斗和未来发展的决心和力量。整体上看,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仅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友好“三交”同甘共乐的历史场景,还展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团结奋斗的感人场景。因此,目前我国56个民族之间的兄弟手足关系并非亲昵的比喻,而是客观的实存,这种关系植根于中华民族“三交”历史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统合”记忆。
(一)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历史依据
共同历史记忆是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本来渊源的重要证据。“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社会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不管承载的内容是什么,形式怎么样,最终都构成共同体成员对本群体最深沉的感情。相应地,这种情感也会不断促使共同体成员对自身本来渊源不断进行追问。
历史记忆“指的是亲历过讨论中历史事件的人的经历。更精确地说,历史记忆指的是将该经历复原和转换为叙事的过程”。因此,复原过往的经历并将其代际传承就成为民族寻根问祖、追根溯源的主要形式。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共同神话和祖先,共享文化记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民族都一直在探寻“祖先是谁”的问题,也迫切希望能得到符合自身传统和惯性思维的解答和阐释。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共同经历过什么等类似的问题,是中华各族人民对自身本来渊源最基本的追问。中国古代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始祖”做了长期探究,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祖先论”。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也有关于自己始祖的记载和传说。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记述。又如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就曾言,“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在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中,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汉族等民族被描述成一奶同胞的兄弟等。仅从这些传说和史料可以看出,各民族在祖先认同文化中表现出很强的趋同性,都呈现出中华民族祖先认同中的共同文化记忆。
除了祖先认同的共同历史记忆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追寻本源的记忆还体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符号上。以长城为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符号,长城的修建者中有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成员,这说明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修建了长城。随着中华民族“三交”的不断发展,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承担军事防御功能的长城逐渐成为促进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纽带。长城为各民族共同修建、共同维护和共同享有,它是历史上解决民族纠纷而促进民族融合的军事舞台和文化结合带。因此,长城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而是各民族共同的象征符号,它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长城一样,“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记忆符号。“在‘龙崇拜’符码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结构可以糅合各民族‘龙’符号之同质性与异质性,积极形塑与传承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各族人民对“龙”的记忆呈现出更多的趋同性,“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始祖认同之记忆符号。
在“三交”基础上形成的“统合”记忆旨在告诉今天的中华民族所有成员,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实体的形成及其历史经历是关系到民族本源的重大历史问题。可以说,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和“魂”,是人们在过往的历史画卷中追寻自己的情感归属,寻找自己之所以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主要依据。
(二)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
共同的历史记忆能转化成共同体成员共同奋斗的实践动能。如果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记忆缺失或断裂,那么该群体就难以存续。反之,有了明晰和强烈的共同记忆,尤其是那些物化记忆的重复闪现,会激发共同体成员承继历史传统,为共同体的整体发展而不懈奋斗。
在共同记忆中,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体系化、立体化、官方化的,有些记忆呈现出零星化、碎片化、民间化特征。如果将这些记忆进行凝练和总结,总能得出记忆的主线,“统合”就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主线。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成为今时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力。
“统合”记忆之延续,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反对民族分裂,追求团结统一的信心和决心。中华民族历史上,虽然在政治图式上不时有短暂的“分化”,但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分裂”,是分而不裂。“分”不是最终目的,“分”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的更强大的“合”的因子,“分”是为实现新的“合”而积聚力量。每一次“分化”都为下一次的“统合”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促进更高质量的大一统。即便在“分化”时期,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仍没有中断,反而彼此接触的程度更深。如宋朝和吐蕃之间的茶马互市并没有因为彼此之间的对立而受到根本的影响,以至于“茶马古道”的物化记忆一直留存在古道沿线汉藏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不仅如此,在“统合”记忆的激励下,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伟大实践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也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广西壮族的瓦氏夫人亲率队伍到浙江嘉兴地区抗击倭寇的壮举成为广西各族人民争相传承的历史记忆,也成为抗战时期“广西军”英勇顽强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反分裂、求团结的历史传统绝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千年来的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源于中华各民族对不义之战的深恶和对无名之乱的痛觉。人们之所以支持和追求“统合”,就是因为在“大一统”国家里,会长期出现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和平以及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盛世。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皇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在“统合”时期出现的。人们追忆这些“盛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今时国富民强的夙愿,而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这一愿望实现的前提。
“统合”记忆之流动锤炼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和坚强意志。曾几何时,富强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向世人展现的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特征。当然,中华民族的富强是各族人民用艰苦奋斗换来的,人们在不断缅怀历史上创造富强成就的先辈们的同时,还憧憬于民族富强的永远持续。这种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曾经既富又强的国家从此变得又贫又弱。列强的枪炮声逐渐将停留在“盛世”记忆中的中国人民惊醒,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及重现记忆深处的荣光,各族人民毅然团结起来,开启了求富求强的奋斗历程。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英勇拼搏,披荆斩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在“统合”记忆的促动下,各族人民求富求强的感人实践锤炼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意志,促动着中华各族儿女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三)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共同历史记忆并非静态的尘埃,而是鲜活的力量,它昭示着对未来的展望,形成了中华民族实现未来发展的不竭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统合”记忆之所以持久且稳定,就是因为人们时刻没忘记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太平盛世和国富民强。这一记忆使人们认识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和平、盛世和富强的保证。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实现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以极大的启示。“统合”的历史记忆告诉人们,中华民族的内部纠纷和矛盾只有靠中华儿女本着互尊互让、互敬互爱的原则自己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够从历史中一路走来,而且越行越稳健、感情越来越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一统”描述的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平面,而是一个集时间、空间和人伦等多向度的向心式的“球形系统”,各族人民因“三交”而形成的持久“统合”历史记忆占据着这个系统的核心体位。因此,不管外部势力如何挑拨和污蔑,中华民族维护内部团结和追求国家统一、世界和平的意志不可动摇。
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之所以鲜活感人,是因为人们没有忘记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发生的民族危机。这种记忆使得今日的中华儿女格外坚强,对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更有信心和决心。在当前“两个大变局”背景下,面对某些国家的抹黑、遏制和围堵,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历史记忆驱动着所有中国人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而自强不息、英勇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各民族共同抗敌的历史记忆时刻唤醒着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民族意识,因为历史上有共患难的经历,各民族会时刻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华民族不断消除内忧、解决外患的斗争史永远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实现更大宏伟目标的力量源泉。“民族当了危难之际,要靠民族本身之力量以奋斗,民族之奋斗力与革命力,是互为因果的,没有奋斗力与革命力,合成为主流的力量,则民族也不会复兴。”长期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如饥饿和贫穷记忆的激活,使人们更加追求和珍惜温饱、小康以及更加富裕的幸福生活。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会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勇敢奋斗。人们对民族英雄的缅怀,会激发其自身强烈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统合”记忆的激活和呈现,使人们更加追求和珍惜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亦使人们更加追求民族复兴。当前,由于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全面推进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不断从各族人民共创中华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只有在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中挖掘有助于引起各族人民情感共鸣的历史记忆资源,并将这些共有的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四、结语
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形成因素,也是巩固和壮大共同体的黏合剂和推动力。中华民族“统合”记忆的形成及传承是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消失于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千年仍坚如磐石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挺过数次“最危险的时候”和“最艰难的时候”的强大动力,更是我们当前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遏制和围堵,却依然能坚挺自身脊梁、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在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的作用下,中国人民必然能够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无畏无惧地阔步挺进,砥砺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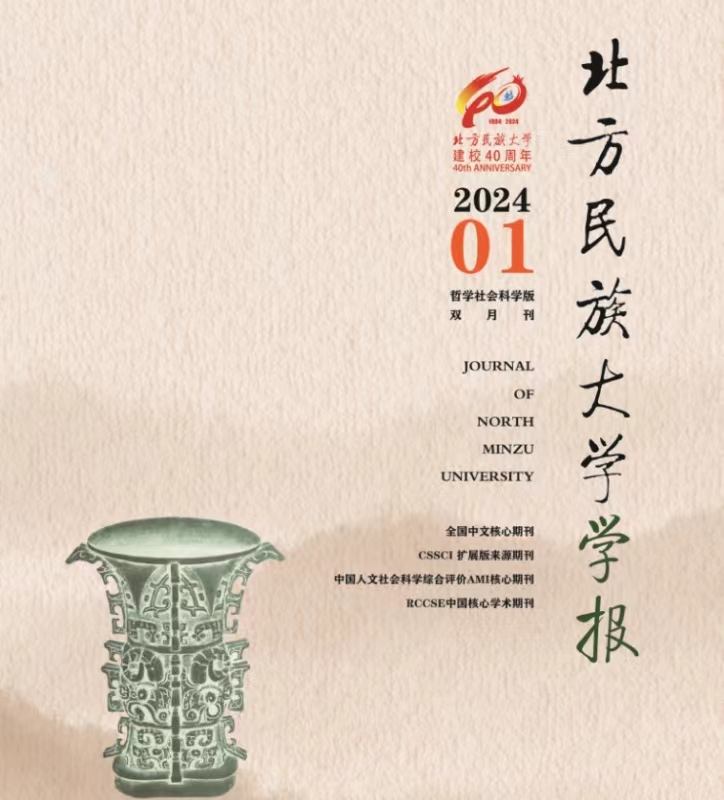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