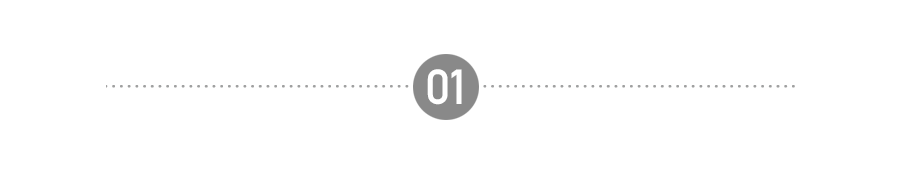
历史学家的心灵枯竭
2002年左右,43岁的李开元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时,他已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在日本就实大学担任人文科部教授,并在两年前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该书于2023年出版了增订版)。
这部倾注了他十多年心血的史学著作,在严密考证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增添统计和数据库的方法,追踪从秦末到汉武帝末年120年间的新兴军事政治集团,在历史过程中考察他们如何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功受益阶层”一说。这一概念为汉史乃至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王朝更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颇具穿透力的研究视角。该书一经出版,在中日史学界获得普遍好评,历经20年仍被视作秦汉史领域的力作。他当时设想沿着既有路径,以整个西汉王朝为对象,为两千年中华帝国史建立一个经典的解释模式。

此时,李开元却隐隐觉得自己的心智出了状况。
“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和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了。”那些历史上鲜活生动的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或者曲面上的一个个点。数据、材料、图表论述、概念,这越来越像是一种逻辑的游戏。不安和怀疑滋长,他失去了继续做研究的动力和激情,“就觉得不对,不能这么下去。”
他尝试转向历史哲学。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理论,尤其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他的《数学原理》。于是他“异想天开”,想写一本《历史学原理》。“很可怕,当时整个人完全陷落到那种非常抽象的哲学思维里面去了,思考像‘历史学第一个时间是什么’这种问题。后来才知道,凡是思考这个问题、与时间为伍的都没有好下场。”
努力以“惨烈失败”告终。其间他也完成了几篇历史哲学方面的文章,投给学术期刊后,多被退了回来,“编审们不知道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他很不甘心,改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言把这些思考重新写出来,发在自己的博客上,然而关注、阅读的人也寥寥。
最终点醒他的,是他的导师、历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
一次,李开元回母校看望田余庆。田先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如实汇报,说自己正在写《历史学原理》,在思考“历史学的时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田先生听罢,慢悠悠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随后讲了胡适晚年把全部精力投入《水经注》,一做就是十几年,一心想搞清楚清代的学术公案——戴震、赵一清和全祖望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他说,如果胡适晚年不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田先生说话是很含蓄的,他其实是在敲打我,说我再这么下去,可能是走了歪路。”
他逐渐清醒过来。刚好这个时候,他的人生也处在谷底,先是大病一场,然后回国任教的计划也遇到波折,他一个人在遥远的日本乡下居住,事业、生活方方面面都不太顺心。苦闷中,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新回顾。
他问自己当年考进历史系是想做什么?——“高考恢复后进了北大,我是决心来学习当司马迁的。”等迈进大门,他才明白:原来历史系并不培养司马迁,而历史学者也不写历史。

▲1980年,李开元和同班同学赵国华在北大26楼 图/受访者提供
“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只做研究、写论文,自己不写历史呢?”李开元曾直接或间接地向田余庆、周一良、邓广铭这三位他敬重的师长请教过这个问题。
“田先生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周先生说我们的文章就不是给普通人读的。邓先生,我不敢直接问他,但我默默关注,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是‘四传二谱’(《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他其实是写历史叙事的。”
经过一番彻底反思,他在2002年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学界主流,自我放逐,破釜沉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不管了。”他决定重新读书,重新思考人生,重新审视历史学,摸索出一种书写历史的新形式。
再次研读《史记》后,他给自己打出一面旗帜——“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为历史学收复叙事的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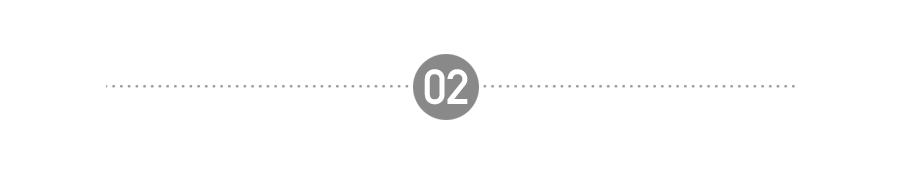
从书斋到田野,从研究到叙事
李开元第一趟历史行走的目的地,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丰县和沛县。
在如今江苏徐州的丰、沛二县,他和当年寻访到此地的太史公一样,听闻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有关汉高祖的种种传说。尤其是云雾桥遗址和两块出土的明、清时建桥碑刻,让他一时浮想联翩——这正是刘邦出生神话流传的物证,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之母刘媪在水塘边休息,“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他感慨:秦一统天下后,过往的世袭贵族制被扫荡一空,如刘邦这样平民出身的帝王为弥补自身血缘、家系的不足,必须制造“龙种”神话来装点他的合法性。
行走在韩信的家乡淮阴(今淮安),李开元对这位军事奇才有了真切的理解。“你看韩信每一次重要战役都是在水边打的,像著名的背水之战、潍水之战、暗度陈仓之战,他特别擅长用水道来行兵谋。一到了他的家乡,你才知道为什么——淮阴就是一个水乡,水系发达,他是从小就受这个灵气的影响。”
不久,他有了同行的伙伴。2002年在西安参加学术会议时,李开元和正在北大访学的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一见如故,两人都仰慕太史公,都有重走历史现场、重新书写历史的心志,于是相约为“走友”,一起行走九州,追随太史公的足迹。
每到一地寻访古道、古战场、旧城遗址和出土文物,他们都要寻求当地考古队和文博工作者的指引和帮助。“最受不了、也是最愉快的事——就是你必须喝酒,”这些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常年在田野,经常和当地人打交道,因而懂人情世故、接地气,个个都是豪饮的好手。
行走、考察,让李开元找到了对历史最直接的感觉。
当亲眼看到遗址、出土文物,亲耳听闻考古挖掘的具体经过,过去的物、事、人都复活过来了。“如果你只坐在书斋、完全沉浸在文献里面,最后很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你弄不清楚历史究竟是历史学家编造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你一直深入下去以后,你的历史感就非常实在了,再也不会怀疑历史本身存在不存在这种非常虚无的问题。”
20年来,李开元因此在天南地北结交了不少考古、文博界的朋友和民间文史爱好者,彼此在历史文献、地下出土文物和风物传说中相互印证、辨析,切磋探讨,留下了醇厚的情谊,也感受到学术和生活的双重乐趣。
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和李开元住同一间宿舍的室友。在他记忆中,李开元那时清高骄傲,喜欢高谈阔论,经常嘲笑他们搞历史地理的工作琐碎,缺乏足够的成就感。“现在他人谦和了很多,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李开元。我是打心底为他感到高兴。”他笑着说。

▲长城考察照,左一为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 图/受访者提
2005年11月的一天,出版社编辑徐卫东在网上“闲逛”,忽然被一篇题为《战国时代的刘邦》的网文所吸引。开篇就讲刘邦和秦始皇只差了三岁,他其实是个战国人,“我学历史的,但这块对我来说也很新鲜。”
当时,徐卫东在为中华书局策划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的再版,很希望能寻找同样“好看又深刻”的历史作品。他立刻通过电邮联系上远在日本的李开元,提出想为他出书。
对当时正在独自摸索、周围尚无人喝彩的李开元来说,这无疑是一道光。
自2002年决意学术人生转型后,他一边行走、考察,一边写作,陆续写成系列文稿,最初取名为《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因为是研究与叙事、学术和文学、游记和个人感怀等各种元素混搭在一起的“四不像”,他也不知该发到何处,曾投稿到一家文史类杂志社,结果被客客气气地退回。而史学界同行们也报之以沉默,有人私下说李开元怎么“沦落”到去写通俗读物了呢。
他并不气馁,干脆把部分章节贴在一家历史网站上,和网友们分享,当起了被友人们后来屡屡嘲笑的“网络写手”。徐卫东是第一个注意到他的图书编辑。很快,前后共有十来家出版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上李开元,争相要为他出书。
2007,中华书局以《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为书名,出版了李开元的第一部历史叙事作品,好评不断。2010年,其繁体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书名被更改为更富冲击力的《秦崩》,迅速登上各大图书畅销榜,此后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楚亡》。2015到2021年,三联书店推出了经过重新包装的注释版,新增《汉兴》,并冠之以“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
三部曲封面上的书名,皆出自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手书。

▲2014年1月27日,徐俊 (左) 与顾青 (右) 拜访田余庆先生 图/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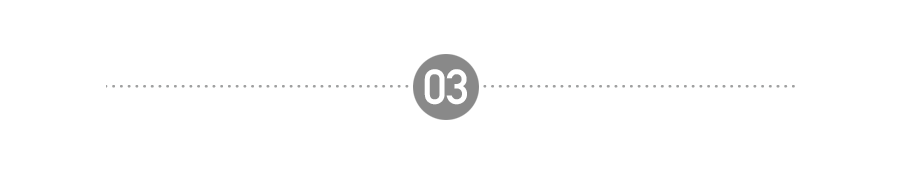
逼近历史真实的武器:研究,推理与想象
在李开元看来,研究和叙事是推动历史学行进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写《秦崩》时,要还原韩国后人张良伏击、刺杀秦始皇的经过,他碰到了一个疑难。
据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共有五次巡幸天下的经历。其中,后四次是朝东的,唯有第一次路线是向西。而且,后四次《史记》记载较为详细,伴随刺杀、封禅、求仙等大事件,是学者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但对公元前220年这一次西巡,相关研究稀少,司马迁在《始皇本纪》上仅用了17个字一笔带过——“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接下去,他转而讲述秦始皇回到咸阳后下令为自己修极庙,并筑小道把庙和自己在骊山的陵连接了起来。
虽然并不影响张良故事的完整性,但李开元不想就此绕开问题。
他想起1990年代甘肃礼县曾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秦公墓被盗事件。多年后,直到被转卖至香港、欧美、日本等地的被盗文物部分流回中国大陆,才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他也读了一些相关文物资料和考古挖掘报告。礼县是秦国第一个都城西县的所在,他由此推想:嬴政的第一次西巡,很有可能到过西县,目的是为了祭祀先祖。
为了证实想法,2014年8月,他和藤田胜久、韩国学者金秉骏师生等十人,携数个研究考察任务,从成都出发,沿川西、经甘东到陕省西部,徒步加租车沿着自然地形走古道,总共九天。他们参照《史记》中几处相关的记载,结合沿路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加上实地行走摸清楚的河流、山川地势,终于还原了秦始皇第一次巡幸可能的完整路线。
最后,李开元得出结论:始皇帝第一次巡游,沿渭河向西,随后北上汧河,翻陇山,途经秦诸先公、王庙和陵墓所在的咸阳、雍城和西县地区,其目的是为了祭祀和告庙,向祖宗们汇报统一大业完成。此行结束后,他开始着手进行宗庙、祭祀等一系列改革,把宗庙和陵寝分开,此后影响了两千年中国君王的墓葬制度。
他所提出的这一证据链和结论,得到了秦汉考古学界的认同。
解决这一疑难后,李开元心情舒畅地改写了张良刺杀秦始皇的章节——《博浪沙一击》。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实地行走和文献考辨结合,写成论文《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到西县告庙祭祖说——兼及秦统一后的庙制改革》,发表在学术刊物《秦汉史研究》上。
复原历史现场时,最令人头疼的,是传世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以及大量空白。
在秦末群雄起义中,陈胜、吴广的张楚大军和秦军之间的戏水之战,一直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公元前209年,张楚大将周文率数十万大军西进,攻破函谷关,兵至骊山脚,距咸阳不过一百余里的距离。然而,周文军突然停留在戏水的东岸,止步不前了。此后,他与章邯率领的秦军对峙,兵败。张楚政权从此由盛转衰,迅速败亡。
一流的军事指挥官周文为何不趁势挥师西进,一举攻克咸阳,彻底摧毁秦帝国呢?
司马迁仅用16字交代这支部队的行进、停留,然后笔锋跳转到秦二世在咸阳召开的紧急对策会议。会上,秦将章邯请求秦二世赦放骊山刑徒和奴隶,把他们编入秦军。接下去,是秦军击败滞留在戏水东岸的张楚大军、周文战败后退出函谷关的内容。
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爱好者也会觉察到此间因果链的缺失:在秦这一边,从咸阳开会、讨论兵力不足的问题,然后等章邯回骊山、释放刑徒,到最后组编军队,要耗上多少时日?其间,张楚军队为何白白丧失时机,坐等扩充兵力后的秦军来战呢?
在《秦崩》里,李开元通过类比“二战”中最具偶然性的关键事件——敦刻尔克之战,结合在骊山出土的秦兵马俑所展示的秦军实战布阵,以及实地考察到的渭水和函谷关——咸阳的地形,做出填补历史空白的一种尝试。
他由此推测:公元前209年,阻挡张楚大军攻入咸阳的,正是卫戍京师的秦帝国精锐——中尉军;他们屯驻之地就在骊山下、戏水旁;当周文部队到达戏水后,中尉军依靠河流在此处形成的瓶颈地形,把守住函谷关——咸阳道,以少胜多地挽救了大厦将倾的大秦帝国,为章邯的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在力图还原这场“消失”的战争上,他在叙事上走得更远一些。在《英雄周文》这一章节里,他运用文学和电影手法,想象了周文率部在戏水和秦中尉军对峙、开战的场景,和其间的心理变化,最终他下令部队停止渡河,退回东岸。
对于严肃的、研究型的历史叙事,这会不会太激进了一些?
“在历史的空白处,文学有时比史学更可信。”李开元似乎习惯了这样的质疑:“在史料缺失的地方,进行合理的推测和构筑,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
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学中的推理和想象,他和田余庆先生有过一次对话。此前,他把自己的历史推理作品——《秦谜》赠送给田先生。
“他说我发现你就是在做推想嘛,你经常是做推想的。我说,田先生,你也推想。田先生笑了。然后,他说他自己的推想比较小,是在两个指头之间,然后他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手势——'但你推想的范围有这么大,还有,你的跨度很大。'”李开元回忆。
“实际上,历史学都是在做推想,区别在于大家的尺度大小,以及合理程度高低。我不是说我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将来如果有新的材料和证据出现,可以来证实我,也可能会证伪我。如果被证伪了,那我就表示我错了,然后再做一些修正。通过这样,我们一点点逼近历史真实。”

▲甘肃省敦煌市小方盘城遗址,李开元在夕阳前拍摄汉代积薪遗物时的身影,远处跑过者为金秉俊 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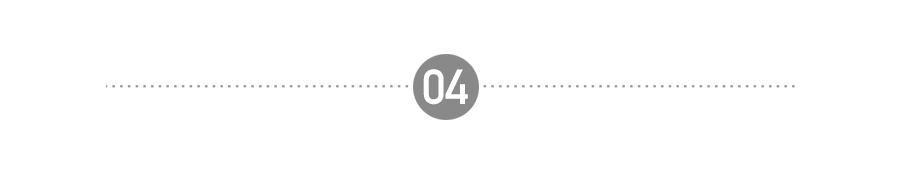
“后战国时代”的再叙事
在《秦崩》《楚亡》《汉兴》中,李开元以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于楚国沛县、到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故于长安为时间舞台,用笔墨呈现了一个风云变幻、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时间跨度整整一百年。
2017年,台湾青年历史学者游逸飞读完《秦崩》后,将之界定为“历史再叙事作品”,是“统摄了各种方法,吸取各种成果,在精密分析基础上的重新叙事”。他进而大胆预言:“再叙事”或许是21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取径。
这让李开元颇有遇知音之感。当初,驱使他投身到对这段历史书写的内在动力,正是基于他在前20年学术生涯中提出的两个史学新理念——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说和对“后战国时代”的认识。
受田余庆先生名篇《说张楚》启发,李开元在秦汉史研究中发现:在统一的秦帝国崩溃(公元前209年)和汉武帝亲政(公元前135年)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激变时期,前后跨度约七十余年。
他将之命名为“后战国时代”:秦末大乱后,“战国七雄”复活,王政复兴,豪杰游士四起,各方合纵连横;此后楚汉相争,刘邦击败项羽,接受七国推举即皇帝位、建西汉王朝。
到西汉初至窦太后去世前,天下则是汉朝一强主持而多个王国、众多侯国并立的“联合帝国”,彼此划界分治,关系比照国际政治;制度上,是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和诸侯国内的封建领主制并存;黄老之说在诸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在社会风尚上,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再起,游侠盛行。
通过三部曲,他想改写自东汉班固起、两千多年来史家对秦汉之际的叙事——“大一统”的秦帝国之后,是“大一统”的汉帝国,汉高祖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云云。在李开元看来,对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甚至司马迁也存在“认识模糊”的问题。
“他是我的偶像。但是,我认为我们是和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李开元带着笑意、自信满满地宣告。

▲2014年8月,甘肃礼县鸾亭山汉代祭祀遗址,左一为李开元,左二为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左三为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秉俊,其余为金秉俊的学生 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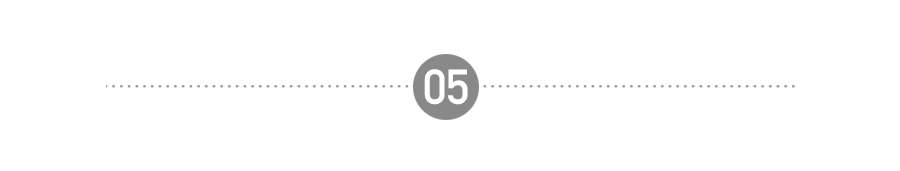
游侠,“无赖”和柔软的时代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读秦汉史,对汉高祖刘邦的直接观感就是一个流氓、混混,身上有无赖气;但同时又感到很疑惑:如果他真只是一个流氓、混混,如何能做到让这么多英雄豪杰甘于追随、拥戴他?难道历史真是简单的“劣币驱逐良币”吗?
但是你的三部曲特别提出:刘邦跟秦始皇是同代人,两人仅差三岁,他在观念上是属于战国人,而且是一个仰慕信陵君的游侠。写这一段历史和众多人物时,你是有心让我们去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特殊性吗?
李开元: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是历史学本位的人,因为我们做这段历史叙事的时候,第一是要做一个很严密的年表,这个非常重要。做了年表以后,你马上就注意到时代的问题了,就是刘邦和秦始皇实际上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年龄差很小。刘邦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战国时代。
而且我们注意到他曾专门去信陵君生活过的大梁,并在信陵君的门客张耳府上住了很久。而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游侠盛行的时代。然后你再考察他和王陵的关系,就发现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那种“无赖”。“无赖”,在古代汉语里是指“没法依靠”,没有我们后面说的流氓、混混的意思。刘邦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游侠,这就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历史特点。我们去了他的家乡以后,就对这个有了更深的理解。
到“后战国时代”,是一个游侠风气重新恢复的时代。从刘邦对信陵君的崇拜、对张耳一直以来的尊重、和王陵的关系、和卢绾的关系,以及他临死前和群臣立下的“白马之盟”——那完全是一种结盟起誓的互信关系。从这一整套关系,就看得出来他完全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游侠。
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公共讲座,包括百家讲坛,都把他说成流氓、混混,这都是因为没有做过仔细的历史研究,再加上陈陈相因,夸张地去说他一个小痞子怎么会成为皇帝的。
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因为我们对于历史的背景比较清楚,所以给他的这个定位非常准确,这也是两千年来没有人定位过,是我们重新定的。对这个定位,我们的这个底气非常足。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出了“后战国时代”的概念,认为班固对此认识完全错误。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当时“大一统”和儒家思想已占据绝对的主流。但是,太史公父子跟那个时代很近,相隔也就一百多年。你为什么认为司马迁的认识反而比你模糊呢?
李开元:因为中间毕竟隔了一百多年。而且,他又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武帝时代又是一个新的“大一统”时代了,所以有很多现实的东西已经影响到他了。那个“后战国时代”,他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也很容易用他身处时代的观念来审视他没有经历过的那一百多年。
但是,因为他没有形成固有观念,所以还是保留了很多真相。你看包括他写的《项羽本纪》,实际上不仅是他认可项羽这个人,而且他认为“楚”很重要,所以他要作为一个本纪来写。另外,在《史记》的表里面,专门列了一个“秦楚之际月表”,是表示在秦汉之间还有一个楚的存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更深的东西,包括整个战国七雄在此期间复活、回到战国时代,这一点他还不明确,我们说他比较模糊是在这里。
但是,他也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一些特殊用词,比如他讲“五诸侯”,实际上就是指除汉、楚以外还有五个王国;包括像“诸侯子”(户籍在诸侯王国的人),他都保留了。但是,我们觉得他在认识上有一点模糊。
而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包括更早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都是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以前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包括经过田余庆先先生他们的缜密研究,我们就觉得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是更清楚、更明确的,而司马迁是比较模糊的。
说实话,我们对于史真(真实的历史)、史料、史著、史实、史释之间关系的思考,要比司马迁高明得多了,因为我们是现代人,不但受到中国(传统)史学和哲学的影响,更主要还受到现代西方史学和哲学的影响,我们掌握的认识历史的工具更强有力。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你有这个豪气,说“跟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吧?
李开元:对。我跟你说,他们都对我说:哎,李老师你要谦虚一点。我说不是这样的,司马迁是我非常钦佩的,是我的偶像,我认为他不但是中国史学的巅峰,也是世界史学的巅峰啊,在那个时代就写出这么伟大的一个著作,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具体到对这一百年历史叙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和他站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比如兵马俑,是他还没有看到的;我们对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思考,可能比他更深刻。不然我们这两千年白活了嘛,这两千年来中西方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是白活了是吧?
所以我们是比较有豪气,肯定比班固以来两千年的史家都更高明。但是,我们和班固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是把他远远抛在后面,所以豪气比较大。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汉帝国的建立和刘邦集团》中指出:在汉初120年里,存在着汉朝和多个王国、众多侯国并存的“联合帝国”时代,彼此相对独立,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探索分权共治、有限皇权的特殊时期。到汉武帝以后,就基本上恢复秦制、确立了“大一统”和皇权专制,此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
如果“后战国时代”里那种政治制度和分权结构能够继续探索下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面貌是不是会有根本不同?
李开元:我们觉得可能会有。因为我们觉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在秦末,他们(起义者们)是采取否定秦的制度、政策,以复活战国的形式来重新建立新秩序,而且是第一次用道家思想、黄老思想来作为统治思想的。这些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柔软的时代。但到了汉武帝时代,他把秦的制度继承过来。这个制度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后来又被拖回到了“大一统”。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可能会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型的机会,但是,后来并没有这样转,又继续回到了秦的“大一统”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没有继续做更深入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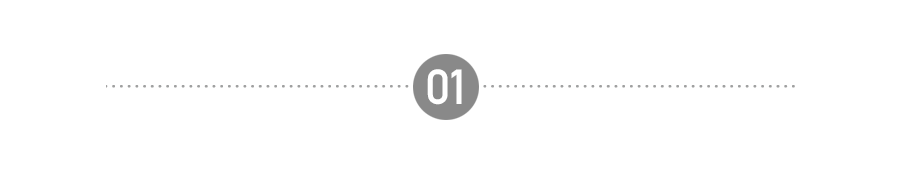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