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指在中华法系的发展历史上,在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审判的依据,来定罪量刑。特别是对于疑难案件,要求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以此作为判案根据。“春秋决狱”的提出者是西汉的董仲舒。自董氏首倡后“,春秋决狱”成为汉朝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成为中华法系儒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春秋决狱”在法律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一、“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带着他的一套“强国之术”来到秦国之后,秦国奉行他所带来的法家之术,结果是“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继续奉行法家路线,并将法家的这种暴力主义路线推向极端。这种尚武功而不重文治,一味急功近利,严酷刑罚,张而不弛,最终导致了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六国残余势力的矛盾的急剧激化,结果,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这无情地暴露了法家学说的弊端。在解决如何巩固统一后的政权,如何调整政治法律政策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当时的民情、国情、社情的问题上,法家思想无疑不是上乘之选。在西汉初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掌权的地主阶级有了一个反省的时期。
于是,自战国就已形成的以道家“无为之术”相标榜而纳法家“刑名法术”于其中的黄老思想受到汉初统治集团的青睐。由于汉初推行“黄老”政治,社会出现了“清静”、“宁壹”的稳定局面。汉初统治者轻徭薄赋,劝趣农桑,与民休息,约法省禁,去奢省费,社会秩序安定,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黄老之术”的推行,对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地位是奏效了的。至西汉中期,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借助于无为而治的思想氛围,地方割据势力大肆活动。在“诸候坐大而害于内”的同时,社会上又产生了一批虽无官职爵位但却横行不法、奢侈淫溢的豪富吏民,极大地破坏了封建等级秩序,威胁着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无为而治的思想已难以适应这种新形势,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又难免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此时,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法家思想更温和的儒家思想迎合了汉朝天下一统,民心安定的时代需要。“《春秋》大一统”的政治学说,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和采纳。这一建议,实际上是按照儒家所倡导的礼义道德观念,建立一套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封建等级秩二、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一)原心定罪“春秋决狱”的核心原则就在于“论心定罪”,其背后的观点是将人心作为一切行为好与坏的根源,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
《盐铁论刑德》记载的具体内容是:“《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古书《太平御览》引《汉赵记》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论心定罪”原则所强调的是主观“心”的好坏,而判定“心”好坏的标准又是儒家的伦理规则。“春秋决狱”作为汉代中期以后盛行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方法,其基本特点就在于依据客观犯罪的事实,着重考察行为者的动机是否与儒家道德相符合,如不合乎,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也可以从轻论处。对于首犯,应该从重处罚,而对于只有犯罪行为而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应当从轻处罚。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这么做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但实行“春秋决狱”在客观上折中了立法和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二)“亲亲、尊尊”原则在“原心定罪”的总的思想指导下,支配人们“心”、“志”的伦理道德理念,即其主观共同正义的标准也相应定位,这就是渊源于周礼“尊尊、亲亲”原则的君臣父子之义。“春秋决狱”中“原心定罪”的标准就是,推原其“心”是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君臣父子之义是贯穿《春秋》的基本思想。《春秋》决狱的根本,就是要求人们用君臣父子之义,去评判是非,决断善恶。
首先,以“忠”为核心的“尊尊”原则,其宗旨是:“君亲无将,将而诛之”。如果说君臣父子之义是“原心定罪”的评判标准,维护专制主义下的皇权不可侵犯则是君臣之义的核心所在。为了维护皇权,尊其尊者,按儒家的伦理观念,君主在国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其含义就是要求臣子绝对服从君主,尊重君主,忠于君主,以至于一切奉献给君主。董仲舒说:“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故为地者务暴其形,为这就是说,人臣对君主必须绝对忠心和服从,不能有丝毫地叛逆和奸伪,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和地位,臣子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其次以“孝”为核心的“亲亲”原则,其宗旨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尊尊”即“亲亲”,“亲亲”即“尊尊”,作为君臣之义的延伸,父子之义则是维系家庭内部道德规范的准绳。“父慈子孝”是传统儒学处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道德准则。“慈”是父母的道德标准和义务,“孝”是子女的道德标准和义务。儒家要求父子自觉奉行慈与孝的道德规范,来协调父子关系。三、对春秋决狱的评价对于“春秋决狱”的否定性评价,从清朝开始就不绝于耳。
刘师培在其《儒学法学分歧论》中就指出,董仲舒的春秋决事,看似宽宏、实则严酷,更为酷吏任意刑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我们也应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春秋决狱的影响。(一)积极方面第一,春秋决狱是统治者推行儒家理论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则有突出的影响。其所宣扬的“罪止其身”、“以功覆过”的原则,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中国的法,缘于礼,附庸于礼。礼在社会管理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法治的发展经常被礼治形成的规则所左右;这在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年代,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春秋决狱的案件中就有不少是用《春秋》中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的原则。第二,春秋决狱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法家指导思想为主的局面,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其它各家学说,开始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为引礼入律、礼法结合开辟了道路,并对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法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律学成就是显著的,其注律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注释律学已经达到了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程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铸造法制文明上的智慧。第三,强调以动机考察犯罪,在兼顾事实的同时,注重动机。
这对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动机、目的和心态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定罪和量刑,并且从中可以随心所欲的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以便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上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在法治化的进程方面,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关注礼教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上,也要警惕礼对法的消极或阻滞作用,防止等级、纲常等礼治思想对法治形成破坏。第四,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纠正了封建法律中有乖人情之处。“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这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决狱制度对于缓和社会矛盾,降 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消极方面 第一, 春秋决狱加剧了司法的腐败。参与司法活动的主体借《春秋》之名, 私利之实,使法律的公正性、严谨性受到影响。春秋决狱的特点就在于可以根据 统治者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而在司法审判中,实际上并没有客观严格的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的判断取决于各级官吏的主观意志。对于司法官吏而言, 因为有 《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尚方宝剑, 可以牵强附会, 可以望文生义, 可以任意曲 解法律。
纵使在正常情况下, 司法审判中也很难避免主观臆断, 更何况有《春秋》 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 司法官吏为了一己之私而置法律的公正性与严谨 性于不顾, 故意歪曲法律。这样, 表面的法律条文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背 后的隐秘交易, 熟不熟悉法律条文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这在当时法律不健全的 情况下,司法更为腐败。 第二, 春秋决狱使得法律和道德之间界限更加模糊。汉统治者推行春秋决狱 以后,儒家伦理道德从各个方面渗透到法律中去,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极力主张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道德几 乎成为法律的化身, 法律也似乎是道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方面, 凡是触犯法 律的行为, 必然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 不合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 甚至是犯 罪行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判断, 有其自身的规范, 对人们行为起约束作用; 法律也有它自身的强制性, 两者虽有内容上的相近或重合之处, 但法律毕竟不 是道德, 道德也毕竟不是法律。如此严重的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必然导致人 们对法律的不信任, 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极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 它动摇了法律 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不可避免的为人治主义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友好:《“春秋决狱”之内涵极其价值探析》,载《克山师专学报》2002 年第四期,第15—19页 2.吕志兴:《“春秋决狱”新探》,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0年9月第26卷第五期,第161—165页 3.封志晔:《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载《中州学刊》2003年9月第 五期(总第一百三十七期),第117—119页 4.武秀艳:《“春秋决狱”原因初探》,载《黑龙江教育学院报》2004年1 月第23卷第一期,第71—72页 5.崔灿:《论汉代的春秋决狱》,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8月刊,第307-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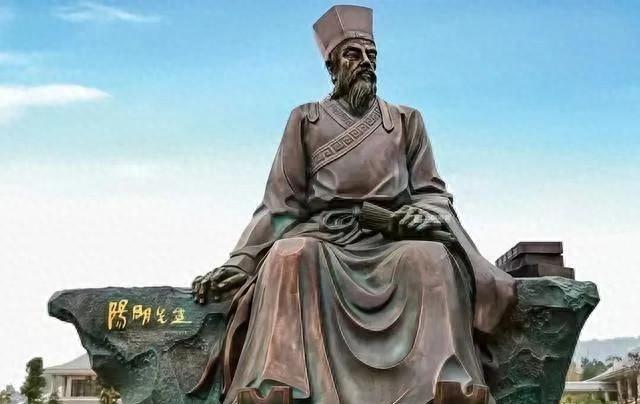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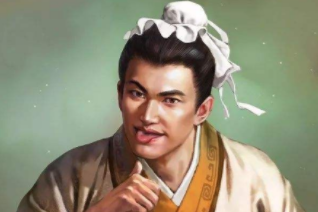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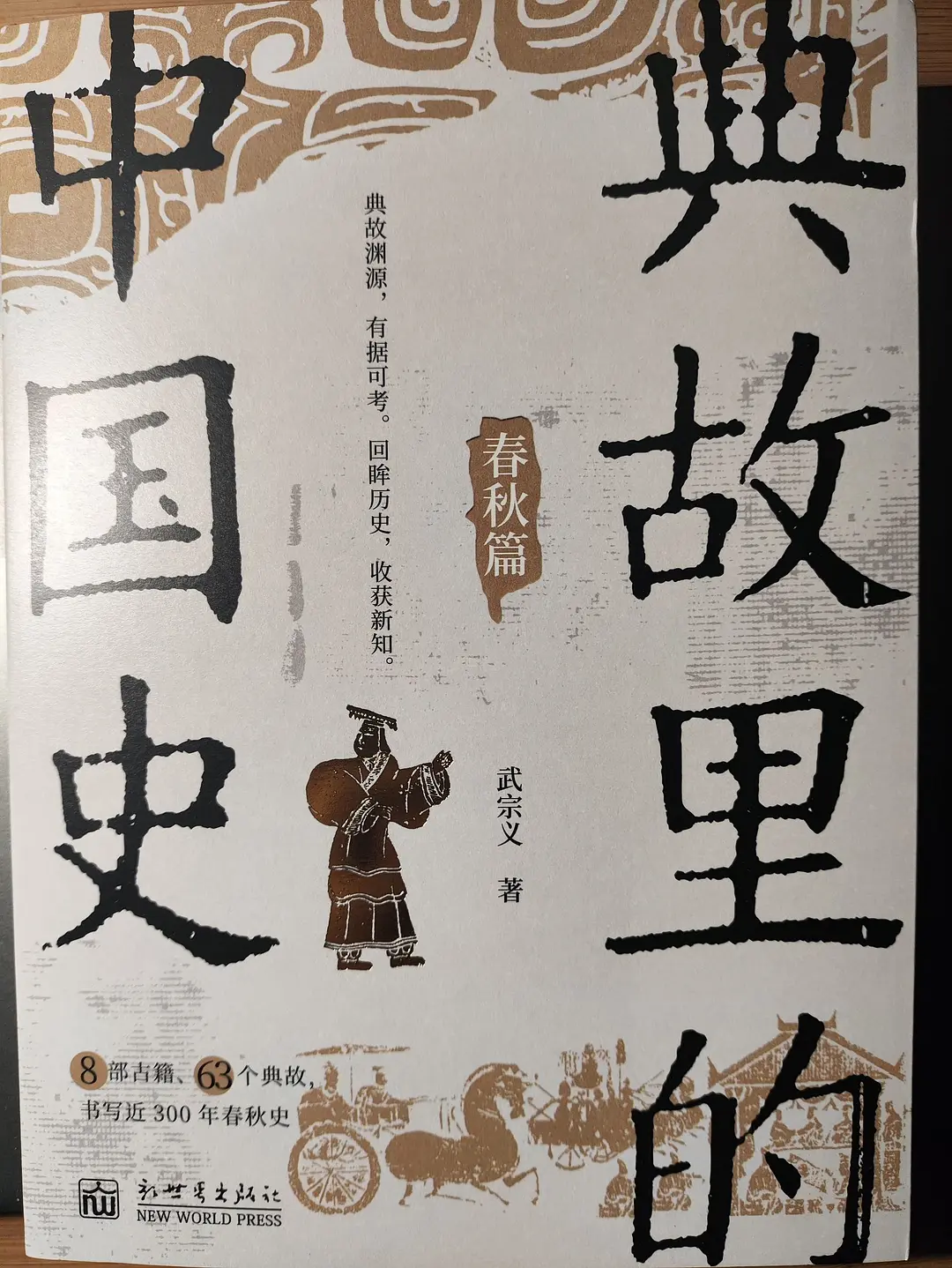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