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61年,为了政治平衡和互信,郑武公娶了申国公主,“武姜”,公元前757年,生下一子,临盆时脚先出来,因为难产、差点害死武姜。也因此受到惊吓,所以很讨厌这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寤生”也就是带领郑国称“小霸”于诸侯的“郑庄公”。
公元前754年武姜产下第二子,取名“共叔段”,对于共叔段,武姜特别喜欢,而且还多次向武公劝说,要立共叔段为太子,郑武公说:长幼有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规律,所以,从上至下都只能认可并接受这个约定。立嫡长子为太子)而且寤生也没有犯什么过错,所以不能打破这个规矩。一直都没有答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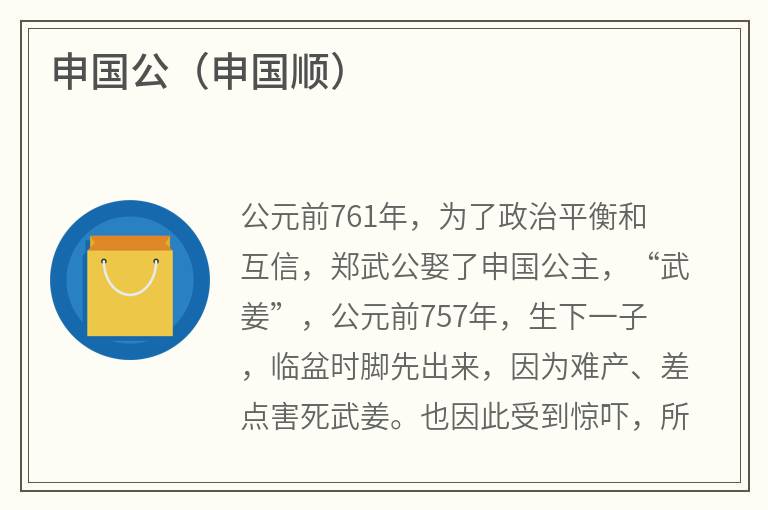
申国公(申国顺)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继承君位,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没多久,武姜就和共叔段合计夺取君位。武姜先是请求郑庄公把地势险要,虎牢关尤扼要冲的“制邑”(今荥阳市区西北12公里、峡窝镇上街村)分封给共叔段。
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更何况先王有遗命,不允许分封此地,若是分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
”武姜便再次请求封给共叔段“京邑”(今江苏省南京市),庄公听后沉默不语,武姜大怒道:如果再不允许的话,那只能远走他国,谋求发展,养家糊口了,庄公听后,连忙回答:不敢不敢,缓慢的走开了,算是答应了。(其实庄公也是很无赖的,亲弟弟和母亲合谋夺取他的君位,他又是个孝子,在没有反之前他只能任之听之。)
第二天上朝宣布分封的时候,大夫祭仲连忙阻止说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京城有“百雉之雄”意思是指城池的长度达到三百丈,(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国君的城池才有三百丈。)而且地广人多,又是太后的爱子,那不是第二个君王么?
大夫祭仲又说:“京邑的围墙超过了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先王的规定,大城市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的京邑,大小不合法度。违反了先王的制度,这会使您无法控制。”庄公回答说:母后的命令,我怎么敢违抗呢?
”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不如趁早给共叔段另外安排个容易控制的地方,不让他的势力滋生蔓延。如果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滋长的野草都很难除掉,更何况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
在册封共叔京邑完毕后,共叔离行前入宫来与姜氏告别。姜氏叫退下人后,小声的跟共叔说:“你哥哥不念同胞之情。对你很苛刻,今日册封的事,是我再三恳求,他心里肯定有阶梯了。所以你到京邑之后,趁机招兵买马,小心准备着,等到有机会的时候,我再通知你,你举兵攻城,我做内应,等攻下城池后。你就代替寤生之位,我死也无憾了!”
共叔领命后,前往京邑居住。从此之后国人也随之改口,称共叔为太叔。没过多久太叔又命令原属郑国西部、北部的边邑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庄公。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侍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民生二心。”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民心。”庄公说:“像共叔段这样不亲近兄长,百姓就对他不亲,势力再雄厚,也将会崩溃。”
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共叔段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段逃到共国。
《春秋》记载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到死后埋在地下),不再见面!”过了些时候,庄公又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颍考叔答道:“小人的母亲,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
”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担心什么呢?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从此,他们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
说:“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诗经·大雅·既醉》篇说:‘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这类纯孝而说的吧?”
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
《东周列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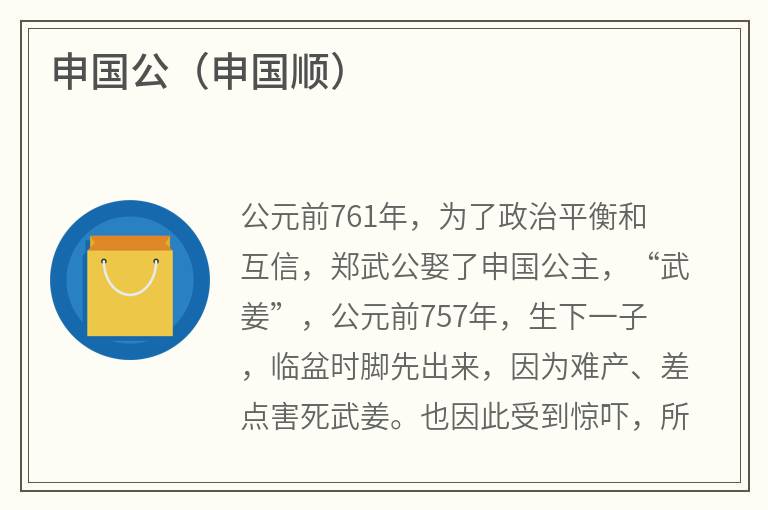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