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密码(一)
栾贵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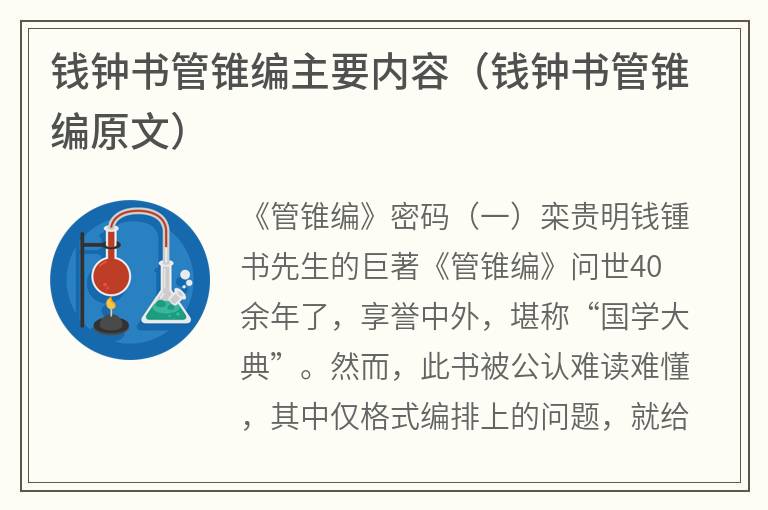
钱钟书管锥编主要内容(钱钟书管锥编原文)
钱锺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问世40余年了,享誉中外,堪称“国学大典”。然而,此书被公认难读难懂,其中仅格式编排上的问题,就给使用者的阅读、理解造成了诸多障碍和困难。何以至此?请看此文,为诸君揭秘。
大书《管锥编》构思于1970年之前,成书于1975年,第一版1979年在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二版出版于1986年,第三版1991年。该书作为中华文化的要籍,开写是在1972年的3月,至1975年7月杀青,三年多完成了全部书稿,原稿约140多万字,语言文字风格大如先写后编再出的《旧文四篇》。
《管锥编》的初版仅四册,字数较比原稿、誊清稿都已大为压缩,我同钱锺书先生一起估算,压缩量大约有40万字。所称誊清稿,是按官定出版商所传的“建议决定”:由原稿誊清稿的字数“不得超过80万”。钱先生的原稿除存有大量修改墨迹之外,只不过字数有所超过,因此在下认为根本不必进行所谓的“誊清”。人微言轻,无济于事。可他们自上而下地通知我,要出版必得用《柳文指要》做模版,誊清稿的字数一定要符合出版方所做出字数的规定,因此从审读初稿看,必须进行“严格的压缩”。对此,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没看到全部原稿,但可以主观规定。第二个反应是,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代表,而我是跑腿出工的苦力,绝无对话甚至谈条件的可能性。又听通知说,他们也力不从心,需要特调某某大编就任才行。
在这种情状下,我坚决主张钱先生对之“不予理睬”,交稿完事。先生说:“照你的办,咱们俩多少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要调人来,我不同意也不成啊!这可不像文学所,你我能当上谁也管不着的自由兵。”“外人会认为是你在逼我抗拒,我找中华是看中了那位好大编马蓉同志来做责任编辑,到头来一定害她当不上什么编辑。”“嗐,算了,能出书最重要。”“你要尽量帮我记着这些事。”这是我记下先生所说的零言碎语,当时记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先生经过一年多努力,做到为过桥而修路,重新压缩着誊清成新稿,卷面质量非常高,几乎没有改动的墨迹。读者大概不太能像我一样,再见到被废的初稿。至于数千页誊清稿,则完全在钱先生预判之中“丢失”,我不可能再见,只能成为我平生最痛之事。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同时“不会有人来问你”的估计,从1980直到今日,已经四十年“言之不爽”。
先生精心设计抄改,分批交出誊清稿,实际上还是突破了80万的上限。不出所料,不管上限还是下限都无法越过严谨的大编周振甫先生。多日之后,我豁然开朗,需要我“帮助记住”的事,还真的很多,让我慢慢还给读者。这是后话,破例提前预告。
记得当初先生猛一听到这一有关字数的传话,也曾立刻出招,说可先出“上册”,再出“下册”。先生自己想想也否定了,因为已参与编辑的马蓉说“你们甭想,《柳文指要》是标志,不得踰越”。可钱先生的写作有如“火山喷发”,岂能按下不表?几天之后,先生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誊清”操作了。先生悻悻地向我说,想想过去,80万已是“天大恩典”,须得快快“领旨退朝下去罢”。钱先生这种奇妙的京腔,外人中只有我能听得到,但不知他老这齣是在学谁,是吴世昌,还是梅兰芳?火头上,自知不可浇油,我只剩下苦笑。此间先生见我可怜,特将自己书写流行的“高压锅”三字送我,我真以为他要托买物品,他否定。奇特字条中有一个奇妙的简化字,并衬以它字组成一句,亲手递交给我,似乎要代他留作特别时期的特别记录。我有如得万斛珍宝,至今高奉,但我不能“全解其意”。
所谓誊清稿的压缩过程,实际就是对“文字数量”进行压缩,既经当时无计其数的论辩和说明,均属无效。先生毕竟对“内容”心疼不舍得,设想只能从“形式”上下手,将“白话文”压缩为“文言文”,是唯一认为的可行之路。先生说他倒可以借机“自得其乐”甚至“表演一番”。悲观主义者钱锺书,往往对生活采取乐观的对策。大规模交稿之时,先生向我说,“我不按规完成任务”,周振甫一定“饶不了我”。然后先生说:“真的不让你再看了,免得生气吵嘴。我一个人生气,已经赔了大本钱。留着你还有别的用处。”所以一二册出版后书到手一翻,先是吃惊诧异,当我感到内容也大有删削时,简直就是狂怒了,我还真以为要分上下册了呢。
后边的话我憋不住,只说两句:岂知原来人家传说,先印一二册是为探求印数的商业手段,得到的反是销路不好的结论,三四册便立即压缩印数。不料等三四册一出,买到并读完一二册的人,有如大梦初醒,可再也买不到心仪的三四册了。
岂不知一二册的滞销,是另有确定的原因的。可以肯定,是由于有人抢先出版了引有《管锥编》的《诗词例话》,帮助周振甫的老东家青年出版社一口气大卖36万册,一举打败了中华书局的投稿者钱锺书。在这里,我们先按下细节不表,因为那不能算是密码,而是明码。
《管锥编》从其初生之日起始,就如一位超人类的顽童,妙趣、深邃、辉煌,总好似摇着拨浪鼓,在路上海上天上,玩耍嬉笑向着敬重他的读者示好。倾听和细读,能带给好文者以无可取代的欢愉。或者说,敝人是一名败兴者,专来展示记忆中的伤害。我爱钱锺书的读者和研究者,要告诉人们真相,免去辩驳谣传和谎言,以求唤囬那位纯真美丽多学的老少年。
钱锺书那些失去的文字,在我每日读写校改的生涯中,记忆非常美好。当它离开书面之后,就变成我的隐痛。先生那时正在国外访问,一囬国便说:“知足吧!把嘴给我闭上。知足者常乐,这些文字足证我文言尚苏而超苏(东坡)!”岂不知稿子送出之后,立即又传出“80万字,超出太多”,编排双方似乎都得了字数“幻想症”。
于是《管锥编》大量出现“……”,成为理论著作“现实里”的特例。
大书一经出世,作者开始了歴时二十年不休不止,不断的“补”不停的“订”,以追索囬来被删除的文字。本不应删除的内容,字数逐渐增加了一册。这对我来说,不出意外。因为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原来就有的,绝非是“后来阐发的”。其中只有《高唐赋》等二三处是被定性为“有问题,是扫黄打非的内容”才责令删除的,其它所删均未曾知会作者,而是作者自己发现,也未曾公开说明罢了。钱先生不止一次地自嘲道:“俺光明磊落,非要逼人用‘……’躲躲藏藏。”
令我大出意外的倒是一件小事:出版方将字数在版权页悄悄“涨”至136万字,远远高出实有字数。钱先生带我猜测,又经计算机计算证实,总字数实际并没有那么多。我们估计是出版者有所悟明而采用的夸大谋略。后来又传出,那是为先生增加稿费,后来可惜没能实现这一条。其实这一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当添出第五册出版时,按规定只计印数稿酬,和总字数并无任何关联。内行人分析下来,虚增字数恐为涨销售单价所预设。
至2001年,钱先生已仙逝有年。在学海潮涌的情势之下,《钱锺书集》三联本急迫出版,我应出版者之命,在退出编辑工作时,奉命须留下一条“意见”方可走人,我曾真诚地建议把作者“补订”的文字复位。希望使失散数百条,20多万字逐一得以“遣返”。由于钱先生预有安排,经我推荐,杨绛先生照允,请马蓉执行恢复运作,幸得116.6万字的全新版本。较之中华本最后的实有109.7万字旧版本就好得太多了,但未及其他旧版问题,而那些问题只能留待今后一一解决。
先生过世半年之前,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分人照管,在我的名下分的是《管锥编》,我和大家一起拒绝了。一来认为钱先生一定能顶过难关,健康可以恢复。二来我必须坚守不取寸纸分文之诺。三联本在筹措之际又生许多分歧,我遵杨先生嘱退出,并留存了那“最后”一条意见,同时加注恢复被“扫黄”的一条,感谢他们照办了。
如今先生去世已二十三年,我亦步亦趋基本完成了他老人家在计算机上建立“古典库”的大业,崭新的“万人集”也已顺利出版了三百多种。在下垂垂老矣,故当瓦盆洗手,只余几桩小事,随兴为之而已。
眼下还得顺路从《管锥编》走起,先说第一件奇妙之景“……”。
说百年文化运动,就得从新文化入手,新式标?,则是最显眼的一项成果。我辈应是还存一些旧味的文人,总会认为,字间的标?可有可无。一但古文要标?、今译、外译等等,当然还是用上的好。不料如今一个大毛病来了,一旦不用标?,不止读不懂文句,还真是一下便曝露了作假的古文和古董。新写文言者,往往不知他离不开标?,没了标?作者自己也读不懂,一切均假。闲话少说,不宜在本文中打假。
《管锥编》的两个版本,在标点方面,共有的妙处之一是“……”六?的省略号。凡标点自有它的用处,不可轻易反对。《管锥编》里的“……”可不平凡。首先让我们看看它在“引文”上的泛滥:中华本《管锥编》全书四册109.7万字,有“……”1840个;三联本《管锥编》全书116.6万字,有“……”2183个。数量之大,令人迷惑。
“……”原称“删节号”,至民国的1930年才统称为“省略号”,强调了作者使用此符号的自主性。想来他们并未采用西方的“…”,大约也是要留下些旧情吧。记得我在编辑钱先生下达的《永乐大典索引》任务时,先生定下了规矩,一定要使用外人的“…”以精简不必要的累赘篇幅,那显然是为了读者考量。语法定义该符号代表以下的意义:“重复词语”“所言断续”“意在言外”“难尽语意”“言语中断”“含混其词”“沉默不语”“语句延长”等,他们似乎忘记了另一项特殊的使用规则,即为被删节的记录。
钱锺书长篇旧作《谈艺录》,也有幸经周振甫手,那时他们二位都不曾使用省略号,究竟为什么会在《管锥编》里大量出现呢?恐怕就是选择了“删节号”的原始定义。在《管锥编》里,有一条通行的规则:除作者常规应用的少数几个之外,只在“引文”中使用。我清楚地记得,应该是在初始校改“排版清样”的时候,先是由编辑开始做主使用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得到删节字数裨益之后,似乎还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周振甫于是特打电话通知作者开放使用。作者本人表示不能“因小失大”,但也不得不用几个应景。可钱先生在出版之后,发现问题严重得“不像话”,又通过我向周责编表示“过分了”,他竟顾左右而言他,加倍使用,号曰“保持体例”。应该说,这一举措,既没有尊重作者,又忽略了对读者的关怀。我到如今也不明白,所谓80万究竟意欲何端?
下边我们为读者随机录出100条例证,原样提供给读者选读。当然还须举出被删文字做参考。就是说读此材料,必须先认明以下凡例:“……”为中华本《管锥编》正文。其位置为编辑使用该符号的具体地方,下面的“【】”内为被删节的全部文字(本系统使用红色),原引文标点保持;再下面“#”单行,则为删除的字数和原有字数的比例。所有字数计算,不包括标点。读书不遵凡例,是不妥当的。违反了凡例的批评者,我不便答复,因那是不平等的对话。
(其余99条见文章后附)
100条的平均删除字数比例/占比是37%,总计3083字/5220字=59%
按此统计,每条52.2字,删除的大约数为30字。按三联本有2183条计,总被删去约65490字,每千字稿费按中华本实付的19.5元计,总省去稿费约1167.25元。如果平摊到初印的30000本上,每本可以节省成本约4分钱,显然是一个不太美丽的笑料。这几乎印证了一位大戏剧家所云“喜剧的终点都是悲剧”,因为引文的结束全是删节号。又听说,宋代大诗人杨万里为一本书写的序,谈的正好是“古者有亡书,无亡言”,称所引皆“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此处却偏说及“言也亡”,当然使我们“喜笑骇悲”四味“咸失”了。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本文只道及“商业”并未言说“文章”,对留名千古的宏著赏观评价不足。我在这一点上,真不敢苟同于朋友;如果他们真说出明摆着的诸多“密码”,我恐怕也只能阻尼一二,慢慢来,免得在下脸面丢失过多过快。
一条条读下来,可以窥见这一百条大体的规律:
第一是本文所涉被删的内容均为引文,这肯定会对作者论述的完整性造成伤害,对读者的理解深度造成影响。如果需要全面了解,再要查找原文将加大读者阅读难度、甚至难到无处寻找。由于海内山外读书的钱某人,引书用书,非他人所能及。引文在《管锥编》中,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帮作者织成“中国好文化”密网,至纲至要。早年间,多有学者证明在钱先生引文中,有的果真因原书原稿佚失而不能覆核了。或者我们真可以判定这种“删节”,是一种纯商业化的操作,也可能疑涉是编辑权力的滥用。
第二是这种“删节”可以肯定是编辑做出的,我们既可以发现所删位置有误,又可以看到所删无助篇幅的缩减。大可想一声令下的删削快意,惟独不见“删文者某也”之署名壮色。“引文不明”之责,只能落在作者头上。
第三是,前面已说过,事实亲身经歴,不容大错。我们如果翻读一下1948年的《谈艺录》,虽然也是经周振甫先生编辑的,前我们已经详查并举证,确无省略号使用。可到了1984年,周振甫在取得《谈艺录下》的编辑权并答应“高抬贵手”的前题下,言而不信,对《管锥编》的不良举措“依然故我”,“习惯成自然”引文仍在省略号遮掩下,大删特删,成为对钱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嫁祸。
因此累年积蓄的许多原则分歧,导至作者对出版商口上不说的全面不满。他不再写、不再出的“倦意”席卷了书桌;写下严肃的“表态”文字;虽有限延绵迟发,仅只避医,并无疗效,更终不能惠及读者。诸多读书人,细心着力而未能引起自己一丁点正确的关注。他们当中的敏感者,有所察觉而描错了方向,费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而未及要害。钱先生转而专心投入到古典数字化工程当中去了,使该工程得到了“得天独厚”恩赐。从那之后,他的大部头的著作都另寻其他出路;他个人和周振甫的关系,也意料之内地变化得面目全非了。如果从那时开始能够冷静、客观地重读《管锥编》,一定可以深感令读者“自叹弗如”的叹息此起彼伏。多年来舆论漫卷的西风,一直对钱锺书先生同情而无奈。但只要走近钱先生本人,便会发生奇诡的变异看法。立即会说“啊,原来这样!”有一位钱学爱好者出于好心,应该说是把先见设置不妥,导至了严重的失误。他说先生“晚年少作”,其实错了。先生用他晚年的珍贵时光,为伟大的、他终生挚爱的祖国留下了一份达20亿字的“古典库”,那里几乎没有一个非作者本人所强加古代文人的“删节号”。先生曾断然下令:不得加“删节号”,不得使用现代标点,只可适当“点断”,而对于大删特删、明知故犯的《四库全书》,一定要选择其它正确的版本。那是一片崭新的新天地,真保护古籍的好办法。
像这个省略号之类的问题,在《管锥编》里远远不是唯一,而是之一。由我来提醒此事,是出于计划之中的一项责任,不是出气,更不是广告宣传。因为最终的《中国大典》即“万人集”,不必做广告。
钱先生早就说了,“省略号”应该恢复至五四时期的定义,还是叫“删节号”为妥,恐怕靠近洋人的“…”也好,因为它可加大删功,为节约稿费提高效率。对此,本文再次重申,《管锥编》编辑们并未写出过“凡例”宣告周知;也未曾在长篇众多论文中有什么公开的说明;更未涉及道德良俗的说教;或许可以干脆直说,那是名实相符而又持之有故的一种枉行。没人能让作者和读者同买一单,至于居于上游的编者还在谋划些啥子,读者自会猜想明白。
因此,在《钱锺书集》中的“……”,应该有两类。一者是作者钱锺书所使用的,比如在小说《围城》《人兽鬼》里,是“省略号”,自己正当地真使用,这是极少数。也有的在使用之前曾郑重声明,比如在《管锥编》(一)下册,页401,云《元秘史》卷七“兹撮录之”,下边用了八处“省略号”。这种情况,为数更少,需要认真甄别。二者是编辑周振甫所假使用的,比如在《管锥编》和《谈艺录下》中,只是“删节”的暗号,均是非作者本人所使用。
此事被冠称作“密码”,任何人都有权不相信、不使用,但请不要怪罪我,我会在结束本文的最后,再使用一个……请看好,这次究竟是省略号,还是删节号?要请您猜一猜了。
2021年4月
附例证: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