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初夏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特别是中午,太阳直晒在街道上,好像火一样。此刻,官巷口的几个做水果生意的小摊主,有气无力地喊着。其中一个摆甘蔗摊子的青年,不觉心里烦躁,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甘蔗一根也卖不掉,路上连个鬼影也没有,这样下去饿死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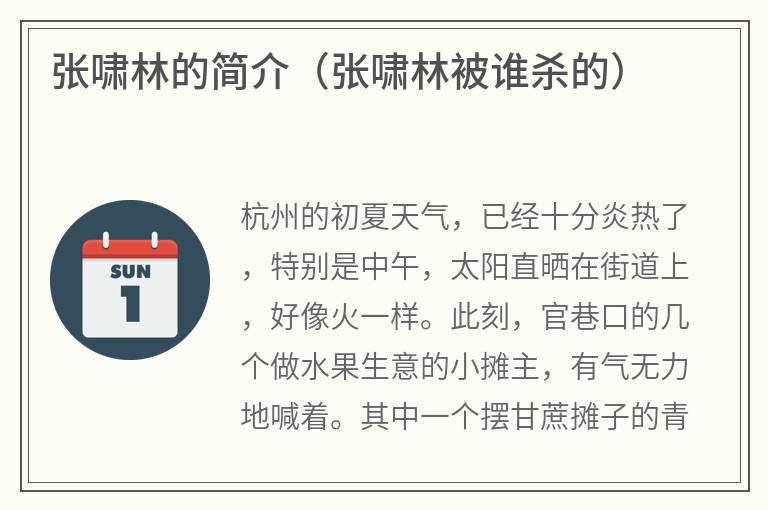
张啸林的简介(张啸林被谁杀的)
旁边有个叫“小浦东”的卖生梨的小贩,就劝他说:“喂,你急什么?不是天天这样等吗,等太阳落山吧!”接着那小浦东叹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杭州这个小码头,也没有多大发展,我打算过两天就回上海去,到十六浦找找我师兄‘莱阳梨’。他比我有办法,你要去就跟我一同去。”
那小贩叫张啸林。他听说小浦东要到上海去找师兄“莱阳梨”,忍不住摇着头:“莱阳梨——哈,想来也是做水果生意的了,半斤对八两,没花头!”
小浦东微微一笑说:“这是过去,可人家现在不同了!他靠师傅麻皮金荣帮忙,早已不做水果生意,贩福寿膏去了!”
张啸林懂得贩这东西虽然发财,但要担很大的风险,小浦东的师兄莱阳梨既然能够做这生意,那肯定不简单,于是对小浦东说:“这还差不多!”两人就这样议定了。
过了几天,两人到了上海,原来小浦东说的莱阳梨,就是杜月笙。此人过去确实在十六浦摆水果摊,后来因拜在黄金荣的门下,靠烟起家,如今已是一方的“土地”。
接见中,杜月笙与张啸林略一交谈,晓得他在杭州并无什么势力,讲话粗鲁,派不了什么大用场,他敷衍一阵以后,想一想,不如留一份人情,举荐他去见黄金荣,杜月笙为张啸林准备了一份厚礼,择日去拜见黄金荣,黄金荣见了这么厚的一份拜师礼,又是杜月笙引见,就高兴地收了这个徒弟。拜师后,黄金荣摆出一副老师架子,关切地问道:“啸林,你到上海有什么打算呢?”
张啸林毕恭毕敬地说:“我到上海,人地生疏,恳求老师指点,赏碗饭吃。”
黄金荣盘问下来,觉得这人是个十足粗人,不觉有点踌躇,又一想,反正自己手下弟兄如麻,也多不了他一个,这人看来还直爽,就说:“上海这个地方条条马路都有我的手下人,我看你跟我一个徒弟在那里管管事,如果有什么为难处,你只管来找我吧!”
张啸林跟着师兄到了下处住下,一了解,才知道“管管事”,就是向马路小贩和过往的外地客人敲竹杠,对一些商店“摆颜色”,要他们出“月规钱”。一条路上由几个“兄弟”包下来,三一三十一,日子还过得不差。张啸林原来在杭州也是这种青皮流氓,不过他那时没有老头子,闹出事来,只好自认晦气。这次有师傅撑腰,兄弟相帮,况且上海市面要比杭州繁华得多,只要脸皮厚手辣,没本钱的生意有什么难做呢?
一回生,二回熟,从此,张啸林就在上海法租界的马路上“立足”了。
张啸林因为胆子大,果断,不多久,那帮小弟兄对他颇为服帖,居然成为一条街上的“大亨”,绰号叫“小杭州”。张啸林这人有一个特点,讲究江湖上这一套,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而且,对孤身女子不欺侮。这倒不是他惜老怜弱,他认为:“好男不和女斗”,从弱女子身上敲竹杠是没有本事的,因而,他专拣硬的碰,这样便免不了常常发生斗殴,好在巡捕房里的头目就是他的老师,自然无理也变成有理。几次下来,“小杭州”的名声扬出,有些店家反而要寻他来作“保护人”了。
这天他走过一家旅馆门口,觉得吃力,就停下来休息,恰好迎门柜台边有条长凳,他就一屁股坐下歇口气,不料忽然听到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喊他:“张先生,请用茶!”
张啸林抬头一看,认出这女人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娘。她年纪不过二十开外,瓜子脸,细细的眉毛,长得虽然算不上漂亮,但十分匀称。她头上戴着一朵白花,满身浅灰色服装,显然是在穿孝,张啸林记起这家旅馆的老板姓樊,上个月得了霍乱传染病死了,老板娘是给她丈夫穿孝,于是接过茶,欠欠身说:“谢谢老板娘!”
樊家老板娘笑着说:“张先生说哪里话,请你都请不到,你在我门口坐坐,我就沾了你的光了!”
张啸林不解其意,老板娘叹了口气:“常言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那个短命死鬼狠心抛下我走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开了这样一家旅馆,南来北往的客商,天天上门的军警,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应付得了呢?恨起来想把这旅馆关了门,可是我吃什么呢!没办法只好暂时对付着。”
张啸林听了颇为同情,询问一下,知道樊家老板娘也是杭州人,大家都是同乡,他拿出好汉架势说:“樊家嫂嫂,你不必烦心,我们都是出门在外的同乡,只要你不嫌弃,要我帮忙照应一下,你只管吩咐。”
老板娘向他含情地一笑,说:“张先生,你不知道,这店虽小,麻烦却多!外面有人三日两头来打‘秋风’不说,就是旅店里的客人有时也难对付,他们三顿饭要吃,总说菜不好;还嫌被子脏、蚊子咬,睡不着;离店时房钱又不肯爽爽快快地付清。真气死人了!张先生,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麻烦你隔两三天晚上到小店里坐坐,吃杯薄酒,只说是我表哥,他们知道你的路道,就不敢放肆了!”她一边说一边用一双深情的眼睛瞄着张啸林的面孔。
张啸林完全被她的神情征服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直到老板娘问他这样可好,他才醒悟过来,忙点头说:“樊家嫂嫂,这……这点事我应该效力!”
从此,张啸林每天傍晚都到樊家寡妇店里走走,有时吃杯酒,有时吃餐饭,果然,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就销声匿迹,店里终于安定起来。
有一天,天正落着雨,樊寡妇想他大概不会来了,就在账桌旁和账房先生谈天。
那账房先生是个绍兴人,脑子十分灵光,他看出寡妇对张啸林有情,于是就试探说:“老板娘,这几个月来,有张先生来帮忙,省掉多少麻烦,这种行业没有个路道宽、兜得转的老板,是不容易开好的!”
寡妇叹了口气说:“谁说不是呢?这一阵子幸亏张先生帮衬,他一来,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今天下雨,也许张先生不会来了!”
账房先生神秘地一笑,迟疑了一会说:“张先生这人蛮爽气,做事也上路,而且比原来的樊先生能干得多!真是难得。我看准来,你还是准备点晚饭菜和老酒吧!”张樊寡妇脸腾地红了,一声不响。
正在这时,张啸林撑着一把雨伞来了,他笑着说:“这雨越下越大了!樊家嫂嫂,你大概猜我不会来了吧?”
樊寡妇一听,脸又红了,本来她口齿伶俐,此时却窘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她才说了一句:“你不要叫我樊家嫂嫂,我名叫嫣红,叫我名字好了!我给你去炒个菜,下雨天寒,喝杯酒去去寒气!”
菜一会儿炒好,一盆炒猪肝,一盆油爆虾。张啸林一口口喝着老酒,樊寡妇坐在他对面痴痴地望着他。这时屋外雨越下越大,张啸林已有七分醉意,他站起来,有点立脚不稳,樊寡妇慌忙扶住他,在喉咙底说:“雨这样大,你就在这儿住下吧!”
不久张啸林就正式搬进店里,成了这家旅店的新老板,招牌加上“啸记”两个字。
张啸林成了旅店老板,不但店中那两个伙计不敢得罪,就是那些难伺候的“客人”,也不来纠缠了。因为这店开在法租界,恰恰是张啸林的“老头子”黄金荣当巡捕头子的地界。张啸林又有一帮小兄弟,如果谁来取闹,就随时可以来“摆平”他,这样,店就稳如泰山,那嫣红如今成了张老板娘,也就安享清福,做她的女店东和内当家了。
光阴过得很快,又是第二年的夏天。有一天,店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年纪不过四十开外,身穿藏青哔叽长袍,脸孔清瘦,举止大方,随身只带了一个公文包。他问有没有清爽的单间,账房先生不敢怠慢,连忙领到后进一间厢房。客人看了看,觉得还满意,就住了下来,吩咐伙食要好一些,数量并不一定多,账房先生连声答应,退出屋外让客人休息。
账房告诉张啸林:这客人似乎是吃公事饭的,循环簿上写明由安庆来沪,大概是路过上海,但弄不清他到哪里去。
客人一住有二十来天,既不见他出去拜客,也不见有人来找他,他每天吃过饭,只到账房问一声有没有安庆来的信,听说没有信,就皱皱眉头,转身回到房间里去,不再出来。
这天账房先生对张啸林说:“住在厢房那位客人自从进店从未到柜上来交过钱。而且伙食每天要鸡鱼肉,不断换花样,算来也欠了二三十元钱。我请他先付一点,他却发火了,说‘我会欠你们店钱!我现在又不走。’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灰。”
张啸林一听就冒火,气冲冲地到后厢房去找那个住店的客人。
客人看见张啸林气冲冲进来,知道他是来讨钱的,便淡然一笑,问道:“老板,你大概是怕我赖账吧?我想我这人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张啸林看见客人并不怕他,而且举止从容,没有一点慌张的意思,他思忖这客人恐怕有点来头,于是露出笑容说:“客官,你猜错了!刚刚账房先生不识进退,多有冒犯。我虽是个粗人,但爱交朋友,客官如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管吩咐!”
客人见张啸林这样说,知道这位老板颇讲江湖义气,心里欢喜,于是说:“张老板,你既然爱交朋友,我不妨直言相告。我在安庆当过一任小官,卸任以后,知道我父亲的朋友在北京段祺瑞手下十分得意,我去信托他谋个差事,如今已得到回音。来沪后,想买一些礼品进京。上街看看,差的拿不出去,若买珍贵些的,一凑钱就不够了,故此写信回家。信去了有十余天,一直没有回复,故此在宝店耽搁了些时日。张老板你放心,钱一汇到,贵店的房金饭费分文不会短少。”
张啸林心中暗暗思量:这人是进京谋官的,肯定大有前程,来日方长,这个朋友应该交,于是借了200元给他。
客人十分感动,双手拱拳向张啸林说:“张老板,你真够朋友,我只要谋得一官半职,定然厚厚相报。”
客人离开上海北去,已经两月有余,却毫无音讯。张啸林有时候问起账房,那位客人有没有来信,账房总是摇摇头。张啸林想:这批读书做官的人,就是不讲信用,我资助你上路,没有书信也要托人带个口信,看来这两百只大洋“放白鸽”了!
这天,他心里懊恼,与几个小兄弟到馆子里吃酒,回来时已经带几分醉意。快走到店,只见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张啸林以为出了什么事,连忙分开众人走进店去,看见门口坐着两个身穿警服的人,焦急地在四处探望,账房先生却站在旁边,低下头不知和那两人说什么。张啸林心中怀疑,连忙走过去问账房先生。账房先生看见张啸林,连忙高叫:“好了!好了!张老板回来了。张老板,这两位老总在等你呢!”
那两人一听这人就是张啸林,连忙站起来向他举手敬礼,其中一人开口说道:“张老板,我们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副官,奉命给您送上这件公文。临行时总文案交代,派令一定要面交张老板亲收,并面告一切。”
张啸林被弄得糊里糊涂,幸好账房先生在旁边,见来人既然这样说,便喊声:“请!”两人便跟张啸林走进一间厢房坐下。另外一人取出个大信封来,这信封要比普通大一倍,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印。他双手递给张啸林,然后拉长声音说:“恭喜张总队长,这是护军使大人的委任状!”
张啸林接过信封,转手递给账房先生:“你看看。”账房先生接过一看,马上说:“恭喜老板,这是淞沪护军使大人委派你为淞沪水上缉私总队总队长,你当了官了!”
张啸林不知这官到底管什么?又有多大?但当官总不是坏事。账房先生见他不懂得应付这一套,便凑到他耳边说:“送委任状是个喜事,要请这两位吃一顿,还要送一点礼。”于是张啸林就叫账房先生去吩咐厨房,从速准备一桌丰盛酒席,款待两位副官。
席间那位送文书的副官说:“总文案从安庆经上海去北京时,曾在张总队长店内停留。现在北京政府推荐他担任淞沪护军使的总文案,除了护军使大人,他是第二把交椅,总文案深知张总队长行侠仗义,因此请护军使大人派你担任这个职务,以后,我们也要请张总队长多多关照。”
张啸林到此方知这就是在店内住了多天,借了200元钱去北京的那位客人,心想:这样说,他已经到上海来做官了,但不知这总文案和我这个缉私总队长到底都是什么官?他来到上海一不见我,二不还钱,弄这样一张纸头算什么名堂!但看张这两位副官对自己这么恭敬,其中总有道理,虽有满腹疑窦,却又不便细问,席散后,就送了20元现洋给两位副官作谢礼,把他们送走。
副官走后,张啸林把账房先生找到屋里商议,这事如何办理?
账房先生笑着说:“老板,我劝你这店不必开了!你可知道这水上缉私队是什么?除了江海关以外,它就是上海各条水路警察的总领头,但凡进出上海河道的大小船只,都要经过缉私关口上税查验才能放行。如不遵令,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扣押船只。这关口的进账就大了,你老板明天接任,那各路分队后天就会来孝敬你。听说过去有人活动当三个月缉私队长,花上近万元的钱。这回,总文案念你行侠仗义,就一下送你这么个肥缺,实在是情重如山。因此,他过去住店的事情,你就千万不要提起。”
被账房先生一讲,张啸林顿时心花怒放,这样的美事,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转而一想,又犯起愁来。他对账房先生说:“不瞒你说,财谁不想发,但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对做官这条路,我是一窍不通!”
账房先生笑道:“张总队长这是多虑了。你上有总文案帮忙;下有弟兄们和黄老板撑腰,谁敢奈何你!现在无非少一个通文墨的人,给你出谋划策罢了。”
他沉默了半晌,又说:“不瞒老板说,我先父就是过去衙门中的师爷,我学了一肚子办公文的本事,在肚皮里搁煞,十分可惜。如果老板信得过我,我一定效犬马之劳。现在不兴叫师爷了,就叫秘书不会错。”
张啸林拍拍脑袋说:“你看,我这个人真是一时糊涂,就没有想起你先生,你准定跟我去,我什么都放心了。”
从此,张老板当上了淞沪水上缉私总队的总队长。这缉私总队是上海对水上船只敲竹杠的机关,有人说过缉私队长的进账不是用一天来算的,而是用一个钟头来算的。
张啸林到底每小时进账多少钱?但不久他就在法租界华格臬路造了十分考究的洋房,坐上了汽车。
这时杜月笙也和他来讲旧交,称兄道弟,十分亲热。这倒并不是因为张啸林一下阔了,转而来奉承他,这里面却另有一段原因。
原来当时上海的华界都属淞沪护军使署的势力范围。杜月笙做的生意虽然在租界里,可是运烟膏的船只车辆还要经过租界以外的地区,如果得罪了他们,他们手下有的是军警,“地头蛇”是斗不过“枪杆子”的。现在张啸林做了淞沪护军使署下面的总队长,而且又管着缉私的重要差事,杜月笙当然反而有求于他了。于是,张啸林一下子身价百倍,大亨们无不刮目相看了。
张啸林懂得要在上海滩上混下去,单靠这总队长还不行,还须在青红帮内有一定辈份。这件事又惊动了黄金荣。
原来黄金荣不是正式青帮,过去他只借这个名头,广收门徒,但青帮的人是不承认的。他如今听说自己的门生张啸林要正式去找青帮拜师,到头来变成“假师真徒”,岂不叫人笑话?这时青帮辈份最高的张仁奎是“大”字辈的。这张仁奎做过一任通州镇守使,刮饱了地皮回到上海享福。黄金荣想:只有拜他为师,才可取得“通”字辈的资格。他花了10万元钱孝敬张仁奎,要张仁奎认他是“通”字辈的弟子,并且主动把张啸林和杜月笙两人请来,说明为了使徒子徒孙们服帖,三人同拜张仁奎,在帮里自己做个大师兄。
杜月笙和张啸林听黄金荣一讲,好不高兴,就当场讲了一番客气话:“我们面子上是师兄弟,实际上你还是我们先生,况且长兄如父,我俩仍像过去一样的对待你。”
张仁奎对白花花的银洋当然欢迎,而且收了这几个徒弟,上海滩上就更加兜得转了,于是择了个日子,就在海格路湖南路他的家中,以做生日为名,大宴宾客。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都到场。在宴会中,张仁奎胸有成竹地向他的弟子们介绍说:“我在上海靠大家帮忙,十分感谢!”说着,又指着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说:“这是你们通字辈师兄!大家互相照应,使我们洪门香火兴隆!”
在场的那些帮内的徒子徒孙,明知这事是财神爷的力量,可是这三人已经通了大半个上海滩,谁敢说个不字呢!
从此黄、杜、张成为上海滩上有名的三大亨。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控制着租界,市民们无不望而生畏,言之咋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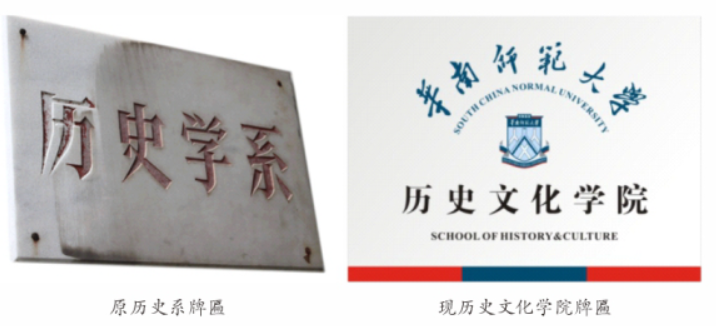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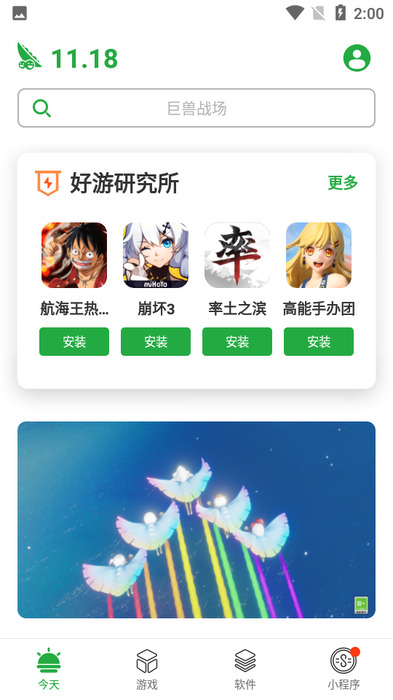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