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那饱受屈辱的血与泪,近代史上更值得人深思的反而是那些曲折艰辛的探索之路。毕竟,血与泪只是证明了那时的无能,而历尽艰辛却仍然坚持不懈的探索求存才是民族国家长存于世的出路。
不过看看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改革之路,按照我大学近代史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太心塞了。就单说晚清的这一套变法操作,就不由得感慨——变法是好事,但关键得走对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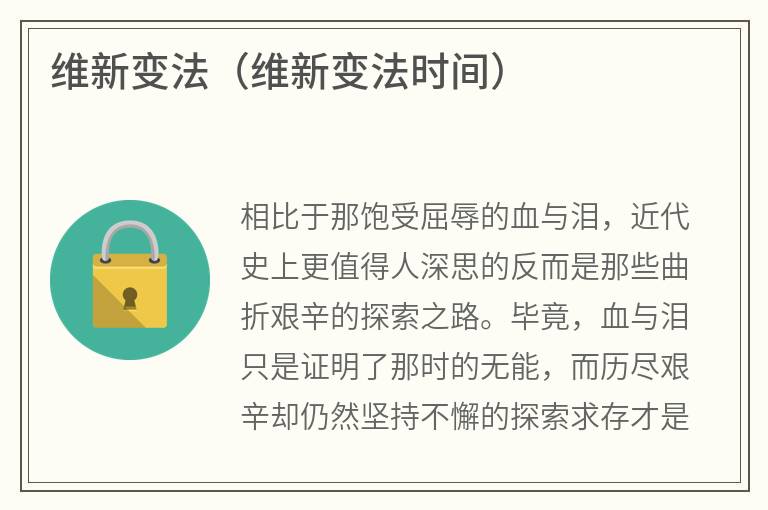
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时间)
晚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应该就是戊戌变法了,相比于之前那个换汤不换药的洋务运动,康有为一伙人的提议确实是触及到大清灵魂的。毕竟如果按照康党的想法,整个清朝的上上下下都要变,而且最终要变成一个新式帝国。
这倒也不奇怪,远的不说,就在大海的彼岸,我们的近邻岛国日本,就通过维新变法走向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东亚的西欧国家。
模板就放在这,而且自身已经漏洞百出、残破不堪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变呢?
所以维新党派的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一干有志人士就开始筹措如何变法救国,让大清重回巅峰时刻。
初衷很好,但仅仅有初衷是不够的。变法之所以可以成功,不仅在于新法有多好,还要考虑到如何才能拿下旧势力,为己用或是消灭他们,从而去保障一个社会的相对稳定性。
但很多变法者并不会考虑得这么周到,毕竟比起破天荒的想东想西,实现自己的抱负要更重要一些,而康有为就是这一种人。
1895年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考上了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初六日又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当时光绪皇帝看过此书之后,一时间心潮澎湃,认为康有为乃是振兴大清的栋梁之才。
深受鼓舞的康有为大笔一挥,便拟定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科举、改书院、废淫祠,保护工商业,要求重练海陆军。
看上去很光鲜,但其实内藏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科举。
康有为很有想法,他认为科举出来的举子只知道做空学问,不懂得振兴大清,这倒是也不假,确实,自打元朝以后,儒家的“腐败”气息愈发的浓厚,出现了大批只会空谈、不切实际的腐儒。而在清代,因为先前大规模的文字狱,清代的腐儒数量已经达到了历代最高。他们霸占着官场,给官场注入的都是些迂腐之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废除科举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科举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一直作为中华帝国的官员选拔机制,其身后的受益群众之基数不可言喻。而康有为却说废除就废除,没有想过如何安置那些试图通过科举谋求官道的读书人,致使大批寒门弟子间接失业,加剧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扩大。可能有人觉得读书人而已没什么可怕的,但别忘了就在五十年前,广西刚刚出了个洪秀全。
此外要命的还有,废旗人和绿营,一样也没有说给个什么失业保障,这也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毕竟作为大清帝国的主要维系部队,绿营军有着规模庞大的数量,动辄以大批量的裁撤,却不给这些离职职业军人以合理的社会保障,其危害之大,自不必多说。
两条下来,表面上戊戌变法是增进了大清的实力,其实却埋下了两颗隐患。
更不要说在商业税收方面,康有为走起了乌托邦路线,认为税收的最高境界是无税,这属于典型的空想主义。
说实话,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搞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是支持的。但是越到后面味道越不对,西太后也就开始出面干预了。原本只是说让维新派不要太出格,康有为却因此以为老太后要阻挠变法,于是串通光绪皇帝准备发动政变,结果被袁世凯告密,最后维新派四散而逃,这个心怀大志的康有为也是远逃国外,留下了一腔热血的谭嗣同等人替自己送命。
照此看来,假如那个“万恶”的慈禧没有阻止这场变革,那大清怕是就见不到20世纪的太阳了。只能说路子没有走对的理想,本质来说也是错误的。
现实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并不是想当然的正确,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是要考虑大众的口味,妥善处理好即将面对的社会矛盾。
相比之下,几年之后的清末新政就要显得成熟得多。
庚子国难后,大清每况愈下,如此危机之下,担心命丧他手的西太后终于下定决心搞新政。而这个重任,便落在了袁世凯的头上。
不得不说,相比于康有为的理想主义,袁世凯则更加务实。同样是教育改革,袁世凯并没有直接斩断科举制度,而是双管齐下,一面建立新式学堂,推广免费教育;另一方面广招才识渊博的读书举子担任新式学堂的国学老师,算是解决旧式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抵触情绪。
除了安置旧学,袁世凯也大力推广新学,尤其重视女子教育,一度大力招聘留洋女教师,向社会招收女学生,可以说为近代史上的男女平权尽了一份大力。
在都统天津的时候,袁世凯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这一举动可以说带来了两个积极影响。第一,随着新军的兴建,老式的绿营军面临着裁撤的命运,而大批的失业军人极可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而警察队伍的成立,可以将绿营军中的精壮力充分吸纳,与新军编制相互呼应,有利于大清的国防和治安。
第二,因为《辛丑条约》中明确规定大清不可以在天津驻军,这等同于清帝国直接失去了对天津的管辖权,而警察制度的建立恰好也是钻了这一条文的空子,一度成为了清帝国在天津提防列强的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兴金融、建工厂,更不必多说。
一直到慈禧去世,整个大清在袁世凯的“折腾”下逐渐走上了正路,综合国力也愈发地强大起来。如若不是那帮王爷瞎胡闹,加上一场清末股灾,兴许革命党在1911年还没有革命成功的机会。
这就是说,变法这件事,我们不能只看出发点,不能只看理想有多崇高,关键看能不能走对路子,能不能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历史上多不胜数的维新变法,大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并非新法不好,而是主要矛盾终归大于次要矛盾,现实问题远比理想要复杂的多。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所能学到的,只有以史为鉴,不至于重蹈覆辙。然而历史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一点——大多数人,是不长教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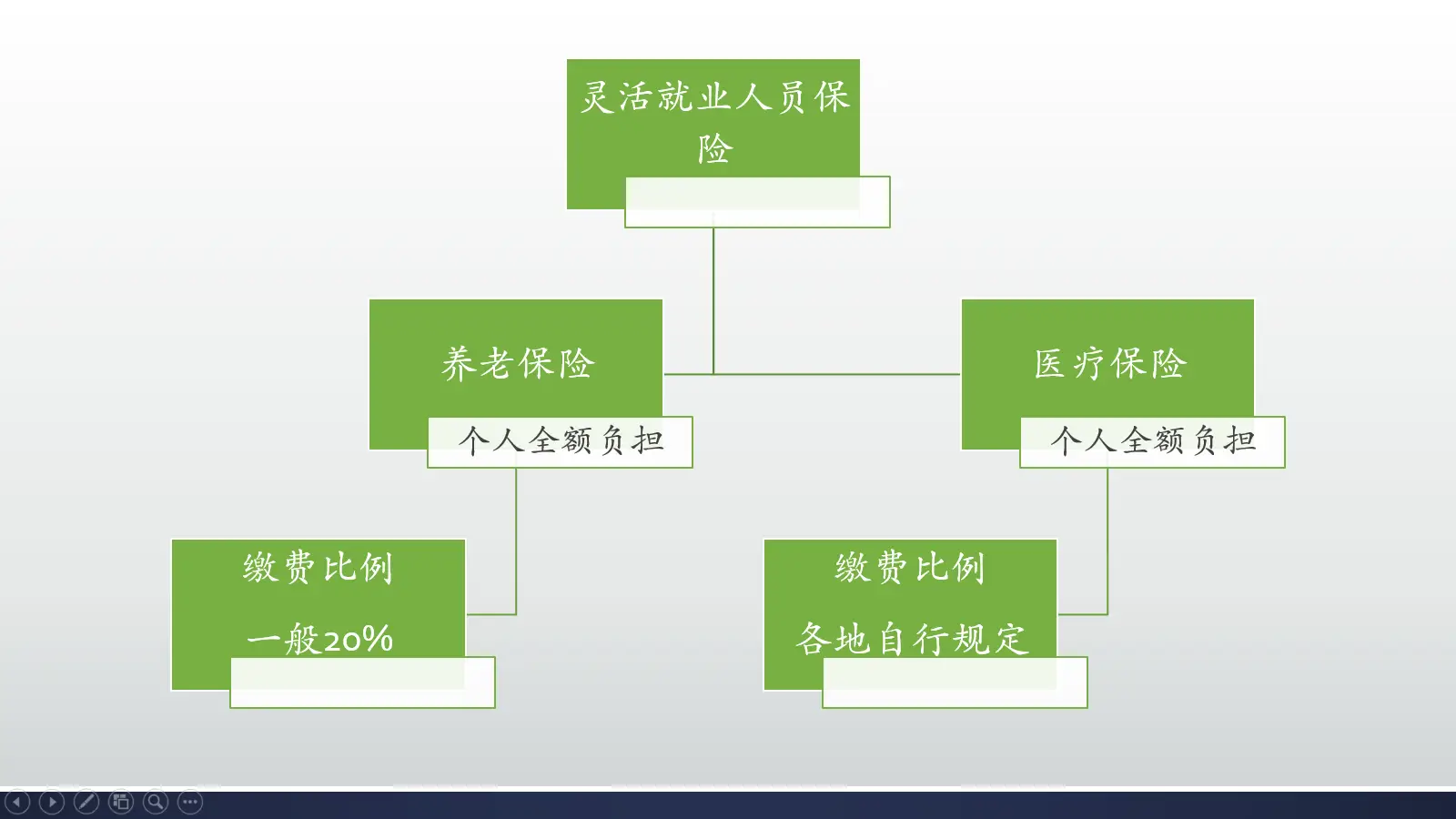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