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知识分子伉俪,知名度最高的几对CP里,一定有法国哲学家萨特与波伏娃(也译作波伏瓦)。萨特阐释存在主义哲学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成为人手一本的畅销“圣经”;波伏娃的《第二性》更是女权理论的开山代表作;而他们两人的终身“开放式关系”也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八卦趣闻......
简而言之,萨特与波伏娃几乎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方式。但这样的一对知识分子伉俪,也存在着后脑勺上的另一面。首当其冲的,是他们与挚友加缪的冲突与决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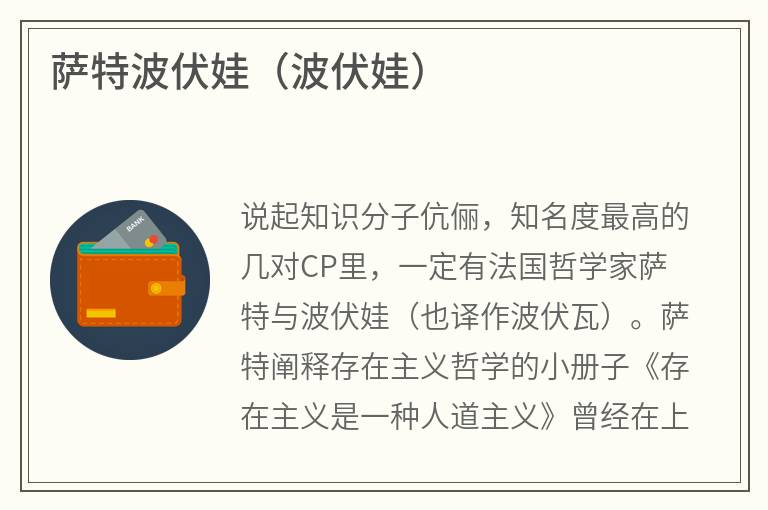
萨特波伏娃(波伏娃)
最近,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作品《站在人这边》及《猎人的一年》中译本出版。在《站在人这边》这本代表性随笔中,米沃什记叙和素描了诸多历史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及与他相交的知识分子轶事。今天,进一步追溯他跟萨特、波伏娃、加缪等知识分子之间的故事,通过他们的交往,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他们的传奇友情、这份友情如何走向决裂,更可以再一次思考,那些引发他们观念冲突的重大历史与哲学问题。
撰文|周郎顾曲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Mi?osz)是个克制的诗人,但在《米沃什词典》里他罕见地对萨特(Jean-PaulSartre)和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开炮。他说:
米沃什自称“小地方人”——“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他接受不了“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看不惯以萨特和波伏娃为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米沃什对他们的不满还和政治有关。战后,波兰在政治交易中沦为牺牲品,斯拉夫人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下,酿就了膨胀的爱国主义,也驱使一批诗人流落他乡,米沃什就是政治避难的其中一员。但在五十年代的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等国家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们对波兰人的苦难缺乏感同身受,用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目光打量着东欧世界。米沃什的政治避难没有为他带来道德的优越性,相反许多人不理解他,当他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逃时,一位法共的精神科医生说:“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
独居巴黎,遭受冷眼,五十年代初,米沃什把他的心声写进了《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试图与他者对话,也是米沃什跟自己的对话。他大胆谈论东欧知识分子如何摆脱束缚,也批判了法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尖锐的批判,让这本书出版并不顺利,多亏加缪(AlbertCamus)和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的帮助,这本书才在西欧知识分子群体里引起关注。
波伏娃。
米沃什提及了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墨提宾”药丸,这个词语出波兰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奇(Stanis?awWitkiewicz)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凯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这个故事犹如一个恐怖的隐喻,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巴黎知识分子还迷恋着苏联式的神话,米沃什已嗅出不安的气息,小说中那个战无不胜的帝国和“墨提宾”药丸,对应着彼时被扭曲的现实。
他的“危言耸听”与当时巴黎的意识形态气氛相左,所以不受欢迎。但也正是在这孤独的环境中,加缪伸出援手,令他倍感温暖。他曾说:“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并且称赞加缪“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无论是文学还是精神上,米沃什都视加缪为典范,但萨特和波伏娃却曾对加缪恶语相向,这一点深深刺伤了米沃什的心。
米沃什和波伏娃没有私人交集,也谈不上私人恩怨,他憎恨波伏娃,主要是替加缪鸣不平。这一点他在《米沃什词典》里说得很清楚:
《名士风流》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者:许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
《名士风流》是波伏娃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她杂糅了法国知识分子们对苏联劳改营的论战,通过小说影射现实。小说中,主角亨利和罗贝尔在“苏联劳改营事件”上出现分歧,亨利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却被误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遭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抵制。罗贝尔支持苏联,但感到自己又不能适应它的生活,由此陷入精神困境。(情节介绍参考:《名士风流》上海译文版)亨利和罗贝尔的原型,部分借鉴了萨特和加缪,米沃什不满的就是波伏娃对萨特的拔高、对加缪的诋毁。
而关于萨特,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的“加缪词条”中补充道:
米沃什讲述的这件事,就是法国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萨特与加缪决裂。他们曾是好友,被外界视作存在主义的巨擘(尽管他们未必认同这一标签),却在1952年决裂。《周六晚报》与《法兰西报》的头版头条披露了他们决裂的细节:《反抗者》的出版引起萨特及其友人的不悦,萨特约好友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Jeanson)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的《反抗者》,“措辞要最严厉,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
萨特与波伏娃。
1952年5月,让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达26页的评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让松在文中抨击加缪“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奉行懦弱的人道主义”,“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蔑为‘令人作呕的冤案’”,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最后定论道:
加缪读到这篇抨击文章后很失落,他对女友直言,自己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1952年8月,加缪回了一封长达17页的信,这封信同样发在《现代》杂志上,信的开头如是说:
萨特则回应道: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披露:早在1946年,这两位哲学家就有了观念上的分歧。那一年,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声援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批评当时的苏联把暴力和谋杀合法化。此举引起萨特及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异议。梅洛·庞蒂撰写《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一文回应加缪(这篇文章被收入《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它也是对阿瑟·库斯勒的随笔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的回应),并且把加缪称作“革命的叛徒”。
加缪读罢愤然,在鲍里斯·维昂(BorisVian)家的一次晚宴上和庞蒂吵了起来。这次不快引起他们共同友人的关注,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充当讲和角色,波伏娃则公开站在庞蒂一边。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作者:(美)罗纳德·阿隆森
译者:章乐天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这件事持续到1947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文《什么是文学?》,批评加缪在《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中的写作姿态。1948年10月,他又发表文章《饥饿已经意味着渴望自由》,指出:
1949年,作家戴维·卢瑟(DavidRousset)在巴黎成立了苏联集中营问题调查委员会,此举引起法国《红色人道报》的批判,后者否定苏联存在集中营,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名发表文章《我们生存的日子》,声援《红色人道报》:“即使经历过集中营的体验也不能绝对地作为决策的依据”,“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苏联的话,就是想要抵消资本主义所遇的罪恶。……这样的话,是要把无产阶级投入绝望的深渊。”这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萨特、庞蒂、波伏娃和加缪的裂痕,论战的火苗持续升温。
加缪捍卫自己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对崇高的革命幻想保持怀疑,对“正义”、“真理”等大词也十分审慎,当身边人歌颂赞歌,他总是用冷峻的笔调指出黑暗,不承诺任何美妙的乌托邦。在随后出版的新书《反抗者》中,他直言:“如今真相大白,我们必须把某种东西如其所是地称为‘集中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不该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礼。”
著名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
《反抗者》的出版,令加缪成为众矢之的,也直接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萨特坚持他对苏联的辩护,批评加缪的人道主义是另一种虚伪。他不支持加缪描写劳改营的做法,“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后来,他又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
萨特不认可加缪的道德要求可以完全运用到现实政治的语境。在1958年的谈话中,他解释道:“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强加的一种限制,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则人就成了‘君子’,就无法做出政治行为。”为了现实的政治,萨特选择克服道德主义,加缪则警惕这种“正义”,在他的字典里,“母亲先于正义”,“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加缪传》
作者:[美]赫伯特·R.洛特曼
译者: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正是因为萨特对苏联的态度、对加缪的讽刺以及他对东欧民众的轻佻,让米沃什对他缺乏好感。而这也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拒绝萨特召见的原因。索尔仁尼琴直言不讳地说:“他如果不是萨特就好了。……我们是非常不喜欢、不接受他的。”
相比在法国知识界呼风唤雨的萨特,加缪更能赢得米沃什和索尔仁尼琴的欣赏。这不仅是因为他殖民地的出身、贫穷和被轻视的经历更能引起前者共鸣,也是因为他在战后法国知识界充满幻想的背景下,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披露苏联劳改营的事实、支持一部分东欧和苏联的流浪作家。
但在五十年代的巴黎,加缪是少数,萨特是多数。《加缪传》的作者洛特曼说:“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以至于加缪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为的是摧毁我。”
加缪“站在鸡蛋一边”的态度打动了米沃什的心,即便在他最艰难的岁月,米沃什也坚定地捍卫这位“柔软的反抗者”。半个世纪前,巴黎最优越的知识分子讥讽着加缪的选择,奔赴铸造神话的行列,米沃什则一度担忧,“墨提宾”药丸会成为现实。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历史也在重审着他们的论战,给“哲人王”开着玩笑。时过境迁,若是萨特、加缪、波伏娃和米沃什还能在天国目睹如今世界的种种变化,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思想变迁?
本文参考资料:
1.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2014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201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周泽雄:《加缪:睿智的写作者》,2016年2月,经济观察网;
4.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2005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1999年12月,漓江出版社;
6.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2016年5月,中信出版社;
7.阿尔贝·加缪:《反抗者》,2010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8.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士风流》,2013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9.文汇报:《加缪与萨特的恩恩怨怨》,2018年3月;
10.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2013年6月,华夏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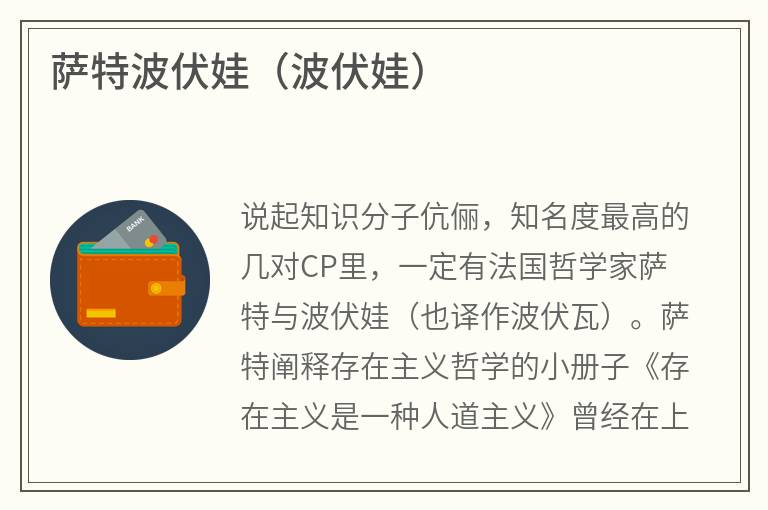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