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天津已近初冬,这天还下着小雨,位于南马路居士林的诵经仪式照常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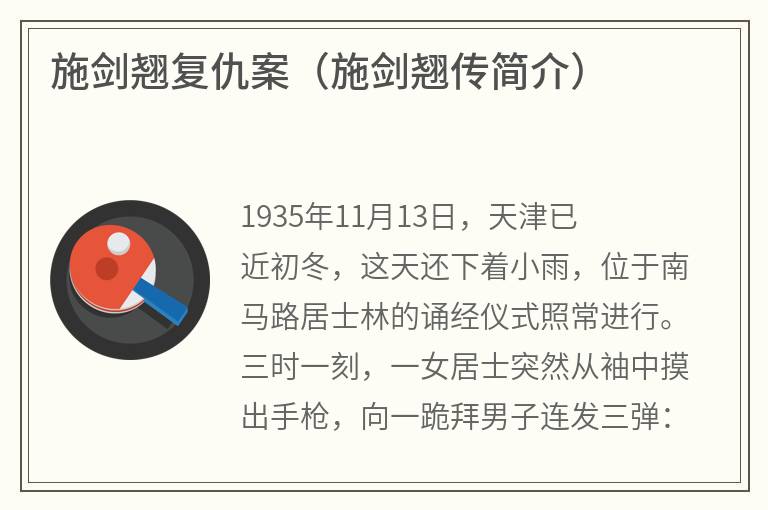
施剑翘复仇案(施剑翘传简介)
三时一刻,一女居士突然从袖中摸出手枪,向一跪拜男子连发三弹:第一颗子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第二颗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颗射中腰部,前胸透出,男子当场毙命。
被打死的男子正是直系军事首领,有「五省联帅」之称的孙传芳。不过,他在八年前已退出江湖,并皈依佛门。
而凶手名叫施剑翘,时年30岁。行刺成功后,施剑翘泰然自若地散发自己所作七言律诗一首、文字声明一份及自白书《告国人书》一封,随后归案自首。
这起案件看似不难断清,却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在两次上诉后,南京最高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从轻处理的最终判决。两个月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又被国民政府的特赦令事实上推翻了。
施剑翘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及判决过程的戏剧性,让此案成为人们眼中的「民国奇案」。
但是,不同于一些人将这宗谋杀案当作历史奇案或民国乱世的注脚,美国现代中国史专家林郁沁(EugeniaLean)却在《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中选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个案件。她聚焦于这个案件所引发的公众反应,并解析这些反应中所包含的现代因素。
在增进人们对中国现代公众的认识方面,《施剑翘复仇案》无疑是成功的。本书在2007年出版时不仅让不少读者引为惊艳,而且也立即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费正清奖,这是美国东亚研究界的极大荣誉。
那么,获得如此赞誉的历史著作,究竟如何讲述中国城市公众的历史命运?施剑翘复仇案又对我们今天理解公众、大众媒体、消费主义文化、威权政治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哪些启发?
开始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回到施剑翘复仇案的事发现场。
01.
「施剑翘复仇案」始末
各位先生注意:
1.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2.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3.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4.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以上即为施剑翘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声明。刺杀成功后,施剑翘随即将这份文字声明散发给现场的目击者,随后投案自首。
报道称施剑翘被捕时「态度从容,俨然无事」。
施剑翘提供的这些意味丰富的材料很快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当时闻名全国的大报《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几乎都对该案的进展进行了跟踪报道。事发当晚,她的自白书就被全文转载。
佛堂禅院、孝女复仇、军阀毙命等元素,也让这一刺杀行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一时间报纸副刊上的连载小说,广播里的评弹如潮水般涌现,各大剧院也迅速搬演这一故事的改编剧,并以此剧目相互竞演。
据当时杂志《福尔摩斯》的记载说:
「杀人小姐施剑翘自为乃父施从滨复仇,刺杀孙传芳后,一时轰动全国,大快人心,各地戏院,均争相竞排侠女复仇记,号召力之大盛极一时。」
富有意味的是,当时的小说、剧作并非如实转述这个时事案件,而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化改编。在这些类似于「公案」、「武侠」的通俗小说中施剑翘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是一个典型的女侠。
而被射杀的孙传芳,则和施剑翘的父亲是「盟兄盟弟」的结义关系(其实纯属虚构),因此施剑翘不仅是要报杀父之仇,还要惩罚孙传芳这位盟叔违反了「兄弟情义」。
此外,施案题材的小说还有意无意地遵循「恋爱小说」的套路,大书特写了施剑翘如何自行解除了一桩有丑闻的包办婚姻,并自主安排婚约的经历。
在这方面的叙事中,施剑翘依然果敢、侠义,同时被视作当时新女性的代表,即使这种「新」依然不免其新旧杂糅的色彩。她在与未来丈夫施靖公初次见面时,就慨叹世上缺乏英雄,说她希望要一个有着侠肝义胆的绅士做她的丈夫。
施靖公则通过肯定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等侠义理想是人类的自然天性而打动了施剑翘的心。施剑翘为此竟然主动向施靖公求婚。这个在当时尚属反常的举动,被大多数小说所赞许,因为这既推进了复仇的目标达成,又果断地实践了新时代女性自主选择婚姻伴侣的权利。
总之,正如林郁沁在本书中所指出,一个道德主义英雄与一个果敢的新女性,就构成了大众传播中人们愿意接受的施剑翘形象。
尽管施剑翘在案发后以及审判间隙的几次新闻发布会上都有意借助媒体争取舆论同情,但她实在无法预见媒体会把她的复仇故事挪用为一场持续一年的公众狂欢。
就在这添枝加叶与众声喧哗的公众激情中,施剑翘案开审了。一审,天津地方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二审,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但不到一年后,施剑翘又被国民政府特赦。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施剑翘案引发的持续轰动?这个轰动背后民众所表现积极的消费、参与热情,具有社会政治意味吗?
这些问题,被林郁沁用一个核心概念一一解开。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公众同情」。
02.
「公众同情」与情感型公众
所谓「公众同情」,其实是指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同情」在中国已获得了一种明确无误的「集体」内涵,因此「公众同情」就被林郁沁定义为「植根于群众情绪并通过媒体的轰动效应而形成」。
据此林郁沁指出,正是这种新型的公共道德情感,形塑了一个具有高度参与性、批判性的公众群体。
这个观点是突破性的,因为此前有关「中国是否存在现代市民社会」的讨论一般都认为,感情、大众文化不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公众群体。而在这种观念背后,其实限定了「真正」的公众必须是理性且具有解放作用的。
因此,过去人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在寻找一个真正理性的、独立的且具有解放性的公众身上,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中国只有在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少数时期才出现了高度参与性的理性公共辩论,因而只有在这短暂且间断的时期内,中国才出现了真正的现代公众。
而其他更长的时期,比如本书所讨论的20世纪30年代,它就因其大众消费文化初露萌芽和政治威权主义持续强化的时代氛围,而被认为不可能兴起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公众。
林郁沁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指出,不应该把理智和情感作一刀切式的划分。高度商业化的传媒和高涨的大众情绪,其背后也包含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理性交往」元素。
媒体的炒作同样也可能推动市民对正义的内涵进行探讨,也可能推动市民谴责公众人物的丑行,并界定现代社会公民的正当责任。
因而林郁沁在本书中开始思索:
「大众媒体的煽情炒作是如何有效地动员或询唤了一个对不断集权化的政权表达强烈批评的现代公众。」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林郁沁指出,这桩植根于情感且引起轰动的施剑翘复仇案显然形成了可以称之为「参与性」和「批判性」的公众行为。而她通过汲取杨凯里(JanKiely)以及迈克尔·华纳(MichaelWarner)的理念认为,「公众是通过询唤而存在的」。
因而她认定,在中国的批判性的政治参与正是被像施剑翘复仇案这样的热点事件所询唤了出来。
在施剑翘复仇案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热情地公开发表他们对此事的意见,甚至是传统中在政治上没有权利也没有参与意识的人,也都纷纷就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加入到这场公共讨论之中。
因而沿着这样的观察路径,林郁沁把施剑翘案所呼唤的广泛的「公众同情」,当作具有参与意识、批判意识的现代市民公众兴起的标志。
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批判性政治参与在中国的真实历史中究竟如何发生。
比如前文所说,以施案为蓝本的改编作品大行其道,上海、北京、天津的市民每日追着看描述仇杀案的连载小说,其实也具有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因为「公众同情」正是靠消费主义行为表达出来的,由此,以施案为中心的媒体报道和小说改编,就为那个时期的公众创造出了一些进行公共讨论的机会。
这些机会在当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正是在小说和戏剧的领域中,对复仇女的集体同情增长起来,这种同情反过来合法化了那些在改编中不断被探索和赞扬的话题和典范。当某些典范承担起隐蔽的、或者有时候不那么隐蔽的社会和政治批评的时候,公众同情本身就变得政治化了。」
这种公众同情,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具有「暧昧」的解放特征的新公众群体在中国兴起了;另一方面,当他们的力量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他们还能因其道德、舆论的权威性而成为一种巨大政治力量。
施剑翘在二审被轻判后,只隔一年就又被国民政府特赦,很大程度上正是公众同情发挥作用的结果。
那么,「公众同情」如何被动员是具有其固有逻辑的吗?这种爆发性的集体情绪背后有着明确的指向和深层动机吗?
详考施剑翘复仇案进展的细节,就能发现其中端倪。
03.
「公众同情」与批判性舆论
可以肯定的是,施剑翘并不是唯一懂得运用媒体来争取「公众同情」的人。
孙传芳的家属和支持者们也在大力争取民意支持。
他们为此邀请不少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如张学良、卢香亭等发布声明或举行新闻发布会,以示支持。
但是,支持者们基于「杀人偿命」这个基本的法律精神,要求法院严厉判决凶手的呼声,却几乎被施剑翘积聚的「公众同情」所淹没了。
这就显示出「公众同情」背后高度理性化的一面,它并非暧昧不明或者完全被动地任人摆布,在其背后其实有着明确的原因与指向。
在书中,林郁沁将「公众同情」普遍倾向于施剑翘的原因归结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市民大众所处的大时代背景可谓内忧外患:
对内,国民党在1927年表面上结束了困扰中国多年的内战,定都南京,开启了史称「南京十年」的国民政府统治。但在事实上,西部、西南部、华北地区拥兵自重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江西组织起来的蒋介石所谓的「共匪之祸」,仍构成了统一国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当时不少人都把所谓「军阀混战」当作中国孱弱国家形象的根源。
这时,施剑翘以弱女子之身击毙大军头,为国除害,为父报仇,自然容易得到公众的广泛同情。
对外,在日本蚕食中国华北五省渐成态势的背景下,孙传芳又被传出与几位亲日派「卖国贼」过从甚密,并被传已经加入了日本人侵占华北五省的计划。
因而,人们愤怒地支持施剑翘代替他们实践正义,并希望借助这起暗杀来震慑那些「卖国贼」,以提振救国者的决心。大众同情的天平也就自然地倒向了施剑翘。
但如果说施剑翘赢得「公众同情」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刺杀的对象是「军阀」代表之一孙传芳,那还只是说对了故事的一半。
事实上,从当时改编的小说与剧作作品来看,一种潜在的市民公众对政府的批评也包含其中。
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无力平息内乱,而且对日本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
非但如此,为了制止公众批评国民政府当局的对日绥靖政策,蒋介石在1934年11月14日还布置了对《申报》编辑史良才的暗杀,此人一直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而以施案为蓝本的改编作品就变换方式,极力凸显施剑翘以女侠的身手,担负起伸张国家正义和公共正义的责任,手刃与日本人有勾结嫌疑的卖国军阀。
这些作品越是凸显施剑翘的迅速、果决与英勇,就越是让读者公众感到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失败。颂赞侠的英勇,背后是对官的无能的讽刺。
同样,公众消费施剑翘案的热情,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民政府的思想管控。国民党政权从一开始就使用审查制度来巩固它的统治,并在1930年实行了管控文化、思想自由的出版法。
以此为据,国民党当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加强了对所谓反动的「文化」作品的压制。
1935年,尽管新闻记者提出强烈反对,但当局还是制定了新的、更严厉的新闻法。
在这样的出版限制之下,施剑翘案以其巨大的可炒作空间,使得有关叙述躲过了国家审查的雷达,从而为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发表公共议论的平台。
在施案基础上所改编的连载小说并不服从于「严肃」新闻业等常规渠道所受到的那种控制,它允许读者公众们广泛讨论对日政策问题、官方系统之外的公共正义承担问题等等。
在这一点上,林郁沁也是在与林语堂隔空对话。1936年,林语堂曾将中国缺乏批判性舆论的根源归咎于出版界过分商业化和娱乐化。他引上海《申报》作为反面例子,批评报纸以市场为导向的性质导致了商业广告泛滥、炒作性新闻报料占据主导地位。
但林郁沁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和其他人哀叹的作为『政治冷漠』证据的商业主义、炒作和情感主义实际上正是一个批判性公众产生的首要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林郁沁认为,对施剑翘案的集体同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具有参与性与批判性的公众群体,而他们表达公众同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一剂解药。
04.
「公众同情」是威权政治的解药?
1936年10月14日,下午两点,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度过了344天囹圄生活的施剑翘,就此获得了自由。
特赦的背后自然不难找出公众同情所构成的影响。
因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全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等不少市民团体开始以公众同情为基础开展运动,它们纷纷通电呼吁特赦施剑翘。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大佬也纷纷出面救援。
但是林郁沁在书中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夸大公众同情在实际政治事务中能起到的作用。
以本案为例,公众同情很可能是被更高层次的政治势力所操纵了。在书中第五章林郁沁就提到,冯玉祥在整个事件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有传闻说,从策划谋杀到操纵舆论再到特赦释放,从头到尾都有冯玉祥的密谋,公众同情有可能是被他利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公众同情易受控制的特性,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下显得更为明显。
国民政府特赦施剑翘只是手段,它更希望借此挪用公众的同情和认同,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正如林郁沁在书中所说:
「对复仇女的特赦可以招降叛逆的英雄,以便实行扼制并将她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和英雄情感据为己有。」
这背后的逻辑是,国民政府在特赦令中特别强调释放施剑翘的原因是因她为「孝」复仇。这就显示出,施案其实是给了国民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公众认同当时正在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及其背后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合法性。
因此,特赦施剑翘对于确立「新生活运动」乃至国民党政府的道德权威,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特赦施剑翘案同样也意味着,借助党义,可以磨灭这个事件中违背法律规范的一面,这实际上也是为党化司法打通道路。
简言之,尽管公众在类似施剑翘这样轰动性案子中能获得参与性、批判性的,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威权政治的解药,但这种批判性力量在根本上却是不稳定的。
因为公众同情的独立性从未通过法律或官方的手段被制度化或者作为法典而固定下来。事实上,自发的公众同情,就其力量源泉来讲源于一种侠义精神。
林郁沁对此总结为:公众的本质是「侠」,那么根据这个设定,公众也同时就是拒斥法律或制度手段的。因为它的道德力量恰恰在于它的自发性和它「情」的根基。
既然以「侠」为根基的公众同情既能勇于批评时弊,又容易被误导操弄;媒体上的轰动传播,也会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及消费文化所左右。
那么,我们或许需要在结尾处将目光投向本案中那些处境尴尬的「批评家」身上。
他们认为,施剑翘的「孝情」和所激发出的公众同情,因其超越于法,所以应当受到谴责;而同时,他们也对试图掌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充分警觉。
但他们对现代法治规范的追求,以及希望对公众力量进行制度化保护与规范的主张,始终处于无可争议的边缘位置。
或许也正因如此,林郁沁在本书结尾处说:
「在20世纪中国,集体情感主义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然而没有保障的、对于威权主义统治的解药。」
于今犹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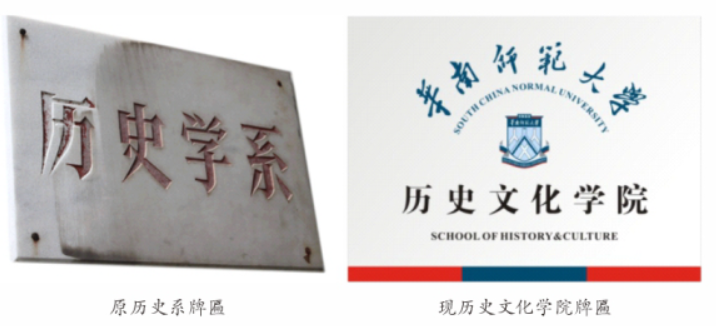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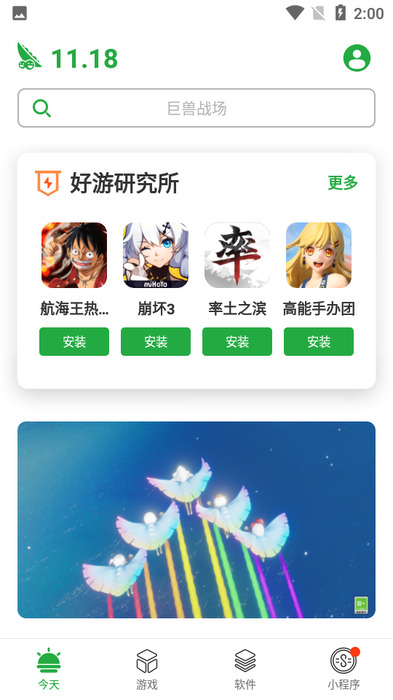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