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铃草(1)
前边大路口有一面大型广告墙,建造的时候,我每次路过都要站在工地上观察那堵墙会不会扭曲。工人跟我熟了,我们偶尔聊聊天。广告墙后面是一块水田,距离一米五,我说:“墙这么高,不是把田里的阳光挡住了吗?”其中一个工人师傅回答:“谁说不是呢?我们也只不过奉命行亊。”我记得清清楚楚,水田后坎一角,生长着四五株八爪金龙,另外有一笼刺梨,一窝山楂果,秋天还开放着千里光和野菊花,为了修墙都被清除掉了。每当天气好,我都会从岔路口走下国道,穿过耗子坡脚高速公路底下的涵洞,去对面山上挖草草药。我肩上扛着的药锄有三斤重,另外我还背个帆布包,进山采药是我退休后的爱好。我对尝遍百草乐此不疲。实际上我并没有带回来多少草药,并不是我偷懒,是对面山原本没有什么贵重药材了。
我在这条山道上已经走了四年,真是再熟悉不过的路。我越来越心烦,所幸建造广告墙这件事在沉闷的生活环境中短暂打开了一扇窗口,让空气得以流通。我每天都去看工人师傅砌墙,看他们用水泥沙浆把墙体抹平。我想将来他们会请一名画师来作画,在这面接近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墙面上作画,站在钢管搭成的架子上把各种颜色尽情涂抹上去。我甚至许多次考虑,这样大的画恐怕要用拖把蘸着颜料才能够完成吧。工人粉墙时我担心墙面不平会给今后作画带来一定的难度,三番五次跑到墙脚去看水平。那个包工头不得不阻止我:“宋老师你得离远一点,当心他们掉东西下来,砸着你若是闹出工伤我可不好负责。”我差不多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将要在钢架上作画的画师,总是添乱,碍手碍脚。旁人不知道,怕会认为我是承包商或者施工人员,其实我不是,修建这堵大型广告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破土动工的那天,我甚至都不清楚那些家伙是在干啥?

观音草(观音草图片)
广告墙完工后,并没有如同我所想请画师来作画,广告画是事先印刷在塑料纸(或布)上的,由多张拼接而成,画面是一条山溪,一片森林,还有个穿布依族服饰的女孩子,写着“石破天惊的地质奇观?响螺河大峡谷漂流好去处”。因为没有请人来绘画,我感到特别失望。有关部门总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杀鸡取卵未免愚蠢,而且响螺河也根本不适合搞漂流,我在白秧坪住了快四年,只知道河水比酱油黑,比南明河臭,从来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更从来没发现响螺河像画上这般美好。我把自己平日的不顺心迁怒于此。我把所有不快告诉了叶金铃。她照例把我嘲弄一番,然后读她的小说,去菜地里看她栽的花草和罗卜。烦躁的情绪其实是会传染的,如同弥漫在雨霖霖日子那种阴冷。
退休前我在铁路局的工会里搞宣传,跟第四任妻子搬到乡下居住以后抛开了画笔。我倒不是厌倦了绘画这种职业,而是认为自己实在缺乏当画家的天分。更别指望成名。我曾在那家企业里画宣传画。等到我和叶金铃结了婚,搬到乡下以后,就不再摸宣纸和画笔,不再提起有关绘画的事。附近的老乡误以为我是中学老师,当然,也无任何人了解我过去的职业画家生涯。
叶金铃是我的第四任妻子。她过去在省民族歌舞团拉二胡。她拉二胡的功夫虽然赶不上阿炳,平心而论,我感觉她还是有一些艺术细胞。叶金铃从来都只是混在民乐队里拉合奏,说不上滥竽充数却也不曾有爱挑剔的观众喝倒彩。她一次都没有坐在舞台中央,让聚光灯集中在他的头顶,而其他乐师仅为伴奏。刚认识叶金铃那会儿我经常想,她没有能开一场二胡独奏音乐会,说不定是她所在那个民族歌舞团的重大损失。我们认识九年后才结成婚。依我们的年龄,照理不应该进行这种马拉松似的恋爱了。可是确实不成啊,主要的反对派来自叶金铃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她的长女是个工人,平时特要面子。小女儿在一家公司里打字,尽管自己常跟公司领导调情,可是自打知道母亲的黄昏恋以后,就感到抬不起头来。她们的丈夫都不太像男人,说话阴阳怪气,叶金铃女儿的态度跟两个家伙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她的丈夫在她的两个女儿上小学时就去世了,我则是三次离婚,所以她的女儿女婿背地里叫我“老色鬼”。他们对当妈的说:“你瞧老色鬼结过三次婚又离过三次婚,他哪一次是认真的,他都到了五十多岁还不肯安份,更何况妈妈你也是快五十的人了。”
“我才四十六岁。”叶金铃说。
“妈,你别让我们爸爸他在地下十几年了还不能闭上眼睛。”小女儿如此说。
叶金铃因女儿这话激动而浑身颤抖:“我怎么不让他闭上眼!他死时你姐才九岁,你才七岁,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我告诉你,我对得起他更对得起你们。”
“妈你不嫌丢人,我们做女儿的还嫌丢人。”大女儿更加直言不讳。
“如果是嫌丢人我就走,你们离我越远越好,”叶金铃伤心、恼羞成怒说,“等我死了你们也用不着来看我!”
她一冲动就从家中跑出来,到铁路局工会找我,眼泪像断线珠子。我的同事纷纷对她表示同情,工会主席甚至替她泡了一杯龙井茶,同事们没有笑话我和叶金铃的关系。我的儿子倒十分开通,他在加拿大留学,对此绝无反对意见。九年马拉松式的恋爱,反复曲折,使人身心疲惫。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叶金铃还试图自杀过一次,喝下半瓶“敌敌畏”,所幸毒药是伪劣产品才没有死成。恰是母亲的义无反顾,她的两个女儿被迫让了步。我们俩结婚非常低调,没有通知亲朋好友,没有请客,我甚至都没有打电话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儿子。我和叶金铃找了家僻静的酒店,我替她点了六菜两汤。随后喝茶。天黑了,我带她乘电梯去二十八层的“军港”唱歌,半夜打的回家。不久后,我们俩在离贵阳五十公里的乡下租了农民的房子开始新生活。
替叶金铃音乐才能鸣不平的愚蠢想法贯穿我们俩谈恋爱漫长的九年时光,成为我对她倾吐衷肠的一种主要方式,她则对我的绘画技法大加吹捧,有时候甚至激动万分,咋咋呼呼,在她眼里我差不多就是李苦禅了。结婚以后,我特别庆幸的也恰恰是叶金铃老师她丢了二胡。结婚是我们的重要里程碑,我们俩都不约而同采取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最极端方式,我放弃绘画,而叶金铃更加彻底,干脆摔烂了那把跟过她三十年的二胡。她声称对这种乐器烦透了,而她想活得轻松自在些。她从民族歌舞团退休后选择了种花,理由源自她年轻时看过的一部叫《花翁遇仙记》的电影,黑白片,她兴奋地告诉我,种花是一种多么有希望的事业啊,阳光明媚,蓓蕾满枝,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无论你在何种季节何种天气,也甭管你的情绪怎样低落身体怎样伤痕累累,然而当你眼前开放出姹紫嫣红、绚丽多姿时,你的心境就会豁然开朗,哪怕在三九严寒时,大地了无生气,但当你走进一座梅园,那些梅花傲雪凌霜,总使你产生无限勇气,寒冷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对于她的这番理论我基本上赞同,对花、对草、对大自然的爱好我们应该是一致的,画了半辈子画的我自认是色彩方面的专家,明知道登高或者更好,看花就未必真让人心情舒畅起来,还可能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未必如同叶金铃说的那么绝对。我很爱她,真的很爱她,甚至还像少男那样觉得离开她就不打算活,所以说格外对她迁就。搬到乡下后,我立刻向农民租了块大小半亩的菜地,让叶金铃充分展示她种花的本事。
她先是栽上月季、蔷薇、茉莉、海棠。后来我们去阳明路花市,买回来木本的八月桂和山茶花。当然不会忘记种上腊梅和红梅。在当年的冬季,叶金铃还种了一株樱桃和一株杨梅,她甚至栽下了我挖回来的中草药,有几株八爪金龙,有一片白芨和观音草,她还栽了些罗卜、白菜和蒜苗。她花园的事我从不插手,只有一次,有农民的一头黄牛闯进去,把观音草和白芨啃光,刚吐芽尖的樱桃树也被连根拨起,瞧她一愁莫展,我向房东借了柴刀去坡上砍些柴棍,又买了些竹子。我们用四个星期时间修建了一道篱笆墙,还做了一道柴门,编得相当精致。叶金铃沿篱笆墙种上蔷薇和月季,仅仅半年时间,带刺的藤本植物把篱笆缠绕得密不透风,花团锦簇。
叶金铃种的蔬菜并不多,我们都是在房东或邻居家买菜,偶尔去县城采购,十分方便。房东的儿子在一所小学教书,偶尔回家。房东老两口比我年长十岁身体健康,每天仍早出晚归,在山坡上干活,他家养了头牛,每天会牵到外面去放一次,我爱看房东老韩牵着水牛在落日余晖中悠然走回来的场景,心中的不安和烦躁便会不知不觉消失。叶金铃种菜是城市人心态,要求绝对的绿色产品,从不施化肥,从不用农药。说起来也怪,现在的蔬菜遗传基因恐怕是变了,不泼点尿素,总是不肯长,即使生长着也是老气横秋的模样;不喷农药,过不久,菜叶上粘满虫屎,各种各样的昆虫在它们的自由王国里任意肆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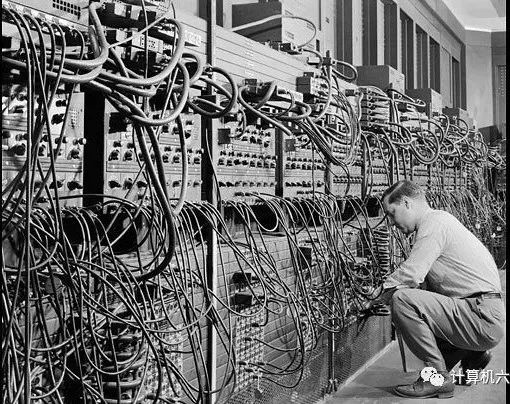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