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是最接近如愿以偿的梦幻的”,真实的历史难免不尽如人意,将历史原封不动地还原出来,不加以艺术手法的加工,会让观众感到了无生趣。
因此,使传奇故事介入历史史实,让历史人物为传奇人物增添“真实”,将不完美之处辅以艺术手法加工,用直观化的影像语言描绘生动故事情节,让传奇性模糊人生中的苦难艰辛。

在电视剧这门艺术的娓娓讲述中,减轻观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满足其情感需求与审美心理,使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感到些许慰藉。
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历史事件为传奇故事充当背景,家族故事也在兴衰动荡中愈显传奇。
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的历史背景是粗略且模糊的,然而,历史史实和荧屏内的家族传奇故事交织呼应,生动逼真地写照出特定历史时期下家族的生存情境与思维方式,展示了创作者借现代价值观念改良封建文化的自觉意识。

电视剧《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借边疆暴乱之局势,以一封“信”设下圈套,使仇家达盛昌大举收购粮草,使乔家摆脱生意衰败的危机。
在太平天国作乱的时局下,乔致庸潜心研究从叫花子处买来的百年商路地图,不顾家人反对,南下武夷山、北到恰克图,开辟早已封锁多年的茶路,千万茶农的生意也得以恢复,让乔家家业重返辉煌。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情深义重的乔致庸因秘密安葬太平军将领,被昔日恋人一纸诉状身陷囹圄,被圈禁的同时缴纳了金额不菲的银两,乔家家业再次归入低谷。
当八国联军入侵紫禁城,慈禧与光绪弃京出逃之时,乔致庸冒天下之大不韪,给朝廷捐银两以助逃难,重新获准汇兑官银使得乔家生意蒸蒸日上。

中国清政府和来华列强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后,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乔致庸创办的票号却由于赔款而得到巨大的收益,虽然乔家家业再返辉煌,但立志图强报国的乔致庸怒不可遏,其力主实业救国、造福百姓的“义、信、利”理念令人钦佩,乔家千古佳话也因此永留存。
该剧体现了近现代家族传奇剧所注重的“家国一体”叙事模式,秉承以人带史、以国史带家史的策略,在深邃厚重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传奇人物、构筑传奇家族,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让电视剧充盈着鲜活的时代气质,与家族兴衰荣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展现角色在各个社会情境下所作出的抉择,有利于丰富人物性格的层次性,使人物形象趋向多元。
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历史人物的设置为虚构主角的“真实”提供依据,也让观众直观体会到家族在传统历史中刻下了无法忽略的痕迹。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家族本身的存在就是传奇。电视剧《大宅门》讲述清末至八国联军侵略、军阀割据到日本侵略的动荡历史变迁中,创作者有意塑造了一些作为社会历史背景而存在的人物形象,如慈禧、李莲英、詹王爷、常公公和田木父子等。
这些人物均与白家的兴衰荣辱息息与共,白文氏收买常公公盘回白家老号、白景琦与日本人田木青一换刀盟誓而为白家家族带来无尽的麻烦……

这些历史人物自然地穿插融入电视剧中,增强了剧情外在的叙事张力。
这些人物与大宅门中白萌堂、白文氏和白景琦等家族主要人物所形成的内在叙事张力交织互动,形塑了“历史——传奇”的深广叙事空间。
家族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共同出现,让家族故事愈显传奇瑰丽。
在白家三代人,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在近现代中国最为动荡起伏的历史时段内,白家百年老字号百草厅上演着兴衰荣辱的史诗故事,创造着属于各个当家的传奇人生,打造出与历史真实共存并生的家族故事。

同时,在家族传奇广阔的历史叙事空间内,创作者寄予了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化深切地思索,历史不仅是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更替史,家族故事在历史进程中也留下足迹,平凡个体也能成为传奇英雄、谱写历史。
所谓寓言,即指以虚构的故事去阐述某个道理或某种教训。寓言与历史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它经常借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以再现、还原和重塑历史,达到警醒世人与讽喻劝诫的目的。

近现代家族传奇剧在此影响之下,对于家族故事所进行的历史“再创作”也是基于当下价值观念及现实生活——“经过同历史的协商与对话,赋予历史以新的认知及意义。他们用行动否定‘历史本来面目’的信条,把历史视为一个充满能指,而所指却横遭悬置的世界”。
因此,近现代家族传奇剧创作者们将历史予以寓言化处理,凸显历史话语的能指功能,表达了新历史主义对家族传奇与历史现象的一种透视,也显现出对历史的一种主体意识。

寓言化作为一种具有巨大表现力的叙事方式,使近现代家族传奇剧突破传统历史叙事的扁平化,使影视表达突破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而直指人类的心灵深处,开拓出一个极为深广的艺术空间。一、历史真实背景的虚化寓言化叙事的一大特征就是历史背景的模糊化与虚构化。
近现代家族传奇剧创作者借助寓言化的叙事方式,在还原历史真实时采用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法,使得电视剧蕴含着更具哲理性的深刻内蕴,呈现出现实世界无法直接传达的寓言化指向。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历史的隐匿与社会功能的淡化。

首先,这类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的历史被精巧地隐匿于家族故事之后。仍然在刻画历史,但它不再遵循传统的方式“历史地”去叙述,不再以还原历史作为创作旨归,而是携有主观的价值倾向与审美指向,使“个人话语”得到极大的张扬。
“历史”不是展示的主要对象,仅作为叙述背景映射个人话语中所隐含的现实指涉,也就是说,其所叙述的历史故事可以只是对现实的寓言,即作为历史寓言来看。
因此,历史史实与家族故事之间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被消解,丧失历时性的意义,家族成为漂浮于历史时空中的影像碎片。

当近现代家族传奇剧创作者将历史事件与家族故事置于共时空间重新编排组合时,家族空间仅是历史事件形构的虚幻场域,失去家族所应负载的文化意蕴。
其次,历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近现代家族传奇剧中被淡化。在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下,近现代家族传奇剧多是以个体视角洞察历史,展现个人化的历史记忆。
而历史真实刻度及事件所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被忽略,历史的发生发展不再具有因果逻辑,而是虚化为家族生存的背景,烘托人物的传奇氛围。

由于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历史反服务于传奇人物的塑造。
《红高粱》在开篇就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提前表明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从个体“私历史”的生命体验讲述他们在山东高密的红高粱地、单家酒坊近乎理想地域下所谱写出的生命赞歌。
即使电视剧中穿插了抗击日寇的片段,但也绝不是以主流叙事的方式而展现的,抗日段落的增添不过是弘扬人性不屈的符号。

电视剧《中国往事》从“耳朵”的个人视角展开家族故事,他是曹老太与佃户所生的孽子,算命先生判定他是小土神转世后,他成为一只盘踞于各屋房顶及角落的壁虎,替曹老爷窥视着家中所有隐秘与可怖。
在他心中的曹家宅院,母子不洁、手足残害和情仇纠葛是生活常态,“耳朵”正如深宅大院里盘踞已久的阴蛰毒蝎,不断引领着观众见识到曹家家族最深处的扭曲畸形。
由于近现代家族传奇剧的寓言特性,创作者有意无意地赋予剧中人物悲观化的宿命,因寓言本身晦涩含糊的修辞表征,令人物命运隐约缭绕在波云诡谲的氛围中。
在电视剧《大宅门》中,开篇就讲述了詹王府认为白二爷白颖轩误诊了大格格的喜脉,忿忿不平的白老太爷白萌堂亲自去詹王府赔罪并暗中为格格保胎,真正惹怒詹王爷,反害白颖轩丢了性命。

《故梦》中秦燕笙为了从封建大家庭里救出陆天恩,二人假扮情侣恳求陆老夫人让他们一同出国,但陆老夫人为了冲喜让二人结婚,陆天恩同意,一心出国、满怀理想的秦燕笙被迫嫁给他,在婚后相处的过程中,秦燕笙渐渐发觉到陆天恩仍旧依附于家族的本性,毅然决然提出离婚、继续求学。
《范府大院》的范敬堂始终执着于封建伦理中主仆等级,视聪明能干的养子郭彩三于不顾,奋力培养虽出身好但品性差劲的继子施光汉,范家家产险些被施光汉挥霍一空。
这种出发点和结果的错位往往隐喻着传统价值观念的陈腐、种因必得果的寓言以及人物悲观的宿命。

另一方面,人物宿命还体现在对其死亡命运的抒写中,给家族故事拢上神秘的面纱、营造阴郁的氛围。
在《中国往事》中,作为曹家次子的曹光汉在欲望的驱使及道德观念的束缚中饱受心灵的煎熬。
他留洋归国本应拥有先进西方思想,但仍旧无法自由地追求自我命运,他遵循封建观念接受了家族包办的婚姻,寄希望于自制火柴炸药以振兴民族的志向却锒铛入狱。

渴求自我人格独立的他以偏执自我的行为折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最终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捍卫仅存的生命自由。
2009年播出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一部充斥着人物与国家命运隐喻色彩的近现代家族传奇剧。

该剧以杨氏家族作为切入点,杨立青、杨立仁和杨立华三姐弟分别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其无法调和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各自持有的政治立场上。
在主角杨立青与兄姐、姐夫董建昌、瞿霞兄妹等人之间所展开的不单是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故事,而是通过清晰的能指,以革命的话语体系讲述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各种“主义”间的争斗,这种“主义”之争借助多元复杂的人性展现,观照国家、民族及个体命运的沧桑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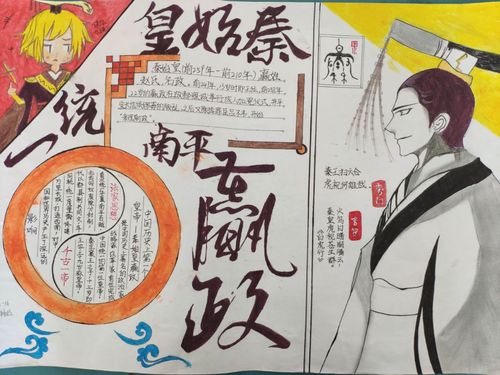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