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sciencenet.cn/blog-415-663187.html。

《中西文化交流学报》创刊号
03
《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的际遇
我对西方文学理论有兴趣,特别是reception studies (接受研究),因此,我也留意中外读者对《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有什么反馈意见。我想,也许会有读者指出书中欠妥之处……
学术书的际遇,不像CNKI(中国知网)论文那样有网上“征引量”可供作者参考。因此,购书网站如“当当网”的读者短评成为参考材料。我记得,梅节先生为了支持我,把“当当网”上的评语转发给陈庆浩先生,然后再发给我。
网站评语:
。
有正式的书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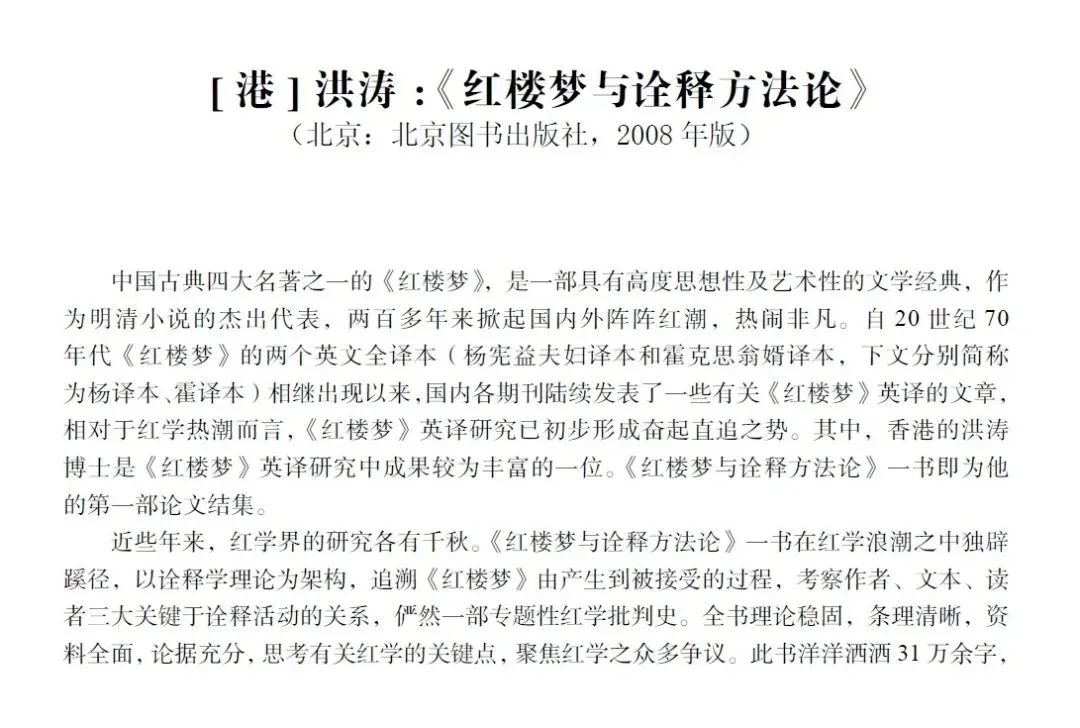
冯凌《[港]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
有一篇。是冯凌写的,发表在《华西语文学刊》2012年1期。冯凌的评语,高淮生先生的书评也提到了。当时,冯凌是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没有公开发表的“接受”主要出现在私人信件或私人场合中,例如,孙勇进先生写信来谈拙著。2008年他正在写博士学位论文,那时候拙著新出版,引起他的注意。孙先生认为,他在学位论文中引述拙著,也是一种反馈。他读书很细心,能指出书本某页有错别字。
比较意外的“遭遇”是在吉隆坡。大约是2008年夏天,我到马来西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马国的丹斯里陈广才先生对我说:“一直在找《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这本书。”我想,也许书名本身有点吸引力。
外国因缘很稀少。只有外国学者 Ronald Gray 告诉过我,他用英语写成《红楼梦》导读共四百页(书稿正在编辑),论及我的见解。他的看法怎样,目前没有人知道。
另外,有学生(毕业后,到其它学校继续进修)特地写信来告诉我:《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是大学某科目的课程用书。
总之,这本旧书的事,我印象甚深。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是我第一本专书。第一次出书,总是事事新鲜、难忘,包括“出版合同被邮局寄丢了”。

胡文彬先生
高淮生先生在书评开头描述了他和胡文彬先生谈话的情况。胡先生阅历丰富,又是研究《红楼梦》的大方家,他的“读后反应”自然特别引人注目。高先生连胡先生说话的神情都特写一笔,读来另有意趣。
04
进一步讨论——“自己该做的事情”
高先生在书评中提到:“作者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哪些是需要别人去做的事情,尽管不免给人以明哲保身的印象,其实,他教读者‘看清红学真相’的一招一式已然参与到红学‘改弦易辙’的过程中了。”
关于“自己该做的事情”,旅法学人陈庆浩先生也向笔者提过。陈先生指出《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的剖析、论断部分占了书本的大量篇幅,他认为作者可以多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的新见解。
这里说明一下,以前我没有贸然提出新见新,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实际原因是:当时(2008年以前)我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和研究空间。另一方面,“《红楼梦》翻译学”有研究空间,我就先做翻译方面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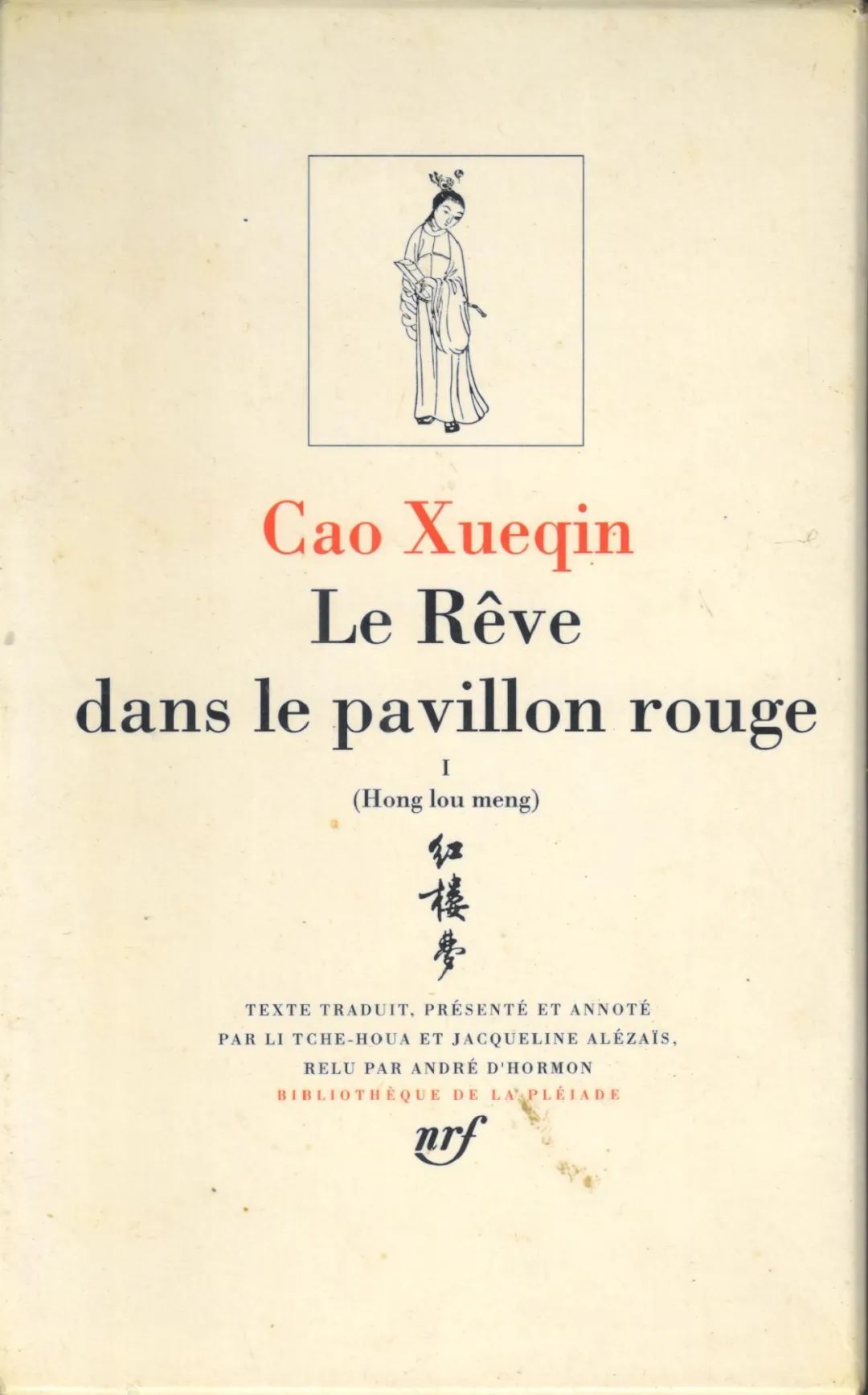
《红楼梦》法文本
到了2019年,在疏理各种《红楼梦》“原型论”过程中我有一些新发现和新见解。以下,分两点简略解说。
第一点,小说将“金陵省”各地的人和事,汇聚到“长安都”(贾家所在地)。书中的“金陵省”,可能包含南京、苏州、扬州、杭州这些城市。南京、苏州、扬州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康熙帝南巡兼省亲,是否关连小说中的元妃省亲、刘姥姥省亲?
上面这些研究线索,不全是我个人的新发现,但是,我提炼出来的是“要旨”,与“原型论”的重点不在同一轨道上。请看下文。
第二点,南巡省亲、靡费、“亏空”问题,都与财政、营生有关。财政困难、持家不易等环节,作者一写再写(秦可卿、赵嬷嬷、秦显妻、王熙凤故事),因此,财政和营生之难,应该是小说的要旨之一。
说起营生,刘姥姥一家人连吃饭过日子都有困难,她被迫向贾家求援。刘姥姥家和贾家连过宗,两家人也算是亲戚。

邮票《刘姥姥见凤姐》
刘姥姥在贾府的遭遇,又衬托出妙玉奢靡浪费(她似乎有意炫富)。小说作者对奢靡浪费是否特别反感?如果是的话,为什么?
走笔至此,笔者联想到:贾芸向舅舅借钱营生,其性质也近似刘姥姥入贾府求助。还有,邢岫烟的景况也值得注意。她依傍亲戚过活,为了应付日常开支,连衣服都得拿去典当(第五十七回)。
小说家是不是对落入困境的事耿耿于怀?为什么小说家要反复写这类小故事?笔者认为,秦可卿、赵嬷嬷、秦显妻、王熙凤故事,还有贾芸、邢岫烟的一些情节都可以用“所指优势”来解释。
以上所述,详见于《幻笔的艺术: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优势”释出的要旨》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3期。这篇文章比较长(40多页),它有一个“简版”,刊于2020年8月16日的古代小说网。
文章刊出后,我寄信给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女士,信上说:《幻笔的艺术》这篇文章的新见解可以略补《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留下的空白。
顺带一提,《红楼梦》中的“金陵”,是个“省”,书中有明文。许多学者只看到“金陵”二字,没有注意到“省”字。

清刊本金陵省城古迹图
我指出“金陵”是“金陵省”,不是“市”,这样做可能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例如那些强调“《红楼梦》专写某城市”的人。我特意将“金陵省”放在文章标题之中,没想到“明哲保身”的事。大概高先生没有考虑我第二本书(《女体和国族》)是何状况,以致生出“明哲保身”之谈。
《红楼梦》有意架空,“金陵省”也是架空的一个环节,因此,研《红》者如果一味文史不分,不免有“反《红楼梦》”的嫌疑。
05
方法论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我在《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优势”释出的要旨》一文中提到“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观念,我是在考虑:有些话题例如“秦学”之类,能否保持生机?能否持续发展?
旧书有了新书评,这刺激我反思:拙著的话题(方法论)是否过时?有可持续性吗?
试看一例。高先生书评中摘录了我2008年的言论,例如:“‘家恨’,成为大部分新索隐的枢纽,这枢纽方便他们在诠释上通向朝廷政争。换言之,曹雪芹的历史性(historicity)成了新兴索隐派的‘种子’(诠释的基本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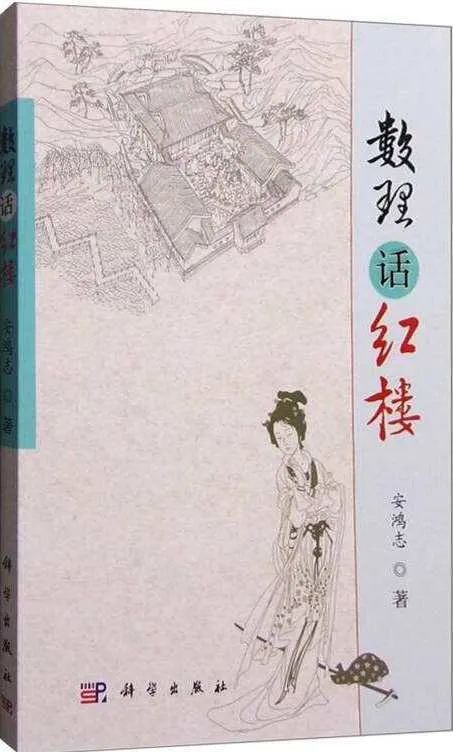
《数理话红楼》
事实上,这套诠释法(家事关涉政争政局)在近年的红学著作中一再重现,例如,与雍正帝相关的“《红楼梦》研究”不时出现,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就走这条路的。此外,谈“《红楼梦》反雍正”的文章也有不少,例如:安鸿志《数理话红楼》(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畅谈《红楼梦》顺带骂雍正。
“家事”,不一定是曹家的事,“别家家事”也可以用这套诠释法。论述的取向仍是说作者或者作者家事卷入政局、政争之中。
关于“方法”,吕启祥老师对拙著的概括很精到。她在《应运而生迎难而上: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4期)有一段话提到拙著,她很了解“方法论”的重要性,她说:

吕启祥老师
这里我还想提到洪涛先生的一本新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著者很有自知之明,借助西方视野十分谨慎,也有知人之明,检点前贤成果,不落窠臼。本书对繁复的红学现象不以时期划段,不以人物为线,也不以流派分野,关注点在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从作者、文本、及特殊读者(脂评)三者着手,看红学家们如何诠释以及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
这种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追问,往往会发现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却源出于同一种方法,或者某学者用同一方法竟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这实在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很有深度的学术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红学真相,看看到底有多少站得住的有学理依据的成果。
她一句“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就切中肯綮。这里,我再补一句:某种方法,可以达到什么诠释目的。

《红楼梦校读文存》
方法的运用,有左右大局的力量,但是,有时候方法的背后是目的,而目的可能主宰方法,红学泰斗也擅长此道。因此,研究者“怎样运用某种方法”和“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也是我论析的对象。
近年,历史性(historicity)仍是许多《红楼梦》新说的“必经路径”,例如,有人强调《红楼梦》是晚明文化的产物,有人强调《红楼梦》是雍正朝的产物(针对雍正帝),有人强调故事反映乾隆朝……
人们谈《红楼梦》的历史性,可能有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就是purposeful),这里不便深究。其实,《红楼梦》整个故事经营自身的历史性,例如,书中说京城是“长安都”,还有节度使、平安州等等。小说家营造这个时空大背景,总原则是不愿与明、清拉上关系。准此,一些学者选择无视故事内文的大背景,自己在那儿做取舍,难脱片面“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嫌疑,见树不见林。读者如果对相关论析感兴趣,不妨翻一翻拙著,尤其是拙著的结论部分。
从方法层面看,不少红学论述的“论述方法”往往是这样的:尝试确定《红楼梦》的时空、尝试确立谁是作者或“原始作者”,最终,作者的确立(authorship)有助于树立诠释的权威(authority)。这种方法和程序,实际上是诠释者的自我授权之法(authorization)。

高马得绘红楼人物
值得强调的是,我探讨《红楼梦》诠释方法论,没有设想拙著成为规约式的研究(prescriptive studies)。读者可能另有期许。
以上,结合拙著得到的评价再次解说拙著的旨趣。希望我不会说得过简(注:涉及文本观念、探佚方法的议题,另文讨论)。
谈论方法,不能缺少相应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案例分析和最终评断。如果没有个案和实际剖析,谈方法将沦为空谈。笔者对没有案例支撑的论说没有兴趣,这也是拙著偏重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重要原因。
具体的案例分析这里不便复述。读者须细看书本中的案例分析才能对“方法论”有较完整的掌握。
总之,考虑可持续性是指:《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所讨论的诠释方法到了今天是不是还有参考价值﹔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看清真相﹔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开拓、细致化。
考察过这十二年的红学现象,再重读拙著,笔者估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高淮生教授写了长篇书评,也许,他有同感?
2020年9月香港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