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逸人生的变异内涵 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他的隐逸人生的影响。但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与其他隐者有何不同?他的隐逸人生与其新型士人人格内涵关联何在,则似乎是人们所忽略者。 从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历程看,先秦两汉与魏晋之后有明显区别。制约二者变化区别背后杠杆就是我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按照这个提法,先秦两汉为中国帝王文化时期。此期隐逸文化的主旋律明显是在围绕帝王文化中心来展开运行。如巢父、许由以拒绝帝王辞让帝位故事表达隐士对帝王核心的疏离;伯夷、叔齐则以二人避世首阳山故事表达其与帝王不同政见。如果说这些传说时期的隐士行为还带有某些高超于帝王之上,因而带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的话,那么到了封建专制时代的秦汉时期,隐士与帝王则完全演化成为主仆之间的依附关系。东方朔把自己“避世于朝廷间”视为一种最佳隐逸方式,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已经丧失隐士自身的主体性,只是在希望寻找一种依靠帝王求生的安全生存方式而已。这是隐士文化的扭曲,因此自然遭到扬雄、班固等人的严厉抨击(参见《汉书》东方朔本传及《严助传》等)。而东汉著名大隐士严光(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之间那种近乎同性恋的亲昵关系更像是一种相互支撑作秀的君臣角色表演,与隐士文化内涵已经关系不大了。 中国文化“三段论”将魏晋至唐宋划为士人文化时期。作为士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文化在此期间也与秦汉时期发生明显变异。其突出特征就是由秦汉时期隐士与帝王的依附关系变异为隐士文化剥离帝王笼罩的自我主体意识。构成魏晋隐逸文化重要的社会基础是门阀士族的崛起和活跃。在门阀士族诸多生活行为方式中,隐逸是其中一种。很多魏晋名士都有隐逸的倾向和行为,但都很难说是纯粹彻底的隐士。如嵇康和阮籍都曾入苏门山拜访过山中隐者苏门山人,寻求隐逸之道。但他们最终获得并效法的不是如何入山成为真的隐士,而是揣摩获得隐逸文化的道理,为现实人生增加参考资源,为士人隐逸文化寻找探索理想模式。 魏晋士人隐逸文化的成功经典模式是谢安。作为东晋士人“仕隐兼修”理想人格模式的典范,谢安曾有过令人敬仰艳羡的隐逸人生内容。其隐逸行为的主要特点是:他完全告别了东方朔和严光式依附帝王的隐逸模式,自己全然掌握了隐逸活动进退之间的主动权;他的隐逸活动完全是一种幸福的人生体验,不仅本人乐在其中,而且也是全社会的幸福人生标本。形成这些特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门阀士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 与谢安这种贵族式隐逸人生相比,陶渊明的隐逸虽然在思想基础和社会社会属性方面有其共性,但在表现形态上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隐逸文化的思想基础是道家出世思想。这是所有隐逸文化的共性所在。具体到魏晋士人的隐逸文化,其思想基础又深受玄学左右。玄学思想中“贵无”“言意之辨”两大主题对魏晋士人隐逸文化精神具有重要影响。“以无为本”的玄学根基从何晏、王弼为理想君王设计人格模式的需求转化为竹林名士用“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玄学人生主题的哲学依据,其中“自然”就是“贵无”的具体体现;而“言意之辨”从《易》学的“言”“象”“意”关系研讨和庄子的“得鱼忘筌”说进一步演化成为魏晋名士“得意忘象”的人生态度。即注重人生真谛,忽略具体行为方式的审美式生活态度。谢安的“雾海行船”,王徽之的“雪夜访戴”均为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而陶渊明也深谙此道。他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好读书不求甚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等等均为这种玄学人生态度的具体理解和化用。可见在思想基础方面,陶渊明与其他魏晋士人的隐逸行为具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然而在表现形态上,陶渊明的隐逸与谢安、王徽之等其他魏晋门阀贵族隐逸行为具有明显和重要的区别和特征。 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对其隐逸行为产生的制约作用。王、谢一类高门大族隐逸行为几乎无须考虑经济状况对其隐逸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他们尊贵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足够支持他们包括隐逸生活在内的所有消费需求,可以超然从形而上的高度品味和体验隐逸生活的美学人生哲理与乐趣。而陶渊明的一生几乎都在与贫困相伴随。其自撰《五柳先生传》曰:“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甚至到了乞讨为生的地步: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陶渊明《乞食》) 古代士人君子大抵有两个脸面底线:一个是生存底线(要脸面还是要生存),这个生存底线或许是很多人苟活的理由;另一个是尊严底线(要脸面还是要尊严),历史上很多人为了生存底线而牺牲了这个尊严底线。但陶渊明一句“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等于向世人宣布:为了尊严底线,自己宁愿放弃了生存底线。这正是陶渊明对于士人人格精神的重要发掘。此前的魏晋门阀士人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隐逸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不具有永恒性。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隐逸中获得乐趣,参悟人生的真谛。但他们可以随时离开隐逸,进入官场。谢安的先隐后仕,便是东晋士人“仕隐兼修”范式的典型案例。但陶渊明不具备那个条件,他是把隐逸当成自己人生最后,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了。如果说“道优于器”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最高精神理念,“道”是形而上,指精神层面,“器”是形而下,指物质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陶渊明以其人生实践所展示对于士人人格中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坚守,已经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其次,对于隐逸文化内涵意蕴的发掘也有明显区别。不同时代,不同生存环境进入隐逸角色的人对于隐逸真谛的体会和理解均有不同。东方朔得意于自己选择“避世于朝廷间”的隐逸方式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严光最为得意的是光武帝对于自己隐士身份的礼遇和尊敬,甚至可以“以足加帝腹上”。谢安在“雾海行船”行为中得到的是超越功利目的之后对于壮观大自然的审美愉悦,王徽之在“雪夜访戴”旅途中得到的则是一种“兴之所至”的人生真谛。而陶渊明没有他们那么高大上,他只能在自己把自己逼向隐逸之路后,自己却能够从隐逸生活中体悟出更加深入、更加真实、更加纯粹的隐逸真谛。先是明确自己走上隐逸之路的缘由: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其六) 作者借夏商周“三季”喻指自己所在晋末乱世纷纭,群小嚣张,“达士”壮志难酬,只能仿效秦末“商山四皓”中的夏黄公、绮里季,走上隐逸之路。尽管这是一条孤独之路,但自己却矢志不渝: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这只进入隐逸世界的失群之鸟,虽然日暮独飞,夜夜悲鸣,但它好比一棵孤生青松,抗拒劲风而不衰,因而坚定地认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而坚持隐居之路的收获,则是从中得到无限的幸福和慰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孤独的隐居生活,艰苦的生活条件,不但没有使他感到任何的沮丧和烦恼,相反却是无限的惬意和欣慰。这其间的欣慰感受之真、之深,来自他本人长期隐逸生活的体悟况味,非他人所能知,故曰“欲辨已忘言”。 从春秋时期士人形成独立的社会阶层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士人精神人格独立的内涵和方式。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庄子以“无待”方式达到的“逍遥”境界。但是什么才是“无待”,怎样才算“逍遥”,人们还是有些不尽相同的理解。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大人先生,是阮籍本人理解的“逍遥”人格形象。说到底,是士人阶层一种脱离世俗,独自无限遨游的精神自由。但由于生活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的精神自由难以与现实对接,非但不能实现真正的“逍遥”,相反只能是“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一生在痛苦的深渊中煎熬。如果说阮籍的人生算是一种“逍遥”,那也只能解释理解为一种痛苦和悲怆的“逍遥”。但陶渊明则在隐逸人生中寻找和真正体悟到什么是士人精神人格中真正的“无待”和“逍遥”。因为隐逸人生给他带来的,不是悲怆和痛苦,而是真正的快乐和惬意。 这才是陶渊明对于士人精神人格建设最伟大、最突出的创新贡献。
(节选自宁稼雨《陶渊明:士人文化精神人格的转折》,《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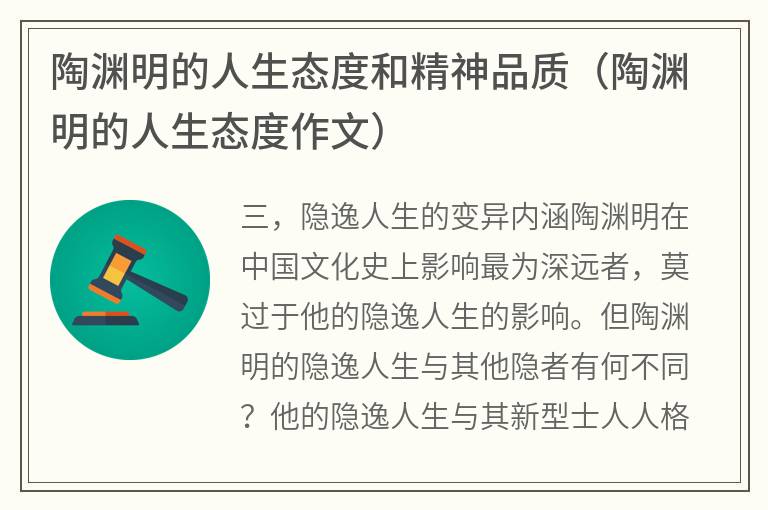
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品质(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作文)






发表评论